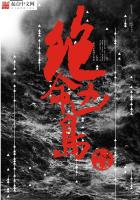“嘎,嘎嘎,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鹅叫声。
鹅叫声还未落跟着就响起了一阵小孩哭叫声,“哇,呜,呜呜,娘,娘,呜,娃娃胆儿,娃娃胆儿。呜,呜,娃娃胆儿......”
鹅叫娃哭声是从一个村庄的普通农家院落里传出来的,鹅刚开始叫的那几声后就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可那嘹亮的小娃哭叫声却一直响个不停。
小孩刚哭闹起来,就听到一困乏中带着疲惫的女子声音:“小儿,小儿,别怕,别怕,娘在这呢。这该死的大白,犯得哪门子神经,这么个大半夜的功夫瞎叫唤啥啊?”
随着女子话音落下,原本一片漆黑的农家院落中,亮起了一簇微弱的灯光,是发声的女子迅速点亮了灯。
屋内有了亮光后,这才看清屋内的景象。女子此时点完灯正转身将躺在自己身边紧闭着双眼,四肢朝上乱扑蹬的一个小男孩抱在了怀中。
在小男孩的另一边是个熟睡的女孩,这个女孩比哭着的男孩看着年龄要大一些,她像是没有听到男孩的哭声一般,在床里靠墙位置呼呼大睡着。
这个年轻的女子一边拍打着怀中刚满两岁的小男孩儿,一边深情关切的哄着他道:“小儿,小儿,别怕,别怕,娘抱着你呢。你看,咱屋子里亮着灯呢。”
妇人的话似是起了作用,趴在她怀中大哭的小男孩慢慢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直到看到屋内的亮光,他才渐渐开始放松下来,不那么紧张害怕了,哭声也渐渐弱了下来。
确定了屋内的状况,这小男孩才一只手捂着自己的一个眼睛,另一只指着墙上的一张画吐字不清的小声说道:“娘,娘,画,画里的鱼要吃娃,娃娃胆儿,娃娃胆儿。”
妇人听了孩子的话,皱着眉头叹息一声,“唉。“眼带不舍得看了一眼满屋中仅有的一张年画。那是一张小儿戏鲤的年画,是今年过年时小男孩的爸爸为了喜庆贴上的。
他们那里过年有放鞭炮、贴对联、贴年画的风俗,他们家这几年贴的年画全是两个孩子喜欢的,像小儿戏鲤,金童玉女,招财童子等等,屋里的墙上几乎全贴满了喜庆的年画。
但自从这小男孩吓着后,每天晚上半夜只要哭闹就指着墙上的其中一幅画,说是那张画里的小娃要吃他。为了不让孩子继续闹,这妇人就依着孩子的意思,将他说要吃他的那张画撕掉,基本上很有规律的一天撕一张,撕了好多天就剩这一张了。
“唉,小儿,这可是咱家最后一张年画了,你没吓着之前贴着满屋子你喜欢的画,自从你吓着后,娘可是依着你把那些画全都撕了。唉,就剩下这黑乎乎的墙了,看着不更害怕吗?”
妇人无奈又有些惋惜的长叹了一声:“唉,好吧,你害怕,娘就将它撕掉。这个畜生,养了它那么多年,没一点良心,要不是它半夜瞎叫唤,怎么会把孩子吵醒?不知道俺小儿这阵子吓着了,身子不舒坦吗,每天半夜来上那么几声,成心的是不是啊?看俺哪天有了空一定把你宰了让俺小儿吃肉。”
妇人一边骂着家里的那只鹅一边抱着怀中的小男孩站起身来,小男孩这时已经不害怕了,也完全不哭了,只是那两只小手仍然捂着眼睛。
妇人走到靠墙的床边,踮起脚,用另一只空闲的手将家里人都喜欢的那最后一张年画撕掉,还有些不舍的长叹道:“哎,多好看的年画啊。年年有鱼,年年有余,这下可没了余了。”
撕下后就将那张画仍到床底下,“小儿,这下不怕了吧?”妇人看了看怀中的男孩,这才松了一口气。
“唔。”小男孩捂着双眼的小手这时放了下来,原本因为害怕紧绷的身体这时也完全放松的柔软了下来。他似是实在太困太乏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竟然趴在自己母亲的肩上睡着了。
“唉。孩子这都闹了一个月了,就是大人也得累个够呛,更何况是个两岁大的小孩呢。”妇人又轻轻叹了口气,一手抱着孩子一手轻轻拍打着他的背,慢慢又坐回到了床上。
等孩子熟睡后,妇人轻轻将怀里的孩子放到床上,这时小孩嘴里还含含糊糊吐字不清的说着不让关灯的话,妇人看他好容易睡着了怕他再被那只可恶的大鹅突兀的鸣叫声吓起来,就没敢再熄灯。
她轻轻的倒下躺在孩子身边,给他盖好被子,开始想着心事,孩子这大半夜的冷不丁的来这么一出,家里的男人又不在家,她一个妇道人家深更半夜的能不害怕吗。
“唉,孩子这都闹了一个来月了,这可咋办?哎。闹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妇人怕吵着孩子轻微的叹了一口气,她都不知道这一个月以来,叹了多少次气了,光今天晚上叹的气她都数不清。
妇人嘴角微动的自言自语道:“这孩子这次怎么吓得这么厉害,村内村外的,都找了好几个会叫魂的老人了,就是叫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别看她在那轻声的自言自语,几乎比她刚才轻微的叹气声高不了多少,孩子是一点也听不到的。
她之所以不敢弄出动静来,是怕再把孩子吵醒,这孩子因为吓着睡的一点也不踏实,哪怕有一点响动他都得惊醒。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天清晨六点左右,天还没亮,孩子的大伯来他们家借工具,刚走到大门口正准备敲门时,不小心放了一个不算很响的屁。
这下可惹了祸了,一下就把原本睡觉就不踏实的孩子给惊醒了,“哇哇哇”的一直哭闹个不停,妇人哄了好半天,直到太阳老高了才算安慰的他不哭了。
从那次以后,这孩子的大伯只要一来到他家,屁都不敢放一个,甚至以后像是有了阴影似的,见到这孩子就躲得远远地,生怕孩子被他的屁给惊醒。
由于孩子的大伯特别爱放屁,只要在他家玩,一憋不住了就赶紧跑出他家很远才敢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都成了他们这一大家子的笑柄。
“唉,孩儿他爸这都外出一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白天地里那么多活,晚上这孩子又闹腾不睡觉,黑白二夜的倒腾,这不得把我也累垮了吗?唉。”妇人又是疲累又是困乏又是害怕,她这阵子被这孩子闹腾的可谓身心疲惫。
这段时间由于家里的男人出差,里里外外的全是她一个人张罗,白天不但指着她下地干活,晚上还得回家忙着做家务,再加上还得照顾两个孩子,特别是这个吓着一直好不了的小男孩,她不累才怪。
妇人名叫张云凤,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人,她的丈夫名叫陆海川,是个在单位上班挣工资的。他们夫妻俩生有两个孩子,大的就是在床的最里面熟睡的那个女孩,名字叫陆建明,小的就是刚才哭闹的这个男孩,名字叫陆捷,他们姐弟俩一个六岁一个两岁。
张云凤看陆捷睡的比较踏实了,又轻轻翻身看了看挤到墙角睡得小猪一样的女儿,轻轻抬手将陆建明压在身下的被子抽出,慢慢给她盖上。
她家晚上都有一个来月不熄灯了,只要灭了灯一段时间或者像刚才那样传出一点声响,陆捷就会惊醒,醒了就会闹上半天,还一直不让熄灯。
陆海川临出发前刚打的二斤煤油基本全点完了,张云凤被孩子闹得哪里顾得上再心疼煤油,只要孩子好了就是点上二十斤煤油她也心甘情愿。
反正今晚她又睡不踏实了,索性就躺着寻思点事吧,“唉,这孩子,点着灯还能睡踏实会,一灭了灯不一会儿就又开始闹。一会睡点一会又哭闹,这可咋办?这深更半夜的,闹得我也心里吓得慌,白天还得干活呢,都芒种时节了,地里又忙,还有那两个不省心的爷儿俩,唉。闹心啊。”
张云凤一会儿在那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在那不出声的寻思着:孩子到底是怎么吓着的呢?那天从地里干活刚回家时,陆捷很听话,怎么到半夜了就哭闹起来了呢,只要熄了灯就哭闹个不停,亮了灯就能睡着。
第二天她曾起来问过女儿陆建明,女儿说是在傍晚时大白鹅无缘无故的突然往弟弟身上扑了一下,幸亏她将大白鹅及时打跑了,要不然非将弟弟扑倒不可。她曾听弟弟说过什么门口有小娃的话,但她没见到就没放在心上,再加上奶奶来找他们姐弟吃饭,没感觉弟弟吓着,也就没详细的跟自己的母亲说。
一开始头两天,张云凤倒也没察觉出异常来,就用她所会的一点叫魂的土法子给陆捷叫了叫,但就是不见好,还是每晚上一有动静就哭闹,晚上发烧不说,白天的精神还萎靡不振的。
张云凤曾开始找人给陆捷看过病,但就是没看好,根据陆捷的状况,陆捷的奶奶及村里一些岁数大的老人都一致认为,这孩子是吓掉魂了。
张云凤找了村内村外的会叫魂的老人,都挨个的给陆捷叫遍了,但结果就是不见好。
“怪了,孩子又不是得病,就是得了病,这医院都确定了他没病啊,难道孩子吓的很厉害,一般人看不好?”
就这样一直点着煤油灯,张云凤胡乱寻思着又艰难的熬过了一夜,中间陆捷像以前一样也惊醒过几回,不过亮着灯,哭闹一会,又被张云凤哄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