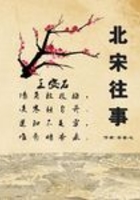且说鲁达三拳打死那镇关西,慌忙逃路,县令捉拿不住,便下海捕文书,四下寻找。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
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连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骤集,车马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鲁提辖正行之间,却见一簇人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
鲁达看见挨满,也钻在人丛里听时。
鲁达却不识字。
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到告官,支给赏钱一千贯文。...”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
拦腰抱住,扯离了十字路口。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金老汉!
那老儿直拖鲁达到僻静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见今明明地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缘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汉遇见时,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见写着你年甲,貌相,贯址!”
鲁达道:“酒家不瞒你说,因为你事,就那日回到状元桥下,正迎着郑屠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不想来到这里。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
金老道:“恩人在上;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寻得一辆车子,本欲要回东京去;又怕这厮赶来,亦无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东京去。随路望北来,撞见一个京师古邻来这里做买卖,就带老汉父女两口儿到这里。亏杀了他,就与老汉女做媒,结交此间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提辖大恩,那个员外也爱刺枪使棒。尝说道:“怎地恩人相会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彀得见?且请恩人到家过几日,却再商议。”
鲁提辖便和金老行。
不得半里到门首,只见老儿揭起帘子,叫道:“我儿,大恩人在此。”
那女孩儿浓市艳饰。
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插烛也似拜了六拜,说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彀有今日!”
拜罢,便请鲁提辖道:“恩人,上楼去请坐。”
鲁达道:“不须生受,酒家便要去。”
金老便道:“恩人既到这里,如何肯放你便去!”
老儿接了杆棒包裹,请到楼上坐定。
老儿分付道:“我儿,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饭来。”
鲁达道:“不消多事,随分便好。”
老儿道:“提辖恩念,杀身难报;量些粗食薄酒,何足挂齿!”
女子留住鲁达在楼上坐地。
金老下来叫了家中新讨的小厮,分付那个娅一面烧着火。
老儿和这小厮上街来买了些鲜鱼,嫩鸡,酿鹅,肥,时新果子之类归来。
一面开酒,收拾菜蔬,都早摆了。
搬上楼来,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筷子,铺下菜蔬果子饭等物。
娅将银酒烫上酒来。
父女二人轮番把盏,金老倒地便拜。
鲁提辖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礼?折杀俺也!”
金老说道:“恩人听禀,前日老汉初到这里,写个红纸牌儿,旦夕一柱香,父女两个兀自拜哩;今日恩人亲身到此,如何不拜!”
鲁达道:“却也难得你这片心,”三人慢慢地饮酒。
将近半晚,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打斗声!三人大惊,慌忙走出门看。只见楼下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口里都叫:“拿将下来!”
人丛里,一个官人骑在马上,口里大喝道:“休叫走了这贼!”
另一边,只见孟浩手持枪棒,正与那二三十人打的火热!孟浩武艺了得,这平常之人如何近得身?
只见孟浩只是三五棒便打翻一人,转眼间便将十多人打翻!
鲁达见孟浩被人围住,不免火气冲天,挽袖便要冲上前!
金老汉慌忙道:“住手!”
只见孟浩并十多人停手。金老汉连忙上前对那官人耳语了几句。那人便教众人退下。
金老汉道:“贤婿,为何与孟恩人打了起来?”只见那官人下马扑翻身便拜,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义士提辖,孟浩受礼。”鲁达便问那金老道:“这官人是谁?素不相识,缘何便拜酒家?”
老儿道:“这个便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却才只道老汉引甚么郎君子弟在楼上吃因此引庄客来厮打。老汉说知,方才喝散了。”
鲁达道:“原来如此,怪员外不得。”
鲁达又道:“孟贤弟,你是为何在此?又是为何与官人打将起来?”孟浩拜道:“哥哥!
小弟护送金老汉至此,便想回去找哥哥,没想在半路见了缉捕哥哥的告示,心想哥哥定是逃去了。我便折路回来,却没想身上没有半分银两,又想起金老汉在此,便去找他。谁想邻居都说金老汉已不在原出,弟四处打听方才知道金老汉在此,没想到来时见一伙人手持枪棒冲进来,小弟担心金老等受伤,便与他打了起来!”
且说孟浩真如他说的如此?
原来,孟浩已知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心知鲁达要来此,便辞别金老汉后在此歇息了几日。今日寻思着鲁达也该到了,便来此找人。
他后面说的却是真的,孟浩来时见二三十人手持枪棒冲来。心里虽知鲁达来的那日会有此景,道还是放心不下金老二人,便拿枪冲将上来!
赵员外笑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孟恩人是什么强人,真是错怪恩人了!”说完,赵员外便要拜下去。孟浩连忙道:“无妨,我也是打伤了如此多人,理应是我不对!”
鲁达道:“你二人不必在此拜来拜去了,既然来了,且来喝一杯!”
二人齐道:“好!喝一杯!”
赵员外再请鲁提辖,孟浩上楼坐定,金老重整杯盘,再备酒食相待。
赵员外让鲁达上首坐地。
鲁达道:“酒家怎敢。”
员外道:“聊表相敬之礼。小子多闻提辖如此豪杰,今日天赐相见,实为万幸。”鲁达道:“酒家是个卤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若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酒家处,便与你去。”
赵员外大喜,动问打死郑屠一事,说较量些枪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赵员外道:“此处恐不稳便,欲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时。”
鲁达问道:“贵庄在何处?”
员外道:“离此间十里多路,地名七宝村,便是。”鲁达道:“最好。”
员外先使人去庄上再牵二啤马来。
未及晌午,马已到来,员外便请鲁提辖,孟浩上马,叫庄客担了行李。径直走了。
鲁达,孟浩自此之后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了五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