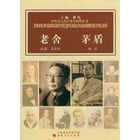10-3万里还家
新疆收复了,可爷爷的故事还没讲完。
“一八七七年四月,清军攻克了吐鲁番,我带着人亲自跑到城里的牢房,一间一间地检查,一个一个人犯地问询,其结果让人沮丧,很多人都不知道此事。我的部下又抓了一批敌军审问,他们都听说有一个清军的提督,后来可能被斩首了。我当时大怒,命人把这几个外匪拉出去砍了。我的心里在流血,‘新满呀,新满,你不是说等我们来解救你吗?’
因为战事紧张,我也无法细查,就嘱咐守军在城中多问,摸索当年捕捉提督之人,定要找出王偏将之下落。
三月,全疆战事基本平息,我心里有事于是又赶回到吐鲁番。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已经找到王新满偏将了,是当地的老百姓把他藏了起来。我连跑带踮的奔向清军中的郎中房,你们知道吗,我是多么想见那个救了自己,又替自己在牢里等了整整三年的新满弟弟呀?
爷爷这时渐渐止住流泪,平静的讲述着兄弟重逢的情景。“当时,我见到王新满,他已经没有了人的模样,就是一副骨架而已。可他的头脑异常地清醒,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哥,新满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你们想不到,这正值壮年的关东大汉,却已经瘦小到十几岁孩子的分量。由于长时间地在水里浸泡,再加上腿上的伤,双脚上的肉皮已经没有了,腰部以下全部溃烂,每次军医郎中换药,看到那秃秃的白骨裸露的双腿,我身边的亲兵们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悄悄问军医郎中尚有时日?回答是或几日,或月余。我毅然决定,要亲自送他回家。你们没有看到当知道要回家的时候,他的眼睛那欣喜的目光是多么的让人······,‘哥哥,你要送我回家?’王新满眨着眼睛,盯着看我。”
黎厚泽向左大人告假半年:“军中弟弟受伤,送回关外家中。”左大人亲笔签发关文碟牌,又让刘锦堂送来白银二百两:“银两虽少,尚能解决燃眉之急,权做路途之用吧。”黎厚泽安排好军中大事,将队伍转由刘锦堂指挥,遂备好马车,只带了亲兵十人,向那几千里之遥的奉天走去。
“那几年,左大人责成入疆清军,要多栽御沙之柳。所以到了哈密,那树就看到很多。我沿途给新满兄弟讲,左宗棠大人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到了兰州,那沿途的杨柳已过了飘絮的季节。官道绿树成荫,坦途无阻。我问新满,你可知那柳树有名吗?新满笑着问我,哥哥你说何名?快快道来。我告诉他,叫左公柳,当时我还给他背了几句别人夸这柳树的诗呢。
十尺齐松万里山,
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
齐唱春风度玉关。
大将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一路上我给新满讲这讲那,新满一直心情非常舒畅。在他那没有肉的脸上,还泛起了了一些兴奋带来的红晕。我指着沿途所见,向他解释着,‘左宗棠大人要求军队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几年工夫,这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清军所到之处,尽要植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新满点头说,真是杨柳婀娜,枝拂云霄啊。”
“新满越来越精神了,每到一处歇息,竟然彻夜不眠,与我长谈。我想:只怕是回光返照吧。因为不愿意再触痛新满,所以我一直不去问那几年的牢中遭遇。你想,在敌人的牢狱里能有什么好呢?可新满却越来越多地对我提起了他的经历。”爷爷讲的越来越平静了,声音也恢复了一开始的洪亮。效罗揉着红红的眼睛,在想:“爷爷是佛,什么没有经见过?这回忆的痛楚,总会过去的。”
爷爷对大家说:新满爷爷的经历,是划在我心头上的刀痕,永远不会愈合的。
“新满对我说,那天你们走后,那几个匪兵听到动静,就喊着‘房上有人,’跑过来看,一看牢里地上还有人躺着,就放下心来了。我们那个亲兵对他们说,将军还在,不要大惊小怪的。亏得他安抚了那几个匪兵,没去张扬,要不,那还真是个危险的事呢。十多天,敌人没有来问话,那个士兵自愿留了下来,在监狱里照顾我。没有药伤口流血不止,他把地上铺的草,拿到外面烧成灰,每天用草灰来封住伤口,就这样,腿伤还好多了。一个月后,敌酋来招降我了。那是一个浩汗国的军官,操着西域浓重的腔调问我,能不能合作?会给我一个更大的官坐。我哈哈大笑,问他,你们更大的官是多大呀?我已是皇家二品提督。那敌酋又问,二品是多大?我用手指比划了一下,除了一,就是二。那家伙看了半天,在那里盘算了半天,摇着头说,你的官太大了,我们这里没有位置了。后来他说可以给我钱,晃着他的鸡爪似的手,多多的,多多的,喊个不停。我问他,想收买我,你有多少钱啊?那小子让人抬出一个箱子,对我说,只要你投降,这里的钱都是你的。当时打开那箱子,一看就是抢掠而来的什么头簪耳环手镯之类。我和他说,象你这样子的东西,朝廷一年给我十箱。那匪官一听眼睛瞪着半天没出气,他在地上来回走了好久,最后向我说,没有办法,只有硬的了。”
后来连续三个月,只要想起来,他们就把新满拉出来拷打一番,无论上火刑,还是拔指甲,新满都一声不吭,那匪酋来了几次,默不作声地站着看他受刑。那个留下的亲兵向敌酋求情:“我出卖了我的将军,现在我要留下伺候他,求你准许。”那个敌酋还真答应了,交代他:“好生伺候吧。”
时局越来越紧,吐鲁番换由叛匪白彦虎防守,这白彦虎大字不识一个,生性残暴杀人无数。一看还有一个清军的提督在牢里,马上下令:“拉出去砍了,留他何用?”那个马人得过来劝他:“一个军官,身已半残,留着万一有用呢?”“那也不能好受了他,扔到水牢里去。”你说这西域缺水,可那大牢里还有水窖,那水牢里的水,都不知是哪年的了,人下去,两只手被吊起来捆在木头上,人在坑里,水到脖子。这一泡就是两年。“亏得那个士兵,一周把我放出来一次,要不就等不到你们来救我了。”我不愿意再提那个曾经背叛的士兵。“提督啊,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可那个士兵用他的生命来洗刷他的过错,也同样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他说的也是道理。“新满继续说着他的经历,就在大军即将攻破吐鲁番的时候,叛匪白彦虎要大开杀戒。白彦虎让手下,把牢里的所有人统统提到城中广场,全部杀掉,还特意的说:“对那个清军提督,我要亲自动手。”
听到要杀人的消息,那个当了狱卒的清兵求那牢里的牢头:“我这哥哥已经在牢里呆了几年了,人都不成样子了,求你救他一命吧。”说完磕头不止,这个克尔克兹族的牢头,一直对这个小伙子非常佩服:“你看他,为了长官把自己留下,又每天去照顾他,多危险啊。”心里很受感动,决定帮他。“不过你放心,他们找这个人时,我会去顶账的。”那士兵向牢头保证。牢头趁夜里把新满转移到一墙之隔的官府院里,“哪里好呢,他们肯定要搜查的。”“这院里有水窖吗,把我放到那里好了。”
第二天,叛匪指名要提督上来,那个亲兵走出去对他说:“我把他放走了,此时已到了清军大营了。”那匪首跳起来一刀就将人拦腰斩断,年轻的士兵笑着:“我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扑通倒在地下。白彦虎在全城搜查,翻了遍,也没有找到个人影:“看来这城中奸细不少,快快撤退。”他连同伙马人得都没告诉,自己先跑了。清军入城后,牢头吓得不敢出来,隔几日给新满送点吃的来,又过了几个月,才把他从井里拉出来,运到城外他亲戚家:“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你也看不了病。”“你把我送到城里的军队那儿就行了。”牢头想了半天,没有做声,新满知道他害怕,就说:“你放心,要不找几个人趁夜里把我送到他们门口。”“好吧。”临走时,这牢头伸出大拇指:“清军都是好样的,没有孬种!”新满知道他在说那个死去的,竭力用鲜血洗刷耻辱的士兵。新满也举起大拇指来:“提督哥哥,那个士兵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进了北京城,黎提督到兵部衙门签了到,顺便打听了一下僧王爷的府第,王新满和黎厚泽都想要去看看。他们远远地望着,就见那朱红的大门外,那对狮子还是那样威武挺立着。黎厚泽心中念叨:“愿僧王在天上,再无奔波之苦啊。”离家越近,王新满越精神,在京城一宿,他说出了心中的愿望:“提督哥哥啊,我家乡的山上有一个青岩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从小我就在寺里进进出出,那佛就象我的母亲。其实,我很早就想出家,去伺候观音菩萨。她大慈大悲的形象无时不在我心中。”“那你怎么又从军了呢?”“后来我想,这是菩萨在磨练我筋骨,考验我意志吧。”没想到那王新满对佛学知道的真多,有些还大段的能背下来。“我这里有一本经文,是宋代的,哥哥你要看看才好。”黎厚泽把书接过来,哪里还有字啊,早就泡的剩下残缺不全的几页纸,留着黑色,红色,黄色的印记。“佛在心中。”新满看着黎厚泽,眼睛里放着光彩,他又说了一句“佛在心中,”就不言语了。从京城出来,新满就不停地问:“提督哥哥,东海里的普陀山你去过吗?给我讲讲好吗?”当他看到黎厚泽提督在摇着头时,失望的样子真让人心酸。黎厚泽马上说:“老弟,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好吗?”王新满又兴奋了:“好,咱们一言为定。”
北镇到了,医乌闾山脚下,王屯。黎提督提前派亲兵到王屯的家里通知了家人,屯里二百多口全来了,在那村口候着,人们不知道这王新满是怎么回事,只以为衣锦还乡,要热闹热闹,那唢呐,喇叭,小鼓,就响起来了。一生难得几回掉眼泪的黎提督,心酸的:“这还折腾什么呀,没看那···”可他不能说,全村的人都在磕头,迎接新满归来,因为这王屯他家的辈分最大。然后回到关帝庙,那王新满还坐起来了,对着关老爷点了三下头:“原谅了吧,咱们都是战袍加身,弯腰不得。”回到家中,新满把家里的人都叫来,向大家说着:“这是黎厚泽提督,也是我的哥哥,就是你们的大爷,亲亲的大爷。”王新满看着地下跪着的孩子孙子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次日早上,王新满离开亲人走了。他没留下其他的话,全家人都记得:“这是你们亲亲的大爷呀。”黎厚泽没有掉泪,他里外的忙着,看着王新满那穿着孝服的一家人,不由地叹着气:“我虽然尽力了,可我永远对不住他呀。”
黎提督决计在山上青岩寺里,为王新满作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然后再做返回兰州的安排。他脱去官袍,素服青鞋的在青岩寺里呆了四十九天,为亡弟祈祷。每日随着那晨钟暮鼓,和着住持老和尚的诵经,他只感觉到是那么的惬意。那些法事上的经文只要一遍他就全记住了。“将军,你的悟性如此之好,真是难得啊。”老和尚对他说了又说。在这佛堂里,他忽然感觉到心里异常的宁静,再也没有马蹄的喧嚣,也没有刀枪箭戟的杀戮。这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熟悉,象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连那寺院供佛的悠悠香味,也好象是闻了许久,沁入了肺腑。再看那地上的圆圆蒲团,盘腿坐上去,是那么的合适啊。终于他听到自己心底里有一个声音,由小变大,由混乱到清晰:“留下来,这里是我的归宿,我应该属于这里。”
黎厚泽做完七七四十九天法事之后,他终于大彻大悟,平静地向几个亲兵宣布自己要剃度出家。“那,那,我们咋办那?”“你们选择吧,把我的官碟度牌,到京城给兵部交回即可。”亲兵们商议了半天,有六个留下来了,他们说:“我们的命都是提督给的,我们就在这里陪他一辈子。”还有四个士兵也没有再回军中去,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
爷爷的故事讲完了,冯麟阁这个从不流眼泪的人,眼睛红红的,背过人去直咳嗽。效罗的父母带着家人,又一次的向爷爷磕头,效罗自言自语的说:“爷爷呀爷爷,您就是我们王家的大山呀。”看着家里人一个个泪流满面,爷爷告诉大家:“我又提起那往事,这让大家都伤感,可我必须告诉家里人,去普陀山,这可是新满爷爷的心愿呀。”爷爷从怀里掏出那本无字的佛经,轻轻的用手抚摸着它说道:“爷爷五十岁遁入佛门,一晃已经三十三年了,这回,我们老哥俩要一起去普陀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