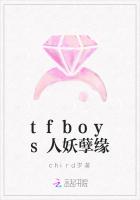政君闷闷不乐,本想来找苟寻问清楚阿母的事,没想到遇到了个泼皮。
这泼皮还是个有地位、有学问、有君子之风的泼皮。
短短半个时辰,温厚的大表哥便将其引为好友了。
政君觉得她不仅是因为被取笑牙还没长齐才生气,更因这个外表光鲜、内心狡猾的泼皮赢得了大表哥的好感而生气。
李汤浑然不觉,还在和苟寻兴高采烈地讨论回去后多练练射箭,免得和淮阳王一起打猎丢丑。
政君垂着头,往马车走去。
苟寻看了看她,快走几步跟上道:“君儿妹妹,汤哥说你找我有话说。”
她点点头,无力地说道:“苟寻……寻哥,你上马车来吧,我……找你有事。”
李汤愣了一愣,不知自个是该留在马车外,让表妹和苟寻好好说话;还是一起陪着表妹,毕竟……他很不放心。
苟寻看他这般,在心里叹了口气道:“汤哥一起上来吧。志哥和崇哥都在斗狗场,不会有事。”
李汤闻言,浑身一轻,也随着上了马车。
政君看着苟寻,却又不知道从何问起,是她叫苟寻想法子让阿母嫁给苟叔。
苟寻办成了,但她又为这样的阿母感到委屈,可这份委屈,对着苟寻说出来好吗?阿母要嫁入苟家做苟家妇,她不能为阿母惹来麻烦。
车内一阵沉默,李汤正想咳嗽一声打破这令人压抑地沉默,苟寻开口了:“你是担心我利用这件事,叫你阿母嫁得委屈了吧?”
政君闭了一下眼,表示苟寻言中了她的心事。
“君儿妹妹,我阿父一直钦慕你的阿母,想必你也清楚。你也不是一直想撮合他俩成亲吗?为何事情成了却又如此?”苟寻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阿父为了李氏,处处谋划,宁愿什么都不要了。政君还觉得委屈,那么他的阿父就不委屈了么?娶一个心中永远有着别人的女人,真不知何苦来着。
政君低下头去,她不知怎么解释。
“苟寻,我希望阿母是开开心心地嫁给苟叔的,而不是迫于……”
“哼”苟寻冷笑一声,看都不看她一眼,冷声道:“我阿父再三叮嘱我们兄弟两,要把你们的阿母当作自个的母亲。
自古以来以孝治天下,我们自然会尊敬侍候后母。但阿父也要我们把你们当作亲兄妹。
阿父做了这么多,你难道看不到吗?你又凭什么说你阿母迫于无奈才答应嫁给我阿父?
若是你阿母不愿意,她不会答应出嫁。
王政君,我竟不知你是这样的小娘子。用得着别人时,就千好万好;用不着时,就觉得委屈起来了。
你阿母就算是为了你和你阿父才答应再嫁,你又有凭什么替你阿母觉得委屈?”
政君脸色苍白,手脚冰冷。
苟寻说的正是她的痛处,是她和她阿父愧对阿母,而不是苟叔和苟寻。
那怕苟叔是趁机圆了自个的梦,那也是阿母她自个同意的。
苟叔那又不是火坑……。
她没有资格和立场去质疑苟寻的行为,反而他们一直在帮助她家解围。
看着苟寻那冷冰冰的模样,她不知道怎么挽回这个场面,不能让苟寻在心里种下对阿母的一根刺。
她越想越急,说不出话来,又开始哭了起来。
李汤瞪了苟寻一眼,忙忙为表妹拭泪,政君靠着他,哭的更是一噎一噎地。
苟寻毕竟是个少年,见不到小娘子落泪,脸色渐渐缓和下来。
马车里只闻政君的抽噎声,好一阵才停了下来。
政君缓缓起身,也不修饰自个地狼狈,对着苟寻施了一礼,声音中带着哽咽道:“苟大哥,今日这番均是君儿的错。君儿不该因内心对阿母有愧,怨怪于你。”
她想了想又说:“苟叔对阿母也是极好,只是君儿总是放不下阿母。请苟大哥莫要往心里去才是。”
苟寻脸上有些不好看,忍了忍道:“我自然是不会怪你的,你也无须多心。”
政君明白,苟寻一向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她没有说出来的话,她在求他莫要因此对阿母不喜。
她不再解释,点了点头。
李汤递过来一只帕子,政君脸红红地也不敢看表哥,接过来擦了眼泪和鼻涕,又将帕子掖进袖袋里,打算带回去好好洗洗再还给大表哥。
苟寻见她如此,眼角浮过一丝笑意。
李汤连忙打着圆场道:“寻哥最是个好说话的,又聪明,上次你阿父的事,他也帮着出了不少主意。”
政君脸更红了,她想起苟寻说的:“用得着别人时,就千好万好;用不着时,就觉得委屈起来了”。
她连忙说:“那日王义连夜带话去舅家,等到中午才带话回来,我还以为……,心急了一宿,陪着阿父说话,后来竟和崇哥睡在了阿父的书房。”
她又瞄了瞄苟寻的脸色,轻声说:“苟大哥,谢谢你和苟叔。”
苟寻笑道:“谢倒不必了,只是母亲今后多给我们做几道菜便好。上次汤哥带给我们的青蒿饼、鱼脍,成哥一直记挂着。”
政君又有些难过,以后阿母就不只是他们三个的了。
她的眼中浮现出大哥那萧索的背影,大哥也是同样难过的心情吧。
她强笑着说:“今后我们就又要多两个兄弟了。”
苟寻觉得马车中始终有着一股沉重的氛围,便找了个借口出去了。
政君身子一软,靠在表哥身上,低声道:“大表哥,我……我很自私吗?”
李汤笑着拍拍她:“表妹这么好,怎么会自私呢?只是听到姑姑要嫁人,担心她罢了。苟叔对姑姑一往情深,不会辜负姑姑。阿父和阿母都一直看好苟叔,姑姑会过得比以前畅意的,她这几日也在准备嫁妆呢。”
政君听着大表哥温和的劝慰,她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便想和表哥们一起去舅家见阿母。
她不愿再回到书房跟着阿父读《尚书》,虽然知道迟早有那么一天,但她不愿这么早便面对阿父的失落。
阿父和阿母相拥着站在堂中,微风轻轻吹起他们的衣摆,玄色的深衣和红色的纱裙交缠在一起,这是政君心中最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