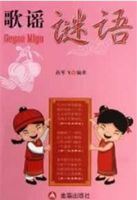八
东江县城,伪满洲国北方重镇,坐落于两山夹一川的地势之间,长宽十几里的面积,砌着高大城墙,城楼上插着太阳旗。城内街道十余条,人口四万,日伪军二千八百余人。兵工厂,医院,中小学校,商埠一应俱全。一条公路南北向穿城而过。
与平时一样,城门口,日伪军例行检查过往行人。
城内,堆在路边的积雪,满目灰色的砖墙,衣衫褴褛的乞丐,三三两两的行人,还有小队巡逻的日军,一身黑皮狐假虎威的伪满警察,典型的日伪统治时期的景象。
东江县初级中学操场上,穿着学生装的同学们,在嬉戏,走动。
穿灰色棉长袍,戴一副近视眼镜,梳分头,眼角和额头布满皱纹,年逾五十的校长马文升,站在校门口摇铃,“叮当!叮当!叮当……”清脆的铃声划破天空的沉寂,飘向远方。
初二(1)班教室,同学们静静等着老师的到来。
校长马文升手拿教材走进教室,转身关门。
同学们交头接耳。“这节课怎么校长来了,桂花老师呢?”
“起立!”班长张二龙喊道。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
一双双渴求答案的眼睛。
“同学们,马桂花老师昨天递交了辞呈,到省城另谋高就去了,以后她的课,就由我来讲,直到有新的课任老师来接替。”马校长放下教案,看着同学们说。
“桂花老师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是他爹,你能说说为什么吗?”张二龙甩了一下盖子头,皱着眉,满脸的疑惑。
“同学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更光明的未来。桂花老师走的时候,给你们留了几句话,张二龙,你来给大家念念吧。”
马校长从课本里拿出一页信纸,递给走上讲台的张二龙。
同学们静静地听张二龙念信,内心深处仿佛听见桂花老师亲切的声音。
“亲爱的同学们:一晃,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两年了,这是我走上教学岗位,最最开心的两年。在你们眼里,我看到了你们泉水般纯净的心底;看到你们心中那片澄澈明媚的蓝天;看到了你们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同学们,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你们是山野荆棘中盛开的小花;是风霜雪雨中挺拔屹立的劲松。而我,只是携来雨露滋润原野的疾风,我要去汇集起更大的力量,驱散天空的乌云,让苍茫大地阳光照耀,让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美丽的祖国,善良的人民,崇高的民族图腾,需要我们的努力,需要我们的坚强,需要我们忘我的奋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与民族之魂同在。
永远想念你们,爱你们的——马桂花。”
桂花老师的突然离开,同学们倍感意外和失落,长吁短叹和失望之声不绝于耳。
张二龙对桂花老师的仰慕和崇拜,是从一年前开始的。
县城的街道上,算卦测字的摊位间,有摆象棋残局的,破了摊主的残局,可按约定获得赌金。
张二龙酷爱象棋,每每上日语课,他都要溜出教室跑到棋摊上,与摊主一决高下,直到输尽兜里的零花钱。他太喜欢这副象棋了,一个个像小月饼,拿在手里的感觉是那么让人想咬上一口。一日赌兴正浓,被路过的马桂花看见,拎着脖领子薅起来一顿训斥。
马桂花原是俄文老师,后来又兼音乐课。人长得出水芙蓉般俊俏,乌黑的短发,一双弯眉,笑眼温和,白净的面庞充满青春的光泽。
马桂花比张二龙大不了几岁,但在张二龙心里,却有着一种因人而异的师道尊严,他不敢和马桂花顶嘴,也不敢嬉皮笑脸地软扛,那是一种大男孩特有的心理。
“回去上课!”马桂花温愠道。
张二龙指了指摊主说:“我书包,输给他了。”摊主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
马桂花噗嗤笑了:“我今天要是不来,你恐怕要光着屁股回家了。”
“不会,顶多穿着裤衩回去。”二龙辩解说。
“你还知道羞耻。”马桂花低头问摊主,赎回书包要多少钱。摊主说两块大洋。
“什么?我输给你抵债是两块法币!”二龙忿忿不平道。
摊主一笑:“书包是我赢的,卖多少钱当然是我定价。”
马桂花说:“行,我跟你赌一把。”
二龙气急地问摊主:“你拿什么押啊?”
摊主拿着折扇按着棋盘说:“就把我这摊儿押上,如何?”
“你这破摊儿半块大洋都不值!”二龙蹙眉瞪眼争辩道。
马桂花坐到棋盘前看了看棋局,说:“行了,开始吧。”
四五步,摊主招架不住,半天不敢挪步,张二龙催促道:“走啊,棋子儿喝面汤拉浆糊粘住啦。”摊主还是低头不语,“你倒是快走啊!”二龙不耐烦了。
“我这步走错了,缓一步。”摊主说着就要悔棋。
“诶?江湖规矩,认赌服输。”二龙伸手按住棋子。
围观的看客也都嘲笑摊主耍赖,摊主无奈,抬起头擦了擦脑门儿的汗:“好吧,我认输。”
二龙不由分说,端起棋盘将棋子倒进书包,拉着马桂花就走。
摊主沮丧地一脸落寞:“这女先生还是个高人。”
自此,张二龙总爱粘着马桂花下象棋,对马桂花是言听计从。
张二龙无心上课,乘马校长在黑板上写字的空档,从后门溜出教室,他要去找桂花老师问个明白,好好的为啥要离开学校。
坐在前排的小胖子洪立晨,扭头看身后的美惠子时,发现张二龙逃学了,也想起身溜出去,马校长忽然转过身来,看见站着的洪立晨问:“洪立晨,你怎么啦?”
“先生你看,张二龙跑了。”洪立晨一指窗外。
马文升快步赶出去,在门外喊张二龙,只见二龙背影一闪,溜了。
美惠子瞪了洪立晨一眼“叛徒!”
洪立晨道:“这叫调虎离山。”说罢,闪身到教室后门,盯着马校长转身的机会,窜出教室,追赶二龙去了。
马文升回到教室,见洪立晨也没了,叹了口气。
马桂花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源自于她能放下老师架子,对学生如兄弟姐妹,且和蔼可亲。马校长很奇怪,女儿喜欢调皮聪明的孩子。他也清楚,像张二龙洪立晨这样的,将来必有建树。
根据伪满洲国的要求,学校设日语课,由于一些学生的抵触,每一届毕业生日语水平都不尽人意,县教育局频繁更换日语老师来任教,效果甚微,日语课经常被学生们搞成娱乐课。
一天,男日语老师见课堂实在待不下去,夹起教案回了办公室,把教案往办公桌上一摔,气哼哼地说:“教不了了教不了了,简直瞎胡闹嘛!”
有老师看着他捂嘴笑。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找校长去。”日语老师转身出门,被一旁备课的马桂花叫住。
她走上前,从日语老师后背摘下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汉奸走狗”,下面还画着一条抬腿撒尿的狗。她一看就知道是张二龙的杰作。
“这,这太不像话了!我不干了,在哪不能养家糊口。”
老师走了,课程又不能取消。教育局督察长来到学校,在全校大会上大讲日中和谐友善,遭到全校学生起哄抵制。
督察长在校长办公室给马文升施压:“日语课必须上,期末考试不及格率不许超过10%,否则,你自寻出路吧。”
马文升无耐,只好准备自己带课。初二(1)班也确实让他感到头疼。
马文升早年在义勇军中当文书,后来部队打散了,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当了小学教员,后与战友杨沂清组成家庭,生了马桂花。女儿天资聪颖,备受夫妇喜爱,寒来暑往,长大的马桂花,思想受父母的熏陶,无产阶级意识渐渐形成,并多次配合母亲完成情报传递任务,后来便加入了我党地下组织,成为一名交通员。
马桂花回到家的业余生活,除备课外,就是和父亲下象棋,十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见父亲拿着棋谱在摆棋局,于是坐到父亲对面和他对弈,走出几步后她对父亲说:“学校的日语课还是我来教吧,毕竟全校看(1)班,(1)班看二龙,他在我面前,还是比较听话的。”
马文升不解:“这个张二龙,自恃爹有势力,不把学校放在眼里,你是怎么拿住他的?”
马桂花笑笑说:“张二龙喜欢下象棋。我帮他从棋摊上把书包赢回来,他就崇拜死我了。”
马文升:“这小子太没志向。”
马桂花:“他对日语课强烈的抵触情绪,代表着绝大多数同学的反日心理,我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
“这孩子贪玩,思想还不成熟,要慎重引导,循序渐进。”马文升叮嘱道。
“我知道。”
马桂花在学校成立了一个象棋兴趣小组,张二龙任组长,七八个组员都是象棋爱好者,下棋的乐趣让张二龙感觉生活充实,马校长不失时机莅临指导,使张二龙对马氏父女的棋艺更是钦佩之至。
马桂花循循善诱地对张二龙说:“下象棋,我们懂得学习对手的长处来提高自己,战胜对手,学日语也一样,我们学会了日本的语言文字,就能更好地学习掌握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为我所用,你为什么不愿学呢?”
张二龙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没想那么多。我保证,日语课一定不捣乱,好好学。”
张二龙来到马桂花家院门外,想悄悄看个究竟,洪立晨在身后捅了他一下,下了他一跳。
“你个跟屁虫,离我远点!”张二龙瞪了他一眼。他上学晚,比洪立晨大一岁。
洪立晨笑嘻嘻地双手操在怀里,歪着脑袋说:“桂花老师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没带全班同学过来,是给马校长一个面子。你班长了不起啊,有本事别偷着跑出来啊。”
“滚远点!找揍啊。”张二龙板起黝黑的面孔,举起拳头。
洪立晨不慌不忙从领口捻出一根银针,足有五寸,平静地看着张二龙:“来,打我啊,你不出手就不姓张,来啊,敢动老子一下,不让你瘫炕上三天我不姓洪。”
张二龙更了更脖子,挠挠头,他知道洪立晨他爹是江湖郎中,祖传邪门手段,****兼治,他亲眼见过洪立晨他爹给一匹见人就踢的疯马扎了一针,那马立刻俯首帖耳乖乖听话。
“老子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你少凑热闹!”张二龙放下拳头说。
“老子还就……。”
“哟,你们俩不上课,跑这来干什么?”机警的杨沂清停下手中裁剪的活,走出房门向院门走来。她宽宽的额头,头发有些稀疏,一双慈祥的眼睛看着二人。
“大,大婶,我来看看桂花老师走没走,同学们都舍不得她。”张二龙摘下帽子,不自然地攥在手里。
“谢谢你们惦记她。”杨沂清笑着说。
“桂花老师去哪了?”洪立晨问。
“你们就别问了,我想啊,总有一天你们会再见的,回去上课吧。桂花老师要是知道你们逃课,也会不高兴的。”杨沂清笑着说,转身回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