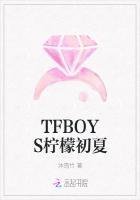韩记粮铺粮仓旁的休息室内,此时亦灯火通明,一个身穿青衣小帽的家丁端坐在一张胡床上,胡床之下,跪着两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休息室很空,除了一张粗木的大床,就是一张做工粗糙的胡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量斗、秤之类的用具。
“去了四个人,就你们两人回来了?”家丁国字脸,面庞黝黑,满脸的胡渣子,厚嘴唇,端坐在那儿,虽穿着青衣小帽,却有着无匹的气势。
“启禀传教大人,李辉原本想在秦家来人之前就刺杀那姓张的小子,可惜秦家人来得太快,他便准备伺机刺杀那小子,只是,秦太守实力太强,最后他以身殉教了!”
“李辉且不去说,尹护教怎么死的?”被称为传教的男子粗壮的手指拖着下巴,他咂摸了下自己的短虚,“尹护教的武功心智都不差,即便是真遇着强敌,也该逃得了性命才是。”
“尹护教见李辉殉教,便潜伏在那姓张的小子屋内,准备一举击杀他,他说,这么做,一来是为了给他人以震慑,二来,是为了为李辉报仇,免得寒了教内兄弟的心。”
“那小子是个高手?”传教眼神一凝,眉头也拧了起来。
“不是他,是那漂亮的不像话的娘们儿,江半月。”
“什么?是她?”男子一拍胡床,从胡床上站了起来,“早前听说秦朗和她交过手,虽然被秦朗遮住了实际情形,但她能从秦朗手中全身而退,想来必不简单,难道她也是官府的人?”
“想必是官府中人,不然,她根本不可能将尹护教一招毙命,也根本不可能是秦朗的对手。”
“一招毙命?你是说尹护教被她一招毙命?”
“是的,传教大人,而且那一招,我根本看不清。”
“这……”那传教倒吸了口凉气,的确,如果这江半月真有这等实力,那她要杀自己,也是易如反掌,看来,这宁州城虽不大,却藏龙卧虎,自己在此地主持本地教务,实在是举步维艰啊。
要谨慎,这是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念头,这次的行动自己行事鲁莽了,下毒之后秦家有人救治便让他救治便是,说起来,下毒只是一招闲棋,能成自然是好的,但秦朗既然拒绝了,那自己就应当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次机会,可是自己却为了这招闲棋将教内的一员大将折在了半月书院,而且,此举可能给自己和圣教带来很大的麻烦,实在是得不偿失!
圣教之中,有仇必报,但是,尹护教的仇,自己只能先放到一边,惹怒了姓江的那娘们实在是后果难以预料,这仇只能待有机会时再报,毕竟武力不能决定一切,她江半月也一定有软肋,她也一定会落在圣教手中,到时候让她生不如死!
“你们二人下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做任何事情。”传教又复坐于胡床之上,扬了扬手。
“是,传教。”
月已偏西,月光却越发明亮。
太守府中的家丁婢女们依然没有散去,毕竟,家主、老夫人和夫人都在守着少爷,自己这些下人若真的散去睡觉,那可能第二天就被管家扫地出门!
主卧内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随后又是哇哇的两声干呕。屋内传来一阵欢喜的惊呼。
“哎哟,我的乖孙唉,你终于醒了啊!”老太太一把扶住趴在那干呕的秦源。
一旁的秦朗和秦夫人也满脸喜色,关切的看着自己的这根独苗。
“奶奶,我这是怎么了?我好难受啊。”
“你中毒了!”秦朗马脸一板,“早让你在家吃饭,就是要去外边吃,要出去你也要去杨楼那些地方,你是我的儿子,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害你!”
“有话不能等源儿身体好点再说?”秦夫人本来堆满笑意的脸顿时挂了下来,“你真是要逼死孩子吗?还是要逼死我?”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孩子在外边吃饭,我多少次让他小心,偏偏不听,这次若不是那小子会医术,我就会被妖人要挟,你到底懂不懂?”
“什么?妖人?什么妖人?”老太太将孙子重新扶到床上,听自己儿子说妖人,她有些差异,也有些惊诧。
“有人冲着我来得,下毒就是为了要挟我。”
“父亲,下毒的是李记馒头铺,不是什么妖人啊,我要杀了那个姓李的!”秦源面色苍白,嘴唇干燥皲裂,浑身没有力气,“我只不过想在他们铺子分些红利他居然不肯,还下毒害我!”
“蠢东西!你老子我是宁州太守!要什么没有?跑去分什么红利?不论是官场商场上,多结交些有用的朋友!”听着儿子走气似的嘶吼声,秦朗心头火一下子就串了上来,“还有,不是李老板下的毒,这宁州不是你一人中毒,他家一家数口也都被毒倒了,没有人为了报复别人会将自己的事业毁掉!以后你给我老实点,老子的仇人已经够多了,别在给你老子我添乱!今天要是张仓曹的弟弟,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张玄?”
“是的,是那小子给你治的毒。”
“他?他什么时候会治毒了?”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秦朗拳头一砸墙壁,“有人想用你来威胁我,如果不是我的身份和能力,如果不是季院君帮着劝说,如果不是你奶奶低声下气的求人家,你以为你还醒的过来吗?”
“什么?就那小杂碎敢让奶奶去求他?老子非弄死他不可!”
“弄死他?事到如今你还想弄死他?现在他成了你秦源的救命恩人,成了季院君看重的人,成了半月书院的教书先生,你还要弄死他?有那么容易还等到你来在这里吆喝吗?”
“爹!那,那就这么算了?”
“算了?算不了……”秦朗眼睛眯缝着,马脸满是扭曲。
……
张府的院落是张自天自己购置的,长白街的院落虽多,但逐年替换的官员有些却不愿意放手居住多年的老宅,故而,类似于张自天这样的年轻官员,很少有人居住在宁州的权利中心——长白街。
好在年轻官员购置住宅,朝廷补贴不少,张自天便是在云台街购置了一间大宅,云台街不是权宦的聚集地,却也是一些新近富商的居住之所,处地幽静,距离繁华的街面也近,只不过离官家办公的地点略远了点。
此时的张府,下人都已经下去歇息了,在大堂之上,之站着张自天夫妇二人。
“小玄怎么能这么不给你面子?”张夫人满脸幽怨,“这小子忘了咱们家对他有多好了?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哪样不是我们家供着,我们家对他和咱们家辉儿可曾有差别?”
“他在怨我,怨我没有帮他。”张自天眨了眨眼镜,长叹一口气,“那时候我在气头上,现在想想,他怨我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是他亲哥啊。”
“不是你不想护他!是你根本护不了他!”
“话虽如此……唉——”张自天很烦躁,其实他挺喜欢这个弟弟的,也却是觉得有些对不住他,至于今日之事,若不是被张玄当时的态度所刺激以及江半月在那里看着,他也不会生那么大气。
“父亲,您见着小叔了?”就在这时,张辉像个小牛犊子从大堂的侧门跑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