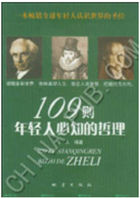草丛开始沙沙作响,营帐边葳蕤的树枝相互摩擦,夜空失去了平静的蓝色,呈现出一片青灰,浑浑浊浊的,虫鸣未衰,风却席卷大地,越刮越厉害,风啸犹如远方神秘的笛声越来越近。
路博德简单修整了一番,在侍卫的引领下走进大帐面见霍去病,无衣早已在帐中,与一众副将们一起迎候他,火光绰约间他逐渐看清了案前的主帅,青年的眉眼更加英武动人,姿态更加从容洒脱,路博德不由内心感叹,距离跟随大将军出征定襄不过两三载,如今的霍去病不再是当年那个一脸倔强、横冲直撞的愣头青的模样,神态更为沉稳清寂,只是眉宇间那份孤傲冷僻,却始终未曾消减,果真沙场才是淬炼能人战将的最佳地方,没有之一。
“太守一路辛苦,塞外苦寒,来不及为您接风……”霍去病边说边抬手示意侍卫奉上杯酒,路博德也不做多余的寒暄推辞,抬手一饮而尽,抱拳正欲向他行军礼,却被霍去病止住,只听得他朗声道:“太守不必拘礼,太守跟随大将军征战多年,论军功或是资历辈分远在我等之上,我不过虚领了将帅的头衔,才位居大人之上。此番射声校尉重伤,军中少了识途辨路的将领,舅舅这才请了大人驰援,还请大人不吝赐教,不负大将军嘱托。”
路博德心下讶异,见霍去病只顾言大将军,却只字不提甘泉宫诏命,诚然临行时大将军确实有特地嘱托他道:“去病年少骠锐,果断有余但思虑不足,我恐他一味求胜心切不顾章法,你权当自己是识途老马,凡事压他一压,务必促成他三思而后行。”言辞恳请而真挚。路博德深知大将军脾性,绝不会以身份强压,只从他含而不露的眼神里,路博德体味了几分凄楚。将他从右北平紧急调往河西的,却是陛下的一封诏命,但见主帅绝口不提,路博德到底是混迹军政的老江湖,心下隐约感到一丝怪异,但也绝不至表露出来。
无衣一五一十地将来时路上的若干细节逐一禀明,大行如何嘱咐尽量不向甘泉宫频繁详细传递军报、调集粮草辎重的过程,乃至路上遭遇休屠王太子今日磾的围击,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时侥幸逃过一劫,听得李敢和赵破奴都长舒了一口气,赵破奴说:“你小子真够玩命的,这么陡的长坡你也敢骑着的青龙,方才我查看了一下青龙的嚼口,着实被拉出老长几道血口子,蹄掌怕也得要重新打了。”
“保命要紧,十多个匈奴壮汉围着我们俩个,不跑就得死。”无衣争辩道。
“那个王太子当真与你这么说,我原本以为匈奴人嗜杀成性,从不留活口,居然会有人说得出‘以多胜少,胜之不武’这番的话,我敬他是条好汉。“李敢道。
“是了,关键是那个王太子说的是汉话,说德忒流利了,如果不看清他的面貌装容,当真还以为是汉人。”无衣惊奇道。
“这么说,大行当真嘱咐咱们不报军报?”霍去病突然发话,得到路博德和无衣一致点头回应,他的眉宇间隐约蒙上一层隐忧:“昔日我带兵在外作战,时常被陛下责备说我疏于汇报,不让他及时知晓军情战况,如今却被授意尽量不报,莫非甘泉宫有变?”
路博德只道自己接到诏命便及时出发启程赶往金州,并不了解甘泉宫内的异动,霍去病低头思忖片刻,说道:“算了,将在外军令不受,后方的事还轮不到咱们操心,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追上两王的主力,听闻降虏们供出如今休屠、浑邪两部主力已在西面贺兰山北麓集结,欲与我军决一死战,既然你们路遇路遇休屠部王太子护送祭天神器,与降虏们的供词不谋而合,我意已决,大军即刻开拔,西进追击二王决战,诸位意下如何?”
霍去病四下环视了案下的副将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孔在火光的照映下熠熠生辉,神色坚定而决绝,散发的虎虎生气令见惯了沙场生死的路博德都难免在心中感叹“后生可畏”,“只不过……”无衣忍不住插嘴道:“咱们的粮草都还么没到……”
“管不了那么多了,朝不虑夕,当下草原上天气变幻无常,我们不能为了一点粮草把自己困死在原地,这一路上没有后方粮草辎重也没见把咱们饿死,只要打了胜仗,什么吃得喝的没有,军情大过天,咱们要分得清主次。”霍去病平静地说道。
那你还把支回后方请求粮草支援干嘛?无衣只得闷在心里腹诽,他料定君侯不会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从后方赶回军中,怕是打好了算盘,大行会将他留在后方护他周全,君侯也可以彻底甩脱掉自己这个小跟班。这种“卸包袱”的小伎俩可瞒不过小爷我!无衣的思绪逐渐开始外飘,身随心动不自觉的翻了个白眼。
“你那是什么表情?!”霍去病怒声呵斥道,“难道对本帅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无衣吓得脖子一缩,小脑袋往下一耷拉,抿紧嘴唇大气都不敢出。
“将军莫动气,无衣年少心性不稳,猴崽子似难免有些小摸小动,将军不必与他置气。”李敢赶紧出来解围,不留痕迹地拉住无衣的胳膊往身后一带。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后方呆的时间长了,又开始皮痒了不成。”霍去病手一挥,转身对路博德道:“太守大人有什么意见吗?”
路博德虽身在右北平,久不近长安朝堂,并不了解霍去病的脾性,只听闻他少言不泄、有气敢任,是眼高于顶全不顾他人体面的一等傲主,眼下却如垂髫小儿般毫无顾忌与下士们斗嘴置气,完全不顾忌当前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着实送令人捉摸不透。路博德细想片刻,开口道:“此前听得休屠王太子提及祭天之礼,据卑将所知,贺兰山北路的沙茨楞高地正是匈奴部落祭天“径路”的掩埋地,匈奴的战前祭祀不仅对天、对地和对昆仑神,还有掌握生死大权的中阴“径路”,休屠王既遣太子将王庭的金人神像护送至“径路”处,敌军集结地势必在贺兰山无误。只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我们不等后方支援而急于冒进,确实要担负极大的风险……”路博德欲言又止,他仔细观察霍去病的神态,见他平静如常,并为因自己一番逆言而动怒,又继续道:“……只是大漠草原气候变化无常,来时我一路观察天象,沉云阴寒,雪沫飘飞,牲畜焦躁难安,卑将断定不出两日恐怕又要掀起白毛风,势必会阻挡我军前进的道路,卑将早就听闻将军行军作战的风格,恐怕是片刻都等不了。”
霍去病听罢,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心想路老儿到底是舅舅的嫡系亲信,战场与官场都混得脸熟,将大将军四平八稳的行事风格有样学样琢磨到了七八分,不明着表态,一番时局分析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把决策权都推给了自己,哪像自己手下一帮愣头青,是非黑白只认一面,一声令下只会热血上头一门心思往前冲——舅舅倒是给他送来了个好“帮手”,令他觉得好气又好笑。
“罢了!”只见他右手端起端起泛着琥珀色流光的夜光杯,左手轻轻揉捏太阳穴,冷哼一声:“即使如此,事不宜迟,明日天亮即刻造饭开拔,与匈奴二王决一死战!”
一块块灰云掠过月前,宛如千军万马般从远山那边由南向迤逦飘来,云层被凉风撕扯成孤零的断片,从月前掠过,投射在宫墙屋檐下层层叠叠的树影,甘泉宫的月夜清凉如水,一声轻不可闻的掩门声,在静寂无声的宫苑内也显得格外明显。
“久未相见,上大夫安好。”廊檐下,曹襄朝着刚从帝的寝殿内迈出的韩嫣寒暄作揖,敬声一言不发地跟在兄长身后,一袭青缎灰鼠褂隐没在夜色中,他微微偏头,青绿双瞳盯着素白禅衣加身的韩嫣,神情颇为无辜。
韩嫣以指抵唇做了个噤声的样子,“陛下好不容易才睡着,千万不可再叨扰。”说罢脸上露出笑意道:“连日来忙于侍奉陛下,无暇与平阳侯、公子敬声寒暄,你们来了几日,竟也不使人通传一声,直到前日里这宫里突出被抓出匈奴探子,才得知你俩从长安赶来此处,还怕被认作是我拿乔端架子不理人。”
“无妨,上大夫侍奉陛下乃是要事,陛下贵体金安,我辈不敢叨扰上大夫。”曹襄笑道:“也不知宫中陡生异变是否叨扰陛下?”
韩嫣抬手拢了拢被夜风吹得抖动四散的灯火,笑道:“哪里,河西战事频传捷报,陛下兴致高昂,哪里有还空去理会那些鸡毛碎皮的小事,听过奏呈便打发卫尉处理了。说起来,陛下当真是小孩子脾性,前阵子战事吃紧,骠骑将军率军伤亡惨重,他急得摔杯踢盏彻夜不寐,如今终于传来捷报,他高兴得拍手作歌,只赞叹说‘有了去病,朕可以安心睡个好觉’,卧高榻不到半刻便已入酣眠。”
“如此一来,上大夫也可喘息片刻。”
“陛下贵体安康,是人臣俯仰天泽鞠躬尽瘁之理,何来辛劳。”一边说,只见仕宦取了药来,他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来,随手取来汤匙蘸药入口,皱眉:“还差三分火候,入口过于寡淡,怕是没有煎透。正经送去茶房回炉再煎了来,千万不要弄得这屋里要气,如何使得。”
仕宦连连称“喏”地小心退下,韩嫣对两人笑道:“天气寒凉,春生万物易引生发之疾,陛下连日咳嗽气喘不平,所以才……”
“是了,还请上大夫多多费心侍奉才是。”曹襄又连连作揖道,敬声兀自地不言语,神色清冷,使人全然不知其所想。
“罢了,倒是那飞水潭边抓到的奸细可有眉目?可曾派人审问查探出什么端倪?可曾寻到什么证物?”
“奸人被俘时悉数服毒自尽,想是训练有素的死士,无从探得虚实,只能再寻机会。”曹襄摇了摇头,继续道:“无奈府上事务繁多,不便在此久留,我等即来向陛下辞行,陛下既已安歇,还请上大夫代为禀告。”
这时,身后的敬声突然开口道:“从长安出发前,我府中突然出了件怪事,还请上大夫帮忙解惑。”
韩嫣听他说得突然,迟疑半分,只见敬声从曹襄身影中的暗处走上前来,他用阴郁异样的眼神盯着韩嫣,一对猫儿眼在颤抖的灯火中愈发显得幽异,韩嫣抬起下巴,一双桃花眼微微眯起,用他惯有的睥睨之姿,冷傲中略带不屑,形色恢复了平日的懒散,他故意拖长音尾道:“哦~难得敬声有此雅兴,但说无妨,也让我凑个趣。”
曹襄已然感受到两人之间流动出不同寻常的诡谲异氛,顿觉浑身不自在,他深知韩嫣在帝身边的地位,自己虽有侯位加身亦不敢有丝毫怠慢,敬声虽极得帝的喜爱,但论资排辈,敬声始终不如韩嫣那般举足轻重。
“年前我府上新得了一只鹩哥,双足赤黄,耳朵小翘,是各中难得的极品,得此珍爱自然要厚待之,每日精粟果物投喂,由一奴子专门侍奉,一天四条炮虫,两枚鹌鹑蛋黄,从无懈怠,只养得毛色纯亮,膘肥体壮后,剪了舌子教习学话,教习过程无所不用其极,这畜生死活不肯开口,以虫诱之,黍麦投喂之,千呼万唤还是不开口。”敬声缓缓道,“尔后灰了心,索性扔在一边不去理睬,另择能言善道的新鸟逗弄,吃食看护自然优先那蠢懒的痴呆癔子,过些时日,那鹩哥突然发声,哀叫不绝,三日后泣血而亡。不才愚钝,始终不知此异像为何征兆,估请上大夫开示。”
韩嫣微微一愣,曹襄分明见他神色稍显冷峻,转瞬之间却又恢复常态,那蹙额挽心之姿,以韩燕的绝世容貌映衬,当真称得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曹襄在心中暗自感叹,又哪里敢显露出半分羡赏,只得低头不语,任由两人你来我往一番较量。
韩嫣笑道:“怕是那鸟雀亦如世人一般有争强好胜之心,专宠之时恃宠而骄,傲性使然不肯屈从,那些在舌尖上酝酿已久却没有说出来的言语,默默吸入腹中。但若是被同类竞抵,经年累月怨气郁结于内,不知何日气急攻心,悉数翻涌而出,哪怕抵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博得主君再度垂青。着实可惊、可敬又可叹。”
这是,风声鹤唳,灯火的光影打在他们身上,如火焰般浓烈,却又是凉的,曹襄望着韩嫣离去的背影,长长输了口气,责怪敬声道:“你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堆无关紧要的浑话,到底想要干嘛?害得我紧张得要命,亏得上大夫当下兴致甚好,居然愿意接过你的话茬论道一番,也是稀奇,换做平常,早就冷脸子甩过来,拂袖而去了。”
敬声并不答他,只是低下头用指尖把玩着腰间的缨络穗子,满腹心事的样子,曹襄早就习惯了与敬声有问无回、自说自话的相处模式,他们虽有竹马之实,但多年之后,曹襄知道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敬声的所思所想,他习惯了直来直往、心无挂碍的生存之道,不像敬声那般多思多虑,久思生忧愤,这是他自幼心思沉重难以释怀的症结,这就注定了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