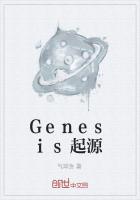你须抱定必死的决心,带着光荣与梦想冲进这片非人的战场,用自己的热血和精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霍去病看着的无衣,不由得皱紧眉头,回想最初在北军营大门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瘦得像根麻杆,脸上身上灰扑扑地满是尘土,夹杂着推搡后一道道血印划痕,眼神明亮而倔强,他已经很久不曾见到如此清澈无尘的眼神。那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与阶位,只是一味地冲撞,固执蛮横地一心投军,报仇雪恨。一个孩子,仅仅只因仇恨之心,便要早早地承受那般暴虐凶险的沙场腥风,与他而言难道不够残酷。那些教养深宫大院内的同龄孩子,哪一个不是一脸天真懵懂地在双亲膝下嘤嘤承欢。
霍去病并没有因此展现一些温情,刀剑无眼,容不得一丝懈怠,趁着刀光血影的间隙,他伸出手按住无衣的肩膀,轻声道:“败三军可用师,胜强敌可智取,但最可怕的、最要战胜的敌人,是你内心的恐惧。”
霍去病的话如指拨单弦,陡然打碎了无衣内心的迷惘与恐惧,在着出离的愤怒与绝望之中,无衣感觉自己浑身的筋肉血脉被怒火蒸腾,濒临爆发的边缘。体内固有的怯意,早在看着英云哥中箭倒地,从马背上重重地甩落在冰面的一刹那,那从伤口喷溅而出的血水将他的视线染成一片猩红。敌军的箭羽从四面八方直射过来,马群已经惊了,开始发疯地嘶鸣,它们不再沿着原有的雪道突围,而是毫无方向的四处奔散,登岸的马群四只铁蹄不停地踩着脚下厚重的雪被,激起一层层翻飞的雪花,冰裂声越来越急促而响亮,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雪湖的一角塌陷下去,那些尚未登岸的将士连人带马滚落下来,瞬间淹没在茫茫雪原中。
“这样不是办法!仆多那边很快就会顶不住了!破奴抢着去增援他,怕是也要陷进湖里了。”前来接应的李敢浑身浴血跨坐在马背上,匈奴骑兵开始围堵登岸的汉军,双方开始短兵相接激烈搏杀,高不识终于带领尚未涉湖的剩余人马从湖边的山谷后方绕行,与李敢的人马会合,马群顺风长鸣,在匈奴人震天的喊杀啸叫声中,汉军陷入空前绝后的绝境。
”不要乱!”霍去病抬起手一声大吼,此刻的危机已不允许他的意志有丝毫转移,回身对李敢和高不识发令:“你们带领余部突围,分散手下部众,越散越好,匈奴人擅长马上群攻,近身单打不是我们的对手!让将士们分散匈奴兵力,近身搏斗!高不识带人去把山面上埋伏的弓弩手给我清了!”仅仅是一瞬间的沉默后,他盯着无衣道:“我下去把仆多破奴他们领回来,你们给我看好了这小子!”
“不行!这太危险了!”两人立即反对,李敢忍不住朝他疾吼道:“湖面随时会全面崩塌,敌人箭雨如此密集,我不能让你去送死!还是我去吧!”说把便要提马前奔,却被霍去病调转马头的迅速拦住。
“这是命令!马上按照我的话做!”霍去病话音含怒,深邃的瞳孔中折射出凶狠的寒光,:“违令者斩!”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用一只手紧紧扶住前鞍桥,另一只手悄悄解开了拴在鞍条上的牛皮筋带,将手中的“和泉”剑柄与手腕牢牢地缠紧,横下心来,快速地把自己从一军统帅转变成决然赴死的勇士,“和泉”的锋刃风雪交加的黑夜闪烁着瘆人心魄的寒光,刃身的菱格纹缝隙里残留着猩红的血污,疾风刮过,刀刃破风发出凄厉的呼啸声。
“不行!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你去!”李敢急了,策马扬鞭拦住浮光。
“成纪,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过瘾地打一场了,你可千万不能扫我的兴。”霍去病形色冷峻地看着前方扬起雪尘,眼睛里开始闪烁着兴奋的精光。
无衣就这样目送他跨着浮光跃入茫茫雪海中,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他已经分不清那到底是谁的背影了,是仆多、是英云、是君侯,还是自己,他的手紧紧握着刀柄,指尖的力量仿佛随时要将这坚硬冰冷的铁器捏得粉碎,他感觉脸上淌过一道道温热的液体,在寒风中瞬间化为雾气,瞪大乌亮的眼睛,任由白毛风夹着一粒粒斗大的雪砂,猛刮向自己的眼睛,激情一阵阵锥心的疼痛,一道道剑雨“刷刷”地落在自己身边的雪地上,直插在青龙的铁蹄边,擦过自己的发梢和脸颊,留下一道道细小的血印。
“小弟!跟上我!”李敢隔着层层雪浪朝自己大吼,无衣咬紧牙关,用尽全力狠狠抽一马鞭,跟上李敢的马一路狂奔。『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与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他回想儿时父亲唱与自己的那首短歌,却始终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此刻真正身处战场的重心,被死亡、伤痛、离别、仇恨、愤怒诸多错综复杂的情绪所包围时,才第一次真正能够体会到那种抛弃胆怯与恐惧,怒火盈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杀入非人的战场的决心和勇气。
青龙在刀光剑影中狂奔的,无衣的脑子里全是金英云的脸——
『如今好酒好肉得可劲儿吃,吃得越饱越好,待渡河之后,且不说还有没有命吃,怕是想这么吃都吃不到了』
『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总像个女人一样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
『告诉你一个秘密,出征前我媳妇其实已有了两个月身孕,按理我是不在征召范围里的,只不过我从军心切偷偷隐瞒了这个事,你可千万替我保密,否则我可就完蛋了!』
『将军在校阅场上对全军各级军官下达演习指令的时候,方能与他打个照面,当然,将军是不会直接与我们这些伍长们直接对话的啦』
他圆润的脸在夜色的火光闪现出柔和的光亮,眼睛笑得弯成一条细缝,嘴角咧起时露出白亮的牙齿,显得他的皮肤愈发黝黑。
报仇!报仇!他迫切需要一个宣泄与突破的出口,此刻无衣的内心除了暴涨的愤恨,依然没有了任何知觉,仅仅依靠体内原始的本能挥刀,砍杀阻碍前行的敌寇,暗红色浓稠的血液层层叠叠地淌过银白色的刀身,一滴滴溅落在雪地上,显出刺目的猩红。
疯狂叫嚣着拥上前来的匈奴兵在一道刺目的白光中无声无息地倒下,头颅和躯干顷刻之间被刀刃划过的光线割裂开来,刀锋箭弩的激烈碰撞声、敌兵临死前发出痛苦的惨叫声、还有那如同野兽般颤栗地嚎叫声,响彻云天。
无衣的眼睛开始充盈血丝,汗涔涔的湿发黏在额前,左臂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使他原本有些涣散的意识逐渐变得聚拢,他猛的转过身,黑云笼罩在他逐渐变得狰狞的面孔上,抓住敌兵还未反应过来的空挡,看准了包围群中的一个空挡,转身一个翻手,刀柄狠狠地砸在敌兵的面门上,整个鼻头一下子被挫脱出鼻骨,被击中的匈奴骑兵滚倒在雪地里,疼得浑身缩成一团,发出凄绝哭嚎,无衣的刀尖径直从他的背心直插入胸腔,牢牢地将他的躯体固定在雪地里不得动弹,少年的狠绝,以及胸腔穿透的同胞渐渐窒息而死的惨痛一面,立即把围在无衣身边的匈奴骑兵震慑住了,而这一幕全数落入不远处包围圈外仍在与敌军浴血厮杀的李敢,他心下一沉,倒吸一口冷气,他太熟悉这样一副面孔了,那股浑然忘我的凶狠与决绝,刀锋嗜血的狂热与失控,仿佛随时可以召唤腥风血雨的暴戾,毫无留情地击杀敌人,冷酷凶残得可令天地为之震颤,他的眼前开始出现重影,无衣的影子与霍去病重合在了一起,惊人的相似。“小弟!快!”李敢一声大吼提醒了无衣,他趁着马群拥挤踩踏的漏洞,拉紧辔头成功跳出了匈奴人的包围圈,寒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温热晶莹的液体流进了嘴里,咸咸的、湿湿的,无衣用马蹄袖擦去冰泪,从身边的同袍手中接过军旗,长风猎猎,此刻他唯一剩下的念头,就是再多杀掉几个敌人。
静静的夜,帐营里一片幽暗昏黄的光,战马悲悲戚戚的嘶鸣声从远方断断续续地传过来,守夜的军士敲着更,绕着营盘一路重复简单而机械的鸣锣打更声。无衣跪坐在营帐前的草地上,眼神呆滞地地上金英云的尸体,他静静地躺在他的面前,眼睛紧闭,面容平静坦然,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灰白的嘴唇上一道道细小的唇纹,在月夜下闪烁着鱼鳞般的银光,酣战过后,风雪尽散,此前那场如炼狱一般的恶斗仿佛只是一场根本不存在的梦境。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晶莹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霍去病站在他的身边,这一次他终于伸出手去轻轻按在无衣的肩膀上,不发一语。透过掌心的温暖沿着肩线的血脉直达他的心底深处,触发了他隐忍已久的悲伤,无衣忍不住放声痛哭,恍惚中,无衣觉得有无数双柔弱无骨的双手绵绵的轻拂过自己的脸颊,那种熟悉的触感引得原本尘封在心底深处的记忆又一次生动鲜活的再现了,无衣抽泣着用袖子抹去脸上的泪,经由自己的手,霍去病感觉到无衣身体的颤抖,感觉到无衣内心最深刻最柔软的部分最惨烈激荡的疼痛。
“仆多的伤情太重,半条胳膊怕是得废了。”高不识神色凝重对自己的主帅禀报伤亡,这一役亡三百,伤四百余人,战马死伤近一千匹。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生离死别,他看得太多,也经历得太多,原本炽热的心魂曾被一道道血痕反复冲刷、浸泡,逐渐失去了痛感和知觉。昔日的战友,出生入死的同胞,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面孔,带着淳朴的笑容,坦白而固执的眼神,刹那间如影子般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好似夜空中一道道转瞬即逝的流星,无声无息地坠落。
“他不能跟我们往前走了,即刻起派人护送他回后方,战死的士兵们就地安葬,让参军和随军医官们逐一诊视,伤情严重者跟随仆多的马队一同调头回去。不能让伤病拖延我们行进的步调。”
一夜之间,青山厚冢之间冒出了一个又一个连绵起伏的坟冢,红巾猎猎,系在坟冢前倒插的钢刀上迎风飞扬,如血色残阳,瞬间之间便是阴阳相隔,那些战死的同袍,臂上紧系的红巾会告知他们的名字,参军们会一一记录在案,发丧回报,举国同悲,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小弟,当初你问我为什么骠骑军的每个军士都是手缠红巾,我没有回答你,现在你终于知道了吧?”李敢陪在无衣身边,看尽红巾满目,苍凉一片。每道红巾都是一个鲜活生动的魂灵,塞外边疆地的莽荒葬地便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其中哪一个,又是英云哥呢?
霍去病看着无衣略显稚嫩的侧脸,眼见他一步步走上自己走过的道路,征战、杀戮、死亡,心灵的冲击与重创,最终会对死亡与生命感到麻木,当初他迟迟不肯允他随军出征,便是不想让他重蹈自己的覆辙。
“我想要你跟随仆多回头,有件重要的差事需要交与你去办。”霍去病对无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