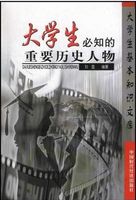北疆方罢兵,国中乱又兴。君臣各算计,同门恩怨起。
暴雨毫不留情地肆虐在每一寸目光可见的土地上,任由自己往何处狂奔,都逃不出它残暴的统治。不断坠落的天降之怒砸向洛熙,豆大的雨滴疯狂拍打着没有遮挡的肉身,在裸露的皮肤上绽放开一朵接一朵的水花,而他却没有任何感觉。漫天的雨幕渐渐平息,视野豁然开朗,然而放眼望去周遭空无一物,无草无木,无声无影,空旷得令人心颤。
乌云散尽后又归烈日当空,时间已然忘记了它的职责,停止了流逝,太阳同样不肯挪歩分毫,霸占着苍穹顶端最为中心的位置。洛熙观察了许久,完全判断不出东西方位,只能像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晃。可无论走了多远,四周都是一片平坦,所能见到的只有沙土和碎石,就连刚才那场磅礴瓢泼送来的雨露也早已干涸殆尽。
脱水造成的乏力感如枷在身,洛熙依然凭皆着本能不断前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到达何处,直到筋疲力尽才停下脚步。不知是疲劳和晕眩带来的错觉还是因为双腿已经无法站稳,他突然感觉的地面正在不停地摇晃,脚边也出现了大片荫蔽,同时身后传来海浪翻腾的声音。回头望去,刚才走过的那段荒路已经化为了浩瀚无边的海洋。
躁动不安的波涛掀起百十来丈的巨浪,气势汹汹地吞噬着阻挡在它面前的一切。在那遮天蔽日的强压之下,洛熙所有的疲惫感瞬间一扫而空,抬腿就朝着尚未被占领的地方跑去,而这头碧蓝海水组成的庞大野兽如影随形,近在咫尺的翻腾声就像催命地魔铃,片刻不离。
一场猎手与猎物的追逐看上去要在漫无边际的土地上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但是上天很快加入了玩弄猎物的行列。洛熙突然发现眼前的路面变得虚幻起来,连忙刹住脚步。这时,路面竟然凭空消失,瞬间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悬崖深渊。
身后汹涌的巨浪还在咆哮着紧追不舍,张牙舞爪的浪花此起彼伏,随时准备把任何落入其中的生灵撕成碎片。洛熙退无可退,便硬着头皮探头向悬崖下面望去,来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生机。但是所见到的只有令人绝望的漆黑以及一阵飘忽不定的迷雾。这阵迷雾在崖间辗转飞翔,最后驻足在洛熙的正下方,悄然消散。
迷雾散尽,黑暗中出现了李承穆的身影。他穿着残破的冕服,捧着血迹斑斑的玉玺,发出了惊悚的狂笑。这笑声在崖间回荡狂散,着实让洛熙浑身发毛,不由得稍稍挪动了一下脚步,而下方的恶灵立刻就捕捉到了细微的声响。他抬起头来,脸上的诡笑清晰可见,遍布血丝的双瞳和憔悴惨白的面容让这诡笑愈加阴森。
“洛熙,快来。”李承穆兴奋地呼唤在这一刻显得格外恐怖,洛熙随即就把头缩了回来,再也不敢直视崖底。可地面上也不尽安全,狂躁的巨浪堵住了除悬崖之外所有的去路,正积蓄着最后的怒火准备碾碎这个渺小的人类。素来无敌的洛熙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害怕的滋味,他彻底被逼到崖边,李承穆像哀嚎一样的呼唤又在耳边响起。
生死之间,最为高耸的那片浪头幻化成了他父亲洛子义的模样,严声厉色地喊出了两个字:“下去!”洛熙脚下的土地应声消失,整个人如同枯朽的树叶般无力地坠入深渊……
洛熙骤然睁开双眼,悬崖和巨浪都已消失不见,自己正好端端地躺在帐中,帐外天色正暗,也没有什么不知疲倦的骄阳。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刚才的梦境真实得可怕,自己如同木偶般浑浑噩噩地四处奔逃,陷入绝境,万劫不复。越想越心惊,困意陡然被驱逐得一干二净,于是少将军索性就起床更衣,披甲佩剑。反正月近将沉,黎明将至,此时为出兵做准备也不算太早。
当他走出帐外时,却看见了一个意外的身影。“夏侯大人起的真早啊!”洛熙想了想,还是上前打了个招呼。“噢,少将军起了啊!”夏侯云转过身来时,疲惫的模样混搭着漆黑的天色以及撩动的火光着实惊悚,把还在噩梦阴影之下的少将军吓住了片刻,误以为自己见到了什么孤魂野鬼:“哦……恩,但凡清晨发兵,我习惯早起准备。夏侯大人,您这是……一宿没睡?”
“噢……没错,在下一直守在校场。”
“这天下间竟然有事能让您废寝难眠?”
“是啊!心有所忧,无意睡眠。”
“哦?所忧何事。”洛熙对这回答倒是有些意外,他还以为这个自负的谋士永远不会惊慌和担忧。”
“如少将军之前所言,上官文芩绝非泛泛之辈,很有可能会看穿在下的计策。若是如此,她必会趁今夜我等懈怠之时前来袭营。故而在下彻夜未眠,以防意外发生。”
“夏侯大人辛苦了。”洛熙这一句倒是真心实意的问候,他对每一个这样尽职尽责的人都满怀敬意,但夏侯云的不择手段始终让他耿耿于怀:“看来您的计策是成功了,等会我们就可以顺利收回泗城。只是殷燕人中毒之后一定气急败坏,撤兵之前必然将毒粮扩散,届时泗城难免生灵涂炭。唉,我军兵将素质、阵法操练皆强于殷燕,为何一定要用下毒来迫使对方撤兵呢?”
“少将军放心,不会生灵涂炭也不会尸横遍野,在下还想多活几年,可不敢乱做那些折损阳寿的事情。粮仓中下的毒不至于伤人性命,只不过会让人晕眩无力、呕吐厌食,经过医治和疗养后,大约数月可以痊愈。”夏侯云意味深长地看了少将军一眼,继续说道:“殷燕虽弱,但是有备而来,兵力也与我们相差无几。要在短时间内击退他们,还要使其无法继续进犯,下毒削弱其战力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在下这也是应少将军的要求才如此决断。”
“夏侯先生所考虑的恐怕还有我父亲的密令吧!他一定派人交待过必须保存兵力,所以你才用这种为人唾弃的手段去迫使对方不战而退。”说着洛熙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的父亲,可是他也无法去指责或是憎恨自己的父亲,而自己对于夏侯云的厌恶,一定程度上也是情绪的宣泄和转嫁罢了。
“丞相大人的确吩咐这次出征须以保存牯州军的实力为先,但这也是为了少将军您啊!”天亮渐亮,火光开始略显迷离,夏侯云的神情也模糊了起来,“自洛大将军死后,军中一直群龙无首,各自为主。赵从杰空承大将军之名,却无大将军之实,丞相大人费尽力气地清算也只是将军中反对朝廷的声音强压了下去,并未完全掌握住兵权。少将军若想在军中占得一席之地,无兵权在手恐怕难以成事。况且……”
夏侯云犹豫了片刻,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况且陛下遇难,亦无子嗣存留,国不可一日无君。时下青年才俊中为少将军翘楚,朝中上下莫不以将军为继承帝位之最佳人选,因此更需要一支忠诚的兵马稳定大局。现在帝州军虽然为我们所用,但赵从杰乃二面三刀之人,绝不能深信。所以丞相另外选中了牯州军作为少将军的亲兵。”
帝位,世人梦寐以求的至高权利,无数眷慕者为之粉身碎骨,无数追求者因之身败名裂。成功之人寥寥无几,却总是不乏野心家的狼顾。而当今天下有两个人竟然对这份至宝没有丝毫收为己有的欲望:一个是洛子义,他一心只想把自己的儿子捧上帝位;另一个是洛熙,他一心只想辅助那位自己所认定的君王。对于父亲“惊天动地”般的溺爱,少将军是承受不起,也不敢去承受,他躲避着夏侯云的视线,同时把话题引往别处:“这么说来,撤出牯州不仅仅是为了坐视武家军和紫云山鹬蚌相争,更重要的是让牯州失守,使牯州军名正言顺的成为供我调遣的私兵么?呵!那七十万无辜百姓的性命竟然是因为我而葬送的,夏侯大人,你这真是为我着想么?我看你是想让我不得善终吧!难不成何林将军和他手下亲信全军覆没也是阁下的算计?目的是为了让我能彻底掌握牯州军?”
面对洛熙的质问和讽刺,夏侯云沉默了片刻,随即自嘲般的笑了笑,回答道:“少将军太高估在下了。的确,撤出牯州是有意为之,但郁丘人会大开杀戒着实令人意外,他们在夺下禺州时对当地百姓都是安抚为主、仁德以待,这突然转性在下也看不明白。至于何将军全军覆没一事,更加令人始料未及,纯粹是文竹清与上官文芩合谋,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东方鱼肚泛白,休息了一夜的太阳英姿勃勃地出现在天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两人之间,依然点不明他们的心绪,只是照亮了两张疲惫的面庞。夏侯云转头眺望了一眼日出,随后行礼道:“少将军,时间到了。泗城百姓还在等着迎接您入城呢!”
“姬如昭!去请柏将军来,准备出征,收复泗城。”洛熙虽然还看不透夏侯云,但已经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为如何重用这个人。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面前这个人拿捏得和父亲一样准确。少将军再向不远处待命多时的姬如昭下令之后,便朝夏侯云回礼鞠躬,随后拔营出征。
大军伴着朝霞一路回到泗城,果真如夏侯云所说,殷燕已经趁夜撤走。现在这里是城门大开,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些横倒的货车。拉车的驮马早已被人牵走,车上的货物也不见踪影,就像被土匪洗劫一清的商队一样。冷清萧条的场景让洛熙有种不好的预感,最坏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了。他正准备吩咐身边的士兵散开查探时,只见一个有些眼熟的人从街边的小巷中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这位狼狈的书生正是泗城太守黄士道,他见到洛熙之后也顾不上礼数仪容,就像一个走丢了的小孩终于找到了母亲一般地扑了上去,带着哭腔哀嚎着:“洛少将军,你们终于回来了!昨日城池失守之后,下官就躲在民居中不敢外出,忧心了整整一夜。真是怕这泗城就像东海郡一样再也不能蒙受我大沛恩泽了啊!”
“好了好了,堂堂一城太守,哭成这样成何体统!”洛熙不耐烦摆了摆腿,在这个好哭太守把鼻涕眼泪都擦在自己脚上之前把他给甩开了,接着用马鞭指着他问道:“我问你,这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百姓们都去哪了?”
黄士道擦了擦泪,边整理衣衫边答道:“百姓们都去官仓抢粮食去了。已经抢到的百姓也是闭门不出,生怕少将军回来后官府会向他们追讨。”“什么?说清楚,怎么回事!”洛熙瞪圆了眼珠,吓得黄士道后退了几步,唯唯诺诺地解释了起来:“昨夜殷燕人撤走的时候故意弄出了很大动静,还要士兵高声宣扬说他们打开了官仓的门锁,要把粮食全部带走。部分百姓们被吵醒之后,见街上遗弃了大量运粮的货车,以为是殷燕军来不及带走的,于是纷纷把上面的粮食往自己家中搬。街面上的搬完之后,就去官仓里抢,那里门庭大开,又无人看守,搬的人越来越热闹多,渐渐地,全城人就都吸引过去了。”
“快!命所有士兵挨家挨户的去追讨粮食!切记不可对百姓动武!”洛熙咒骂了一声,又对自己侍卫们喊道:“你们立即随我去封锁粮仓,同样切记,不可伤及百姓!”说完之后立即准备扬鞭策马,而黄士道还有些不明就里:“少将军,不必如此紧急吧!让大军入城休整片刻,再同官府一起慢慢追回即可啊!”
洛熙没有理会,扬起马鞭差点抽到黄士道脸上,同时丢下了四个字,让这位泗城父母官楞在了原地。
“粮中有毒!”
日至晌午,牯州军和雸州军还在苦苦追回散落民间的毒粮,根本没有余力出城追赶殷燕人。但这个好消息难以让高行旭轻松下来,他望着缓慢前进的队列,心中苦闷不已。这根本不像是在行军,士卒们手中的兵刃都成了他们赖以前进的拐杖,就如同一群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游园一般,走走停停。病重者更是需要健康的士兵们抬着前进,就像一群逃离瘟疫的难民。“天下大势,兴衰更迭,素无常时。为何唯独我殷燕久衰难兴啊!”太子望着泗城方向,脸上一副大志难成的苦相。对这句情真意切的感慨,上官文芩却不应景轻哼了一声,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高行旭的脸色不太好看,周围其他人也都不敢吭声。
“军师有何高见啊?”
“若想振兴殷燕,又何必在乎这一城一地得失。我军已得雸州门户,几座城池随时可取。”
“本宫并非纠结于区区城池得失,知道看到大军这般模样,有感而发。”
“是吗?可小女子看到现在的样子,是高兴都来不及哦!”
“?!”高行旭和身边的所有人都是万分震惊,纷纷转头看着上官文芩,等待着帷帽轻纱下的那张玲珑玉唇能有怎样惊世骇俗的言论。
“堂堂大沛官军,连下毒这种为天下所不齿的烂招都用了出来,可见其为了保存兵力是无所不为。他们保存的兵力的原因无碍乎是要平定武家义军。由此看来,大沛的这一次权力之争将会相当精彩,厮杀也是相当激烈。而大沛内耗越重,对殷燕越是有利,这难道不该高兴么?”
“哈哈哈!军师一言令顿时令本宫释怀啊!”高行旭笑了起来,他身边的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上官文芩看到这副场景,同样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