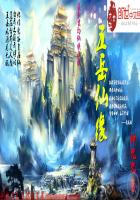“都给朕住手!”
就在这时,天华殿的大门豁然洞开,幽暗的光线汹涌出来,氤氲的光线里走出来一个身着明黄龙袍的威严身影,脚步沉重有力,神情隐怒。
袁临顿时心弦一紧,连忙收刀,站定,恭敬的朝帝君所在的方向跪了下去,其余铁旅侍卫见状,也赶忙如风吹麦浪般跪倒,齐声唱诺:“臣等参见陛下!”
当帝君一脸威怒的出现在天华殿门外时,殿外一时间的气氛忽然就变得肃穆无比,所有人低声喘息,感受着那道睥睨天下的君王的目光从他们头顶扫过去,登时身子一震,没有人敢抬头。
“都起来吧!”武安君慕容周恹恹的挥了挥手,神色复杂地瞥了一眼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得袁临,又说了一句“你也起来退下。”
不知何时袁临已经将把柄长达四尺的碎川刀隐藏在了破碎不堪的重氅之下,此时听到帝君发话让他离去,方才缓缓起身欠着身子往后退了几步,刚想要为自己辩解开脱几句,然而疏忽抬头之间,他忽然撇到了殿门外还站着侍立着一个有些微胖的人影,正是大总管刘登。
见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与任何大臣都没有任何交集的大总管却轻轻向自己眨了眨眼,袁临顿时心神一震,心中立时了然方前那一幕已经被帝君看在眼里,而且已然龙颜大怒,他若再说些什么触怒龙鳞,怕是······心念及此,他立刻诚惶诚恐朝帝君重重叩拜,然后立马便下令带着众人离去了。
袁临率众离去,在转头的不经意间向着刘登略点了下头表示了自己的感激,刘登面目慈祥也唯一点头回礼,这才快步带着麾下铁旅走远了,可同时他的心里也不免对那位宫里的大总管生出些莫名的意味来。
慕容周站在殿门前俯视着胸腔起伏不定的颜孤,眼中飞快的抹过一丝不悦,淡淡道:“进来吧。”说完,他便扭身转回了殿中。
颜孤见他也并不行礼,也并不是仗着同门师弟的身份,而是此时的他对师兄有些无限的怨愤,他一昂头便要踏步进去,这时刘登适时的提醒了他一下,眼光瞄了瞄他手中染血的雪霁。
历朝历代以来,宫廷之中最忌讳的便是内臣与外臣暗中结交营私,刘登自然也懂得,所以他既不不巴结权贵,也不得罪权贵,凭着多年来察言观色的本事时常施些好处与他人,对谁都小心逢迎,于人都是一副和气的模样,这正是这样所以他才能历经三朝不倒而最终爬到了大总管这个位置。
颜孤知他好意,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剑,心想既然师兄肯见他了,那事情必有转机,就算没有,难道自己还真的能把剑架到师兄脖子上吗?他自嘲一笑,左手瞬时探空一抓,修行至无为境便可有十丈之内隔空取物的本事,虽然他还未入无为,但取个剑鞘倒也不是难事,沉重的玄铁杉剑鞘被他用真气隔空一拉,立刻便飞落入他的手中。
右手挥剑迎空一甩,抖落了点点血迹,殷虹的血珠被雪霁凌厉剑气催发刚飞掠至空中便立刻灰飞消解不见了,在一旁的刘登看了不免啧啧称叹,“铮!”一声,长剑入鞘,颜孤这才恭敬地将雪霁递到了刘登手上,剑鞘入手,颜孤刚想提醒他要小心脱力,却不想这位看起来身材微肿的大总管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轻飘飘的将玄铁杉剑鞘捧在了手中,然后朝他笑眯眯的笑了一下。
颜孤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大总管也是位修行者,平日里他倒也不怎么注意刘登,此时凝神一瞧,发现他竟然是个天命境界的高手!要知道天命境界的高手即使放眼江湖也找不出多少人来,身居天命那也该是一门之主一派之掌的大人物,可这宫中的一个宦官便是天命境界的高手,还不知这宫中究竟还隐藏了多少这样低调行事的人物?颜孤心下难免诧异,不由的想起一句话来,真人不露相。
见他失神,大总管刘登呵呵一笑,道:“剑圣大人还是快些进去吧,陛下该等急了。”
颜孤也不跟他客气,略一点头,便走进了殿内。
刘登将殿门掩好,自己则仍旧侍立在门外,面目温和含笑。
这时甬道之上又神色匆匆的赶来了一个人影,查看着四周打斗的痕迹,沐昭雪心急如焚的看向刘登,忙道:“总管大人,颜孤他怎么样了!?”
刘登轻轻摇头,指了指殿内,他也不唤她长公主,只低声说:“昭雪姑娘,陛下已经召剑圣大人进去了,无论事情如何,姑娘还是请先回去吧,切莫再惹恼陛下了。”
沐昭雪忧心忡忡的朝天华殿望了一眼,暗暗忖度一番,知道他所言不虚,自己留下来也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便拱手向大总管行了一礼,轻叹一口气,转身离去了。
不久之后,大殿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然后静默,再是苦苦的哀求,再然后便是沉默,长久的沉默??????
没有人知道帝君与颜孤究竟说了什么?直至等到夕阳落日余晖将尽,暮色四起时,刘登才终于看见失魂落魄的颜孤从殿内走出来,要不是刘登出声喊他,他甚至忘记了要带他的雪霁剑。
刘登望着他这幅模样,便是历经沧桑如他,也不禁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
在夕阳的橘色晕影里,颜孤拖着被日光拉扯的长长的影子,落寞的握着剑,冲着夕阳笑出了声,只是笑声里的装的并非愉悦,却只有无止无尽的苦楚和悲凉。
他握着剑,走进了落日里,从那一天开始,到很久很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真正开心的笑一次,那个放荡不羁,天大地大任他遨游的少年剑客,终于逝去在了岁月的荒流之中。
春寒料峭,阴沉的天穹响了几道沉闷的雷声后,紫雷划过浓黑的云空,一场春雨忽然就飘摇着跟来了。
在这样阴沉的让人抬不起头来的天气里,酒楼里基本上没什么客人,清闲的要命,几个店小二百无聊赖的聚在一起插科打诨,说说笑笑,倒也好不热闹,不时发出几声笑来,只是笑声回荡在空旷的酒楼里不免显得有些怪异,被掌柜的训斥了几句之后,便阴着脸散了各忙各的去了。
黄小二收拾好了桌椅板凳,又将毛巾浸湿了一遍,使劲拧干将桌椅板凳全都擦拭了一番之后,看着酒楼干净清爽的模样略感满意。此时无事可干,他便找了个凳子坐下,歪着脑袋去看柜台上的沙漏,里面的沙子窸窸窣窣的往下流动,越看眼睛越乏,终于过了半个时辰,这才眼看终于要到打烊的时间了,黄小二开心的笑了笑,心想这下终于可以收工回家看媳妇去了。
可一起身便瞥见了那位靠在窗边饮酒的客人,窗户敞开着细雨斜风飘洒进来,打湿了地板,也浸湿那客人的肩头衣衫,可他仿佛对一切都置若罔闻,只举酒喝下,一口接着一口,完全没有尽兴的意思,也更没有要离去的打算,他孑然一身独立在窗旁,落下一个无比孤单的影子,望着漫天的阴霾细雨独饮独酌。
万般无奈,于是黄小二便赔着笑脸迎了过去,想要劝走他。
可当他一走过去,就被大大小小肆意横躺在地上的数十个喝完的酒壶吓了一跳,以为这个客人大概喝多了,怕是要赖账,于是赶忙加快了步伐,走到窗边。当他着眼一看那个客人仰头望着天空的模样时,那一双俊朗的眸子在电闪雷光里雪亮如剑的神态,他就不由的心中一悸,恍然间明白,这个人没有醉!
虽然没来由相信眼前这个衣着不凡的年轻人不会赖账,可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就是无法放松,看着他的影子,觉得自己的心也被揪起来似的。黄小二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的酒壶,心想,那么些烈酒混合在一起,怕是能放到十头牛了,又有谁能喝了那么多还不醉?
临窗的客人似乎也早已发现了在身后接近他的黄小二,本不愿理他,可察觉他久不离去,便对着下着雨的夜空仰头灌下了一口酒,方才神色戚戚的回眸去看他,被他眼神一扫,黄小二隐隐的,竟然有些莫名的心慌起来。
黄小二才结结巴巴的说了几个字:“客、客官······”便立刻被客人扬手甩过来的一定金子打蒙了,半天怔怔不能言语,反应了半晌之后,方才兴高采烈的捧着金子跑远了。
客人不再看他,又转身去看漫天飘洒的春雨,看着那些雨水在屋檐上缓缓凝聚,然后顺势聚股流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看着夜色中衔接天地的雨水连珠成幕,他仰首将最后一壶酒整个朝着喉咙里灌了下去,只觉得喉间一阵火烧火燎的灼痛,他缓缓阖上了眼睛,唇角勾起一丝笑,然后毫无征兆性的轰然倒地。
砸的整个板楼都隐隐作响,黄小二好奇的往这里望了一眼,手中暗暗的用力握紧了金珠,面色不定的喃喃道:“这个人终于醉了······”
醉倒在地板上的客人,松开了手中抓着的酒壶,壶中未喝完的酒水顺着壶嘴流淌出来,浸湿了他的胸襟,湿漉漉恼人的一片,可他脸上却带着一丝心满意足的浅笑,笑容里又藏着太多让人难以分辨的悲戚,让人不忍心看他,空荡荡的楼层里只听他喃喃低语,仿若梦呓地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阿雪,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夜色笼罩下的皇都晋阳城,灯火璀璨,恢弘雄威的帝京街巷里,无数的行人仍在夏日夜晚的暖风里游荡,无数个不眠夜。
一个华袍的男人打着一把油纸伞从巷口处缓缓步行而来,他的身后尾随着两个孩童模样的人影,慢慢走到了酒楼门前不远处停了下来。
一个小厮打扮的人从酒楼里钻出来,穿过浓密的雨幕,微躬着身子凑近了过去,在男人的耳边低语了一番。
男人满意的点了点头,从手中递出一块银钱给那小厮,小厮顿时喜笑颜开的借住,千恩万谢的转身走了。
而男人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的带着两个孩子走入了已经打烊暗静下来的酒楼。
三个人步入楼上,看到了那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正歪歪斜斜的躺在地上的酒水里,男人蹙着的眉头忽然就松开了。
雷光闪过,照亮了来人的脸庞。
莫儿也抬起了头,看向了那个英俊却无比颓废的男子,发问:“三叔他为什么在哭?”
雪烨慈爱的抚摸着莫儿的发髻,缓缓开口,声音宛如叹息一般,“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时,任谁也都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忍不住大声哭泣的,即使他是这世间最强的剑客,也不例外。
莫儿似懂非懂,他仰着脑袋看着伯父郁郁不乐的脸,懵懂的目光里闪烁着不解的神采,“那他为什么不去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
“因为······”雪烨顿了一顿,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嗓子有些嘶哑,不知道自己此时说出口的话这些孩子们能不能听懂,短暂的停顿之后,他终于还是重重的叹息了一声,说,“人在江湖,尚且身不由己,何况身陷朝野争斗漩涡里呢。”
“走吧。”他吐出一口气,仿佛整个人都轻松了,“去接你们三叔回家。”
话音落下,他的儿子,那个青袍博冠的少年在酒楼的阴影里恭敬的颔首领命,“是,父亲。”
莫儿和雪枫一同朝着三叔走过去,想要将他搀扶起来,就在这时候,一直静默不动的雪烨又忽然说了一句话,落在两个孩子的耳朵里,犹如嗡雷般轰鸣。
“天还没到塌下来的时候,沉默还是爆发?总要做出一个抉择的!”
这也是莫儿孤身留在晋阳的第一天,他从伯父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