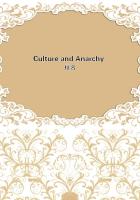容若从正房出来,想自己多日未至官氏那里,明日又要出行,便信步而往。官氏住的东一所,位于正房东侧,前后三进院子,官氏住了南边,前院儿有角门和正房相连,往来十分便利。
官氏正在房中,和几个丫鬟抹骨牌解闷儿,闻得窗外爆竹声声,喧闹不已,记起未出阁时,每逢新正,家中姊妹兄嫂猜枚行令,玩灯剪彩,何等有兴,如今只身落寞,虚度良辰,丈夫又一味冷淡着,全无伉俪之情,一腔情怀无可排遣,不可谓不苦。心中正自烦闷,忽听外面高声传报道,“大爷来了”,小丫头急忙打起帘子,容若已迈步进了房门。
官氏心中有些欢喜,面上却淡淡的,徐徐起身让座,唤陪房丫鬟彩笙,斟上容若爱喝的绿茶。近一年来,他夫妻二人面和心不合,时有参商,容若轻易不来官氏的屋子。官氏性子刚强,绝不认短服输,二人言语稍有不合,便百般不如意,到公婆前回禀一声,回娘家住上个十天半月,好在容若也不以为意。
倒是丫鬟彩笙,见自家小姐嫁得这般一位风流俊逸的姑爷,尚且任性使气,说起话来,更是每常带着刺儿,叫人下不来台,便不时开解一番。新年里,他夫妻二人各自忙碌应酬,连话也没好好说上几句,虽是正头夫妻,比一般的亲眷还不如。彩笙几番欲请主人过来坐坐,缓和一下,又唯恐被他看轻,踌躇再三,竟是无可措词。所幸容若今晚不请自到,正合主仆二人心意。
夫妻对坐闲话几句家常,官氏便和容若商议,新年伊始,要将几个得用家人调换,以便各称其事。那几个见识琐小的,恐为人利诱,行卑劣之事,不如趁早打发掉,不知丈夫意下如何。容若于家事不甚经心,外面之事,自有父亲主理,内庭大小事体,悉听母亲做主。近来官氏帮着理家,容若也乐见其成,便说道,“你见识甚明,行事颇有主见,母亲已和我夸过你几回,尽管去做就是,不必一一和我商量。”
官氏笑一笑,“大爷虽不在意,叫我自家做主,我却不好自专,必得告知一声,况这些家务世情,我也实在不谙练。”二人又议了几件家事,官氏忽然记起一事,看丈夫今日颜色多欢,何不趁便和他求个情,便说道,“我还有一事相求,望大爷看在我的面上,务必应允。”随即说起自己任户部给事的兄长,近来疏于公务,差错连连,激怒了上司,要将他降级罚奉。那现任户部尚书余国柱原是公公手下能人,心腹密友,拜托容若和老爷说一声,斡旋一番才好。
容若闻言,不由微蹙双眉,有些为难之色。他对这位郎舅颇看不上眼,嫌他一身纨绔习气,外清内浊,浮浪不谨,尽有造祸之才,实难同堂共语,故平日里疏于往来。此番乃是他自家玩忽职守,惹了乱子,如何冒然向父亲说起此事?更何况那余尚书靠巴结逢迎,一路升迁上来,容若鄙其为人,一向不甚理睬,如今怎肯为姻亲之事,求助于他。
官氏见丈夫只是含糊几句,并未痛快许允,心中顿然不快,后悔向他说起此事,便冷笑一声,赌气道,“家兄之事,虽系他自作孽,却也不忍放任不管,既为骨肉至亲,凡事护蔽些,也是理所应当。原也不是什么大事,既然大爷不便出面去说,我自己一会儿亲自求老爷去。我只想着,当初老爷和大爷,连八竿子够不着的一个江南流徙犯人,尚且费心尽力,搭进人财去营救,如今自家人有了事,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容若听出官氏嗔怪他不肯为娘家出力,又暗讽他营救吴兆骞一事,淡淡一笑,懒得和她计较。原本想再解释两句,看来也大可不必,一时无话可说,默默坐了一会儿,起身和官氏说道,“我这会儿还要出门,此事回头再议。你好生歇着罢。”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出了房门。
官氏恨容若竟扬长而去,心里有气,稳坐着并不起身,还是彩笙看不过眼,忙叫来两个小丫头,提灯护送主人。侯容若走远,回身劝解道,“大节下,难得大爷过来坐坐,说说家常话儿,奶奶何必又提起旧事,闹得不欢而散。”
官氏气愤愤坐着,无言可答,隔了半晌才说道,“教我如何不气?不过是托他求一求老爷,又不是什么办不了的烦难事。他倒好,沉着脸不发一语。他嘴上不说,心里却瞧不上咱们这位舅爷,当别人瞧不出来么?”
彩笙劝道,“大爷那个清高性子,奶奶还不知道?叫他为舅爷这事儿求情,千难万难,不如直接求老爷来得爽快。奶奶且消消气,大爷近来烦心事也多,自顾不暇,方才奶奶的一番话,连讥带讽的,换作旁人,兴许早就翻脸了,大爷不过一笑而已,奶奶且看在这副好涵养上,饶他这遭儿也罢。”
官氏脸色稍缓,又嗔道,“你个小没良心的,到底是哪一头儿的?怎么尽帮着他说话。”彩笙抿嘴儿一笑,“自然是奶奶这头儿的。只是不愿见主子们新年里便夫妻不和,劝和几句罢了。”彩笙善察主人心意,拿些闲话来打岔,官氏的一腔怨气方渐渐平了。
容若出了东一所,记起几天前小女缠着他要去灯市口看灯,如今看来又要落空,便信步走到颜氏的住处,进门见桌上地下铺满红绿彩纸,颜氏正陪着几个孩子剪纸做灯笼消遣。一见了容若,三个大点儿的孩子便立起身,齐齐向父亲行礼问安。容若含笑坐下,问了问二子目下所读何书,所习何文,随口考问一番。见兄弟俩对答如流,条理清楚,便夸奖勉励一番,让他们自去玩耍。两个孩子如得了大赦一般,恭敬的行了礼,欢天喜地的逃离父亲,如飞而去,颜氏忙嘱咐几个跟随的小厮好生照看。
这长房二孙,可谓明珠家的掌中珍,匣中玉。长子乳名福哥,乃颜氏所出,年方九岁,生得一貌堂堂,眉目和祖父有些相像,性格刚毅果决,已有大家公子的气度,故最得祖父的赏识,言此子疏疏朗朗,慷慨好交,日后必拾金紫如青芥,扬名显爵,不亚乃父。
次子乳名永哥,乃卢氏所出,年方七岁,面如美玉一般,性格温柔腼腆,神态酷肖乃母,尤其一双俊眼,每每令其父不忍细瞧。永哥乃是长房嫡子,年幼失恃,体弱多病,是以深得祖母的怜爱。只是容若心底里对这个幼子态度,却是一言难尽,可说是柔肠百结,又爱又怨。
颜氏见兄弟俩见了父亲,如老鼠遇猫一般,不由笑道,“大爷每见了两个孩儿,必要严词训诫一番,也难怪两兄弟总是有些怕见你。”容若正一手抱持幼女坐在膝头,逗引她耍笑,闻颜氏所言,蹙眉道,“我也并没怎样,无非是让他们知书识礼,顽皮时严加管教而已,和小时候老爷待我一般无二,谁知这兄弟俩却就此怕了我,叫人无法可处。”
颜氏道,“老爷当初如何管教,我并没瞧见,只是老爷的爱子如痴,可是朝中闻名。便是揆叙他们几个顽皮淘气,也少见老爷动怒,但只薄施责罚而已。”
容若道,“养儿女全仗父母教化,若父母宠溺过甚,难免良才为废物,美玉成顽石。像福哥他们,自幼享现成富贵,若不加约束,受小人蛊惑,日后只怕难以收场。我和老爷的教子之道虽不同,然殊途同归。老爷也并非一味宠爱,可谓恩威并施,总是望儿孙辈不辱先祖的英名。”
颜氏一笑道,“大爷之言俱是正理,我岂敢妄议。只是词色过于严厉,让他们心生敬畏,便不敢来亲近你。”容若点头道,“你提醒的是,老爷太太也埋怨我督责太过,我日后注意就是。”
容若教子甚严,视如朽木顽石一般,朝夕磨砺,望其成才,对两个女儿却宠爱有加,闲暇时常亲自教诲。长女韫儿,年方十岁,乃卢氏所出,因是夫妻婚后第一个孩子,容若尤为珍爱,特赋诗一首,以贺弄瓦之喜。韫儿生得端庄美貌,性情沉静,且天性纯孝,长辈前颇能解颐尽欢。次女煜儿,乃颜氏所出,是年不满四岁,生得乖巧伶俐,活泼可爱,最得父亲的欢心。
卢氏去世后,留下一双幼小儿女,由颜氏亲自教养。那颜氏温柔敦厚,抚育一双嫡子女尽心竭力,视若己出,是以韫儿和永哥和庶母一向亲近。颜氏多年来谨言慎行,抚幼子,调幼女,颇得阖府赞赏,容若也因此对颜氏心存感激,另眼相看。
颜氏见容若寡言少语,心事重重,便道,“大爷既要出门,不必尽在此耽搁。明日又要扈从出行,务必早些回来,睡迟了只怕又要头疼。”煜儿见父亲起身要走,却撒起娇来,缠住父亲,定要带去街上看灯。容若见爱女莺声婉转,稚嫩可爱,早已是心软,遂抱起小女,和颜氏,韫儿道,“时候尚早,我带你们到后花园里转转,看看府里的花灯。”
明府花园设在宅院西侧,南侧便是后海。花园中央临水起造一组楼阁,尽可赏月观荷,蜿蜒曲折的湖面环绕花园四周,别有情致。周围高低错落,点缀些亭台水榭,假山树木。此时天已黑尽,但见树枝上檐口下,悬挂着各色琉璃花灯,连水面上也是飘浮着一盏盏荷花灯,绣球灯,将一座花园装点得五彩斑斓。
当年卢氏在世时,每逢元宵佳节,最喜自制花灯赏玩。卢氏早年随父任,在岭南住了几年,见识过制作精美别致的花灯。嫁给容若以后,年少夫妻情投意合,惟风雅是命,时常弄些风花雪月之事,以助闺房之乐。因此头一个元宵佳节,卢氏便提议弄些新奇的花灯,给家人一个惊喜,容若岂有不乐而相从之理。
二人于是分工合作,自画图样,亲自监工,从腊月里就开始准备,命南方来的能工巧匠,制成各式精巧的花灯,元宵前几天就装点在花园里,请合府老少前去赏灯猜谜,好不有兴。那彩灯色色不同,人物各异,机关旋动,就如活的一般,一时众口称赞,名声在外。京城里相识的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明府花园赏灯,艳羡不已,传为一时佳话。
卢氏病逝后,每年元宵节,明府仍聘请南方匠人制灯,并市面上买来各式花灯装点,只是今非昔比,盛况难再。虽顾及容若的心情,无人敢当着他的面,提起往日之景象,但私下里却免不了追忆一回,叹息卢氏夫人当年的慧心巧思。
容若带着两个女儿四面观赏,漫步徐行,逛至湖边水榭,见里面花灯粲然有趣,便踱进去猜一回灯谜。韫儿生于高门贵第,自幼得父亲悉心教导,年岁不大,却已秉承母亲的敏慧灵秀。可喜她仰承父志,终朝以琴书为乐,吟咏为欢,不知不觉也学成诗书满腹,出口成章,俨然是一位闺中才女。偶有无关紧要的题咏,容若无暇自作,也曾倩韫儿代笔,无不深合己意。韫儿今日难得陪父亲同游,已是开心不已,便格外用心,要在父亲跟前卖弄才学,容若随口问的几个灯谜,略一思索便猜中了。
颜氏笑着打趣道,“韫儿真是聪明绝顶,这些灯谜全难不倒她,得了好彩头,做父亲的要厚厚打赏才是。”容若扭头笑问韫儿要什么赏赐,韫儿静静望着父亲,眼珠一转,甜甜笑道,“父亲当真要打赏么?别的赏赐也不稀罕,只要把那个宋朝有铭文的端砚赏给女儿就好。”
容若微笑道,“呵,瞧瞧,人虽不大,眼光却还高,竟然惦记起这件宝贝来。那双凤砚台,可是北宋的名砚,等你长大一些再说,如今可不能,我另赏你一件珍物吧。”韫儿向父亲撒娇,嘟嘴抱怨道,“闹了半天,父亲原来是诳我的。既然父亲这般小气,女儿也不要什珍物了。”容若不由大笑,怎忍心让娇女失望,便和韫儿约定,待她十二岁生辰时,便将此砚台赏给她,如今权寄我处。韫儿闻言,方始开颜一笑。
煜儿初进园子,尚有几分雀跃,不断地指点发问,容若也耐心的一一告诉。奈何她不过是小儿心性,如何长久,看了一会儿,便趴在容若肩头,两手紧搂父亲的脖子,不断哈欠连天。颜氏摸摸煜儿的头,笑道,“这孩子,念叨了好几天,让父亲带着看灯,临了儿又这么没长性,下次要想看灯,可要等明年了。”
容若搂着女儿道,“怪不得她。这小花园的灯却也平常,没啥可看的。明晚是元宵正日子,你们若有兴致,可带着孩子们坐车去灯市口观灯,再一道去走走桥,多叫上几个家人陪着就是。”京师旧俗,元宵赏灯之外,还有“走桥”一说。但凡有桥之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相率而过,有度厄之意,能祛百病。
颜氏答应一声,见煜儿把小脸儿埋在她父亲肩上,已是酣然甜睡,便从容若手里抱过孩子,交给奶娘,口里催道,“天不早了,又冷得人牙战,略转转就回屋吧。”两个小丫鬟提着防风灯在前面照路,却见那黄色光影里,隐约有细小的雪花纷纷飘落。
众人见天降瑞雪,俱各欢喜,独颜氏担忧起来。回到房中,将容若雪天的衣服找出来,乃是一件银狐披风,一领银灰色的貂绒帽子,帮他一一穿戴起来。又把几件出门更换的衣服装在衣包里,叫丫鬟彩筝拿出去交给跟随的小厮,还有几句交待的话,无非是不许偷懒,别让大爷喝太多酒,早些回来等等,吩咐彩筝转告。
颜氏送走容若,想到阖家团圆之日,不能与丈夫共享天伦之乐,心里颇有些怨忿不平,正闷闷的倚床坐着,心腹丫鬟彩箫过来,低声和主人说道,“奴才看大爷今天一直懒懒的,提不起精神来,方才酒席上也不肯多饮,这会儿将要出门了,脸上才见些喜色,当真是有了新人,气象大不一样。”
颜氏嗔道,“你这丫头,忒也放肆了,背地里议论主子的长短。大爷一直待你和和气气,连句重话也没说过,你倒好,言三语四的,可不反了天了。”彩箫笑道,“奴才能有多大胆儿,就敢说这些。不过是偶然想到这一层,为姨娘有些不平罢了。”颜氏微微一笑,啐了一口,“我还并没怎么样呢,哪儿就轮到你闲操心,替我吃起瞎醋来了?”说得彩箫一笑,低头无语。
容若或喜或忧,今晚意欲何往,颜氏心中明镜儿似的,只是碍着容若的心情,不便说破就是了。还是去年秋末,颜氏就听闻容若禀知老爷,要娶江南来的的沈姓歌姬进门,被老爷一口回绝。觉罗氏问清这歌姬的身世,满心不悦,斥道,“咱们这样的门第,长子居然要娶来历不明的歌姬为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给老祖宗丢脸不说,旁人会怎么看?既然有心纳妾,天底下好人家女儿何其多,怕不挑花了眼,何苦痴心要定这一个,可不是失了心,昏了头么。”
容若百般恳求,和父母也闹了几回,见父母绝无退让之意,之后再不提此事。只是过了不久,彩箫便悄悄告诉颜氏,大爷已经知会官氏夫人,在外面租了一所宅子,纳了沈氏,就住在南边儿不远,德胜门内,只是严词吩咐下来,不许一言泄露,让老爷太太生怒。
那时节官氏正烦心娘家的事,见容容正言告求,明知无可挽回,只冷笑两声,也懒管这笔闲帐。合府仆从,或敬重容若为人,或有心讨好,也就相帮瞒下了。想着过一阵子,生米煮成熟饭,即便老爷太太知道了,不过责骂一番,也翻不过天去。
颜氏咋一听彩箫所言,不免有些心烦意乱,微微含酸。想到自己嫁来相府这么些年,与夫君也称得上相敬如宾,有情有意。近来见他心神不定,几番欲言又止,却原来是为了此事。想自己也不是妒嫉之人,纳妾一事何苦单要瞒着我?当真是“日亲则情薄”么。
颜氏虽有些不平,终究是敦厚贤良之人,视夫君为天,并不敢争长论短,有亏德行。此后见了容若,一如往日,尽心周到,把此事绝不提起。见夫君两下里兼顾,不胜奔走之劳,未免顾此失彼。毕竟是十年的夫妻情份,心里反而为他担忧,便放下早先的不忿,帮着丈夫在老爷太太那里遮掩。
。。。。。。。。。。。。。。。。。
根据纳兰家族墓志铭及其它记载,纳兰生前育有二子二女,并有遗腹子一名。长子名福格,次子名富尔敦。长子次女为颜氏出,长女次子为卢氏出,遗腹子据认为沈宛所出。子女年岁和书中描述一致。年长二子成年后,一文一武,各承父业。长子福格年未弱冠即选充侍卫,二十六岁即早卒。嫡子富尔敦走科举之路,年二十三登进士第,后遭谪戊,卒年不详。据明珠墓志铭所载,成德二女俱嫁当朝名臣,嫡长女适内阁学士高其倬,次女适翰林院侍讲年羹尧,可惜俱年寿不永,未满三十岁即早卒。纳兰家族最长寿者乃是明珠,享年七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