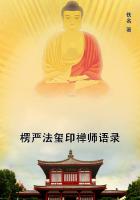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四月初七,日月同辉
母亲病势日增,脉气不祥。
最后那夜,母亲尸居余气,形神已离,
咽气前夕我在她的床榻旁打弹弓,
将五只佛手搁在距我十步之远处,
并于心中默念若打得一只佛手母亲的病便能好一些,若全部打中,母亲便能立即痊愈。
当第五只佛手也被顺利击倒时,我乐坏了,似觉神佛在助我,母亲的病一定会好转起来的。
怎料就在庆贺之际,母亲便撒手人寰了。
父亲悲痛不已,见我竟然在此玩弹弓并面露悦色,二话不问就将我鞭打一顿,骂我不孝。
虽受委屈,但我没有多做解释,也不怨父亲,
只于心中认定一理:原来世上是无神佛的。
母亲染疾下世,除了一条幼犬,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只小狗乌眼褐毛,其饮食起居之前皆由母亲一人打理,和我可谓亲同兄弟。
为报养育之恩,将其命名为白里,即满语里恩情的意思。
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调教的,白里虽属大型猎犬,但它从来不会叫不会咬猎物,对人分外亲。
遵照母亲的遗嘱,丧事未按萨满教葬仪。
当夜和尚们进来绕棺念经,超度亡魂。
父亲以银票代替纸钱,即便库存所剩无几,也绝不烧冥币,他想让母亲收到真正的银钱,不至于在阴间受欺。
我和白里守在母亲的灵柩前哭了一夜,泪水难禁,一直牵着她的手不放,谁要拉我走就咬谁。
到了辰初发引,应佛僧开方破狱,传灯照亡。道士们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
待破土下葬后,人们相互安慰,都说人活百岁横竖要死,须得节哀才是。
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香火味对我来说,是母亲死亡的味道;
对僧人来说,则是每日出工的味道;
对卖香火供品的小贩来说,更是金钱的味道。
自从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家道中落,父亲不得不举债度日。
清明过后,舅舅捎来的几张银票加一纸书信如雪中送炭,既助父亲还清欠款又诚邀南下,同进同退。于是父亲决定从北至南举家迁徙,投靠回云镇的叶赫那拉氏。
一来是打算在那儿兴办烟花厂,重振辉煌;
二是今年早春,京城天花横行,每至天明开城门常常出现骇人景象——无数马车拉着一口口小棺材出城掩埋。穷人家则是用草席一卷,再小点的孩子则是塞进坛子里密封起来就完事了。听说我哥哥在四岁时就是死于这种病,父亲至今仍对其念念不忘,他不惜重金制造冰棺,并每月从天山运来数吨冰砖,将哥哥的遗体封藏于冰里。若不是这样也不会欠这么多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高人,令哥哥重新睁开眼睛;
三来是听闻在湖北有一种妖术能请死人起死回生,名为“叫魂”。
于是父亲决定赌最后一把。
我感到父亲喜爱哥哥更甚于我,甚至怀疑,父亲希望患天花的是我,而非我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