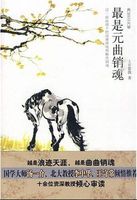殷凤离气得额头青筋突突直跳,又见凤凰寺琅邪凌厉一鞭破空而来,眼见会伤及那个只顾和她调笑的景珏,她情急之下不觉喊出一声:“住手!”
连殷凤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挺身而出,眼看鞭梢将至,她只把手里的琵琶挡在身前。
这一鞭承载了凤凰寺琅邪所有的愤恨,他要景珏死,所以当他看到殷凤离冲出来阻挡在他和景珏之间时,他即便想要收回鞭子,也是势不由人。
殷凤离只感觉手里的琵琶应声碎裂,而她以为的疼痛却没有袭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天旋地转,再相看时,才见景珏已和她互换身位,她被他单臂护在怀里,而他另一只手,却稳稳握住了鞭梢。
那样强劲的鞭势,岂是肉身轻易能承受的,只见景珏握住鞭梢的虎口,被生生震裂,鲜血顺流而下,染湿了他青衫的衣袖。
而景珏并未因手上伤势而住手,那只拥住殷凤离的臂膀翻手弹出一道流光,直袭向凤凰寺琅邪左胸。
凤凰寺琅邪身形稍滞,被琉璃弹丸击中心口,当即就闷出一口血来。
“你没事吧?”殷凤离拉过景珏左手,眼底只有他血淋淋的伤势,她哪儿管凤凰寺琅邪吐没吐血,只取了丝绢替景珏包扎。
景珏看着她替他包扎时的心疼样,不免笑道:“果然是只会疼人的妖精。”害他都有些魂不守舍哩,“放心,刚才狼王在最后收了气力,我这手不会废掉的。”
殷凤离此时才去注意凤凰寺琅邪,知道他是为她才收回鞭势,她不免朝他道了声:“多谢!”
而凤凰寺琅邪却将脸侧向一旁,不搭殷凤离的谢,只对景珏哼道:“你以暗器伤我在先,胜之不武。”若不是他的左臂无法动弹,也不至于躲不开他最后一击。
景珏只瞅向凤凰寺琅邪的面庞,眉目间凝着冷色回道:“你大月氏也派人刺杀于我,又有何光彩可言?”
眼见两人又要争执起武,殷凤离才出声喝道:“够了,这里是寻*欢之所而不是比武场,你俩砸坏的东西统统都要赔钱,若是彼此都还不服气,那用棋来一决胜负。”让他们打打杀杀,她实在觉得心脏承受能力有限。
两个左手都暂时废掉的人脸上皆露出冷笑,嘴上倒是不说话,两人只同时移到棋盘前,凤凰寺琅邪取了黑子,景珏捻了白子。
这白子走先,景珏却侧目问殷凤离:“小妖精,你说这盘棋,咱是攻还是守?”
殷凤离挑了挑眉,回了景珏一句:“观棋不语真君子。”又不是她下棋,她才不管那么多。
景珏只瞅着她,又戏一句:“你乃妖精,何来君子之说。”
只一句,气得殷凤离跳脚,嘟囔道:“我只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景珏低笑点头道:“果是胸无城府之人的下棋之道,那就依你之言。”
说完,景珏右手上白子,直落棋盘正中的天元星位。
正真对局之人,嫌少会起手便走天元这一点,因为先走这个星位,便颠覆了一切成名的定局,这一盘棋,是自由之局,而先子必有优势,可落在天元点上,那起手的优势便就都没了。
“你在让我。”凤凰寺琅邪的话语是肯定而不是疑问,对他的君子之风,他只以冷笑对之。
景珏冷嘲道:“大丈夫祖坟不让,功名不让,女人不让,除此之外,让你一子又有何妨,更何况,我也不一定会输。”
闻言殷凤离只想翻白眼,这人,都自负到自大了,想来也是,没那点自信的人谁敢起手走天元?
两人落子速度极快,别人一双眼睛都忙不过来,更遑论思考。
在殷凤离看来,那两个天之骄子般的人物,浑身气场真的好生吓人。
而气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楚,凡品德、能力、风度等等都取决于气,那是源于人的先天禀赋,又赖于后天的自身修养。
而那两人当真好修养,一个气壮山河,一个势吞万里,皆有盖世之气。
而他俩,真就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一局不够,整整下了十局。
棋盘上攻既是防的理念被那执棋的二人表现的淋漓尽致,直到数百年后,凤凰寺琅邪的子嗣后代建立了大金皇朝,在南下入侵之时用的便是以攻代守的手段,每隔两三年便会南下侵扰一次,使得南朝疲于防备无从发展,此消彼长之下,南朝逐渐衰落,大金终吞并南朝,一统九州。
一切之始,都源于这位大夏皇朝“凤凰儿”的一席话。
不过当时,凤凰寺琅邪和景珏的这十局,不分胜负。
这惊心动魄的快棋十局,被后世称为“云雨十局”,不仅仅是因为下棋二人后来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更因那一个女子,大夏皇朝步入一个密云不雨的局势。
凤凰寺琅邪离开云雨坊时已是深夜,今日一弈虽未分出胜负,但他想用不了太久,他便会和那位信王再次交手,下一次,就不是在棋盘上,而是在战场上,到时候,他就不止是让他信王让功名,让祖坟,他还要他让出那个女人。
行至停泊着他的福船的码头,早有暗部在此恭候,凤凰寺琅邪正待要上船,夜色里蓦地现出一道修长且华丽的身影,而那道身影踏过的地方草木皆枯。
凤凰寺琅邪沉眉,出言道:“来者是唐门何人?云雨坊内伤我之人,便是你吧。”依他和信王交手后的印象,他不认为景珏是那种会使阴招下毒之人,他的左胳膊,中的不是信王的流光暗器,而是这个人的毒针。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虽然我不想承认,但皇甫景玥确实是我的名字。”景玥的声线阴沉冰凉,他认定的女人怎容他一个外族蛮子亵渎,没毒死他,算是他那张脸的荫庇,再有下次,他定要让他凤凰寺琅邪死无全尸。
“不知阁下深夜阻本王去路,所为何事?”凤凰寺琅邪蹙眉自思,大夏圣宗皇帝有三十五位皇子,可他从没听过皇甫景玥之名,而唐门天子却叫唐玥,不知他二人是否有什么联系。
“交出唐佑,我给你解药,你滚回草原,从此不许踏入我大夏一步。”景玥提出条件。
凤凰寺琅邪扶着自己左臂,他还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左胳膊,只得扯起邪笑道:“看来我没有选择,让我交人也可以,但我要知道,云雨坊内你宝贝着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不过是想偷得一吻,便惹来他的毒针,让他愈发好奇那女人的身份。
他回头,吩咐下属放了抓来的唐佑。
景玥见唐佐将唐佑扶定,方才将装着解药的瓷瓶扔给凤凰寺琅邪,同时回道:“那是一个你绝对要不起的人。”
见凤凰寺琅邪登船,景玥只道:“狼王就这么相信我给你的一定便是解药。”俗话说卧榻之下岂容他人安睡,他真该毒死他以绝后患的。
凤凰寺琅邪立定船头,他也未服解药,便将瓷瓶投入江中,立誓道:“无所谓,只要本王还活着,迟早卷土重来,踏平大夏。”
江面波光粼粼,风景好不美丽,而江面下,却是暗流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