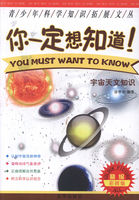朱慈燝到了天阀军控制区域,就发现官道上竟然有水泥路,越是接近厦门军区地界,越是多得见到有富家少爷骑着自行车。虽然不多,但还是很让朱慈燝欣慰,感觉到一些现代的气息感,原来这天阀军行政委员会,鼓励乡审修路,并有立路牌纪念,这些有了钱的人当然想留名,便开始出钱修路,而天阀军新设的各地县长权力和朝庭的知府县令权力相对,但因为天阀军的强势,县长的权势反而更大,天阀军的县官考核方式也是以修路为政绩之一。
朱慈燝到达福建镇海县(明朝称镇海卫)时,已经出现了不少是水泥建筑的院落,琉璃瓦争相晖映。当然,这些都是富甲一方的仕审所建的。
朱慈燝恢复正常身形,到的海岸,已经入夜,见一旁似还有渔夫,希望他能送自己过海到厦门,渔民道:“小娃娃啊!你家大人呢?是不是走失了。”
朱慈燝看他唠叨不已,从包袱里拿出碎银,道:“老伯,这是我的银两,够是不够,送我到厦门港,这些银锭就是你的了。”一般的过海,其根本只要几十个铜子就行了,但他心急,便开出了高价。
那渔夫眼睛一亮,不经意间眇了眇朱慈燝的包袱道:“好,我就送你过去。”
朱慈燝因是着急,他的水上功夫本来很强,但如果身上湿了又要换买衣服,反而误事,而且这一路走来也有一二次坐船,便上了他的船,此时海风风势已颇不小,布帆吃饱了风,小船箭也似的向厦门港驶去。内海中浪头大起,小船忽高忽低,海水直溅入舱来,朱慈燝却还坐立如常,身不摇腿不动,渔夫看的一奇,心下更是谨慎。
这时突得下起大雨来,风浪益发大了,小船随着浪头,蓦地里升高丈余,突然之间,便似从半空中掉将下来,要钻入江底一般。船篷上刹喇喇一片响亮,大雨洒将下来,跟着一阵狂风刮到,将船头、船尾的灯笼都卷了出去,船舱中的灯火也即熄灭。
朱慈燝黑暗中,只觉那渔夫借着抓灯笼,靠了过来,森森寒光中,朱慈燝避开,仅仅是一会时间,他的眼睛就看到了渔夫的体温色,没想到这渔夫敢见财起义,发力一斜踢,渔夫就倒在船沿,那渔夫见这小孩如此利害,果然是练家子出身的,只不知是那位武学世家,身子顺势跃入海里,这渔夫长年生长于海岸,是海沙帮的大当家,选择在雨夜里出船,只因为想从这天阀军的地方走私一批精盐,正等接应弟兄,本来看朱慈燝手上带财,刚好可做下没本买卖,却不料点子太硬,连船都赔了,气不打一处来,捅破船底,见离开出发的岸边不远,正好游回去。
狂风挟着暴雨,一阵阵打进舱来,朱慈燝早已全身湿透。猛听得豁喇喇一声响,风帆落了下来,船身一侧。再一看,舱中不知何时,涌上大量海水。
朱慈燝猜想定是这渔夫捅破了船只,自是恨极,只能跳入海中,游向厦门,因为想要快点游过海面,朱慈燝选择了变异身形,虽然海浪翻滚,水流汹涌澎湃,但朱慈燝在生化力量和九阴寒冰真气的作用下,还是以极快的游速的到的了厦门港。
刚爬上海港岩壁,朱慈燝就给海港的气势宏大所镇,仅自己离开厦门半年有余,这里已建成了大明朝最大的港湾,停泊靠岸的船只不计其数,货物仓库更是如山积一般。
朱慈燝变回正常身形,走没多久,海港就有穿着蓑衣蓑笠的巡逻士兵过来,那些士兵见是一个小孩在港岸行走,便是围将过,其中一人问道:“小鬼,你是哪里人?看你一身湿水衣裳,是和家人走丢了吗?”
朱慈燝来了一记天阀军礼,道:“士兵,你是那个师的,我要见你们师长,快带我去。”
众士兵突然间一起哈哈大笑。
“这小鬼开什么玩笑呢!师长是你说要见就见得到的。”
“这小鬼以为在过家家呢?是不是他父母经常以我们为榜样,教他家孩子。”
“真是笑死人了。”……
朱慈燝很是无奈,说了一句文不文,语不语话,众士兵有一人突然立正,向朱慈燝敬了礼,报了暗语,众士兵中有奇怪的,也有不奇怪的。
那对话的士兵和朱慈燝以暗语对答几句,那士兵便尊敬的请朱慈燝到海港边的士兵休息区去了。
朱慈燝耳中隐隐传来对话,“佬肱,这是怎么回事啊!班长怎么对一个小鬼这么尊敬啊!”
“哎,你怎么踢我,我问你话……。”
“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然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朱慈燝很无奈情报局怎么好像变了,在众兵员中成了有多可怕的组织。
那班长用自己的杯子盛了热水递给他,朱慈燝接过杯子,这是一个铁制保温杯,是朱慈燝当年在程乡时送给一些军队长官的,后来兵工厂大量生产,军中也向下发放,但因为产量跟不上,就只发给有立功杀敌的士兵了。
朱慈燝看看室内,这是一个中西合并的水泥平房,砌有有烧水的暖炉,这水正是这里烧开的,旁边的平台上放着九个杯子,知道他们是一个班的,没想到这还是一个战功不小的班。
那班长到外面发了一个七彩信号弹,就回到休息区里陪着朱慈燝,他虽然不知道这小孩是什么人。他很想知道,但他进入情报局时间已经有一年多了,在明里是个班长,实际在情报系统里官可不小,是个正排级,也是第一次收到这种暗号,一旦有这暗号切口的就是特别人物,他心中猜想几个师长都没孩子,看来是温总会长等商会成员公子孙子一类的。
“呯、呯……啊”朱慈燝听的外面枪声大作,时不时的还传来惨叫声。
朱慈燝问道:“外面的枪声怎么回事?”他已经随便换了身由士兵们提供的军服,虽临时剪短,很是不合体,但总比没有的好。那班长正帮自己烤衣服取暖,见班长的军服是蓝色的,胸口上写着一师,知道这是海一师的人。这也是,每个师驻守的地方还是朱慈燝划定的。
那班长听他说枪,而不是铳,更说明这小少爷有点见识,更坚定了是天阀高层的子弟的猜想,便道:“是走私精盐的,也不知是哪个奸细在工厂里走私精盐,打了一批又一批。”
朱慈燝点点头,问道:“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那班长心想:和一个小孩说什啊!他能听懂吗?
朱慈燝见他没说话,估计是认为自己是个小孩的原因。
没过多久,那一班士兵就回来了,还带了一大帮人,其中之一竟然有那个渔夫。
朱慈燝见他给拷住了,右胸口上有个枪孔,伤口血在不断的流,以这个时代的医术,恐怕再不加于救治,是活不过多久的,但他体魄雄健,出口骂人,也不见伤的有多重,只是也是进气的少,出气的多。
幸好这休息室很大,还有看守房,用来看押审问犯人。
朱慈燝看着那渔夫,那渔夫也在看他,骂道:“小鬼,看什么看,没看到虎落平阳被犬欺吗?”
一名士兵听他这样骂,立马给了他一拳头,没想到这渔夫捂了肚子还在骂,又对朱慈燝道:“你爷爷的,没想到你落海水里没死,真是奇了。”
朱慈燝见他还挺硬气的,道:“你化成灰了,我也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呢!”
渔夫转头对旁边的人道:“用火铳,你们算什么好汉。”
班长哼道:“你算好汉,进班房里的好汉。”点了几个人,叫人帮他止血。
渔夫怒道:“有本事将老子放开,看谁干的谁赢。”
那班长笑道:“真是没脑子,我一枪,你也就没命了。不过,也不用浪费子弹了,大多数军医都给派去台湾了,周围百里地都没大夫,你死定了。”
渔夫见血止不住,强道:“怕什么,我也没想过活命,老子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朱慈燝突然走到火炉旁,将放在火炉上烤的匕首拿起来,走到渔夫旁,单手按渔夫挣扎的双手,另一手挑入弹孔内,匕首只一转间,从里掏出弹头,痛得渔夫哇哇大叫。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朱慈燝拿起炭灰就往流血的伤口上撒去,渔夫更是惨叫连连。
余众没想到这个小孩这么胆大,似乎还懂医术,都是惊奇。
没等众人感叹多久,外面嘈杂声响起,几个士兵出去看,不多时奔回来一士兵。
“报告班长,咱们海一师的师长到了。”
班长道:“快,集合所有弟兄,我们一起列队去迎接。”
回来的士兵道:“班长,不用了。师长他说他亲自……。”
“报告,海师第一师,秦百胜到。”
众士兵一怔,只见那小孩回了天阀军军礼,在众人奇怪目光下,朱慈燝由秦百胜抚上马,和秦百胜带着一众人马跟在后面一同走了,众兵员面面相觑:如是温会长的孙子,还轮不到有这种待遇,这小孩是谁啊!
朱慈燝在路上没少问秦百胜问题,也只知道王承恩是和自己的外公、母亲、紫雷一同过来的,还带了一批小太监和宫女过来,而且听这老粗形容的样子,这王承恩和自己外公真的很熟。
朱慈燝多问了几句,见这老粗也不如何了解王承恩为什么会和自己亲人在一起,还有自己设在亲人身边的护卫都在干什么,连问几个都不是很清楚,必竟情报局不归他管。
朱慈燝晚上因担心家人,睡不着觉,在船中守卫的人又都是自己人,只好变异打坐消磨些时间,竟意外发现自己的龙行寒虫真气又变得更加充沛,等于常人几年苦俢,细细思来,定是在海中风浪中逆浪游行的原因,但为何会如此,朱慈燝也不得而知。
坐着铁板船到得台湾,一路马车直到天阀军城,这军城因为是荷兰人监督修筑的,所以即使天阀军重修改制,也能看出来有浓浓的西式风格。
朱慈燝见他们将原热兰遮城内城当成自己的府邸,看着所谓的朱府两字,简直是浪费,心想:我一家人能住得了这么大的地方吗?不说说你们简直是不行了。
朱慈燝一进内堂,一路花花草草,各式树木,觉得甚是浪费军费,却见有几个小太监着装之人正在打扫庭院,有宫女还在浇水。
朱慈燝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王承恩这太监住招待所吗?怎么这么多太监官女在这里。连接问下来,秦百胜正要答话,门口有好几辆马车相继赶来,朱慈燝一见,原来是温守思、李连捷、齐哲等人,他们早就接到秦百胜传递的消息,而且又在外城办公,相距很近,便一同赶来。
朱慈燝和他们在超大的花园院落中谈了一会,叙了会旧,各道军、政、商、农、士管理之事,朱慈燝转过话题,便开始下令要他们不用这么浪费,只建一个小楼房给自己家人住就行了,内城就让出来进行办公、居住等。
见众人一一应是,朱慈燝又问道:“这些太监和宫女是怎么回事。”
温守思道:“军长,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本来有说我们有仆人,但王公公偏偏安排了人过来。”
朱慈燝正要下令将他们都赶出去,突然紫影闪过,朱慈燝就给扑到在地上,和紫雷戏耍起来,此时的紫雷之大,已经是成年老虎般的大小,而且还在往上长,加上又是猛兽,体形实是骇人。
众天阀高层从属虽多次见过紫雷,但从心中还是惊惧世间有如此神虎。
朱慈燝正不断的抓捂着紫雷的头,给它挠痒痒。
“燝儿,燝儿,你回来了,快让娘抱抱。”
朱慈燝放开紫雷的头,拥入刘氏的怀抱。
刘氏拥着朱慈燝哭了一会,道:“让娘细细看看。”
“我的燝儿瘦了。”朱慈燝笑了笑,心想:在道观主食大多是吃素,只有偶尔能在山腰打得野物,当然会这样。
向旁一看,刘可平也来到花园,站在旁边微笑看着他母子。
朱慈燝叫了外公。
刘可平要说什么,刘氏在旁道:“燝儿,你老实告诉娘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可平加上一句,点头道:“我想知道王公公说的是不是真的。”
朱慈燝知道外公对天阀军有偏见,吸了口气道:“不错,这些都是我的兵,甚至整个天阀军都是我创的。”语气威压十足,伸手掌引向在军长府门旁和刘可平、刘氏旁边护卫的猎鹰队,接着又引向一旁的各天阀高层。
见刘氏抚摸胸口,听的儿子威压尽现,心下紧张,朱慈燝道:“娘,非是孩儿要瞒着你们,只是孩儿要做很多事,怕惹你两担心。”
刘氏眼中含泪,摇摇头,又点点头,也不知想说什么,良久不语。
一个尖细的嗓子喊道“钦差有司,王大人到。”
朱慈燝看城门兼院门进来一中年太监,正是王承恩,旁边还有个端着盘子的人,正是武功极高的太监——小系子,旁边还跟着一众待卫。
朱慈燝一见这两人,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正是这鸟人跟家人说了自己的事,还有也不知道家人有没有中什么毒,虽然还没叫军医查看,但想和自己猜想的八九不离十。
朱慈燝咬牙下令道:“众将士听令,给我包围这些人,如有反抗,杀无赦。”
随着朱慈燝的命令下达,无论是猎鹰队还是秦百胜和李连捷身旁的士兵,都举着机枪对着王承恩一众,慢慢形成包围之势。
王承恩旁边的待卫一见,也拨刀相对,形成疆持。
刘可平、刘氏、天阀军高层、一众打扫宫女太监见形势突变,场中杀机四伏,人人都是脸上变色。
刘可平、刘氏正要说话。
小系子将盘交于王承恩,轻轻一纵,手中细针射向一名天阀军士兵,这名士兵正是猎鹰队副队,神枪手——温细弟,只见他拉栓开枪一气呵成。
那枚秀花针放弃针刺重穴,轻轻回转,只是轻轻一拔枪管,这枪便失去准头,“呯”“呯”“呯”朝向地天45度以上角度发射。
小系子右手又发出一枚秀花针,直取温细弟天灵大穴,眼看温细弟就要陨命当场,旁边天阀军几把枪管也被拨开的当子,朱慈燝到了,快速变异,挟着九阴寒冰真气,匕首直取小系子要害。
小系子大惊,他近来研习葵花宝典,那针法上的功夫已经非上次可比,熟练非凡。算准了朱慈燝就算来的再快,也能杀鸡儆猴,殊不知朱慈燝得九阴寒冰真气相助,虽来不及体会使用,但速度快极,今非昔比。
小系子情急自救,两枚秀花针经细线牵回,挡下强劲的匕首直刺,同时乱枪响完,几名朝庭待卫要么陨命,要么受伤,王承恩给众待卫护住,听得枪响,下蹲不及,帽子都给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