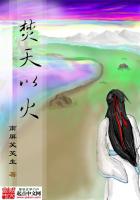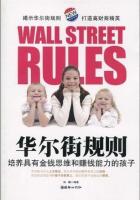李牧实在是犹豫了,心中虽仍觉得自己应该阻止太子赵偃继续殴打蜷缩在地的两个小男孩,却又不知该如何出言,只觉得心里始终有些不是滋味。
难道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
李牧脑海中稍微闪过一丝疑问,却很快苦笑着将之彻底否定。作为赵人的他,会同情秦燕两国的质子,实在是天底下最荒谬的想法了。
就在李牧踌躇不已之际,耳边传来的一句大声喝骂却骤然将其惊醒,那嗓音虽是嘶哑稚嫩,但听在他耳中却宛如洪钟大吕一般震撼。
“你们赵人若是当真有血性,就拿起斧钺刀戟,跟我们秦燕两国堂堂正正血战沙场。若是没卵子,只会领着阉人****以大欺小,便是将我兄弟二人活活打死,本公子宁死不服!”
李牧循声望去,只见原本趴伏在秦国质子赵政身上,尽力为其挡住赵偃等人踢打的燕国长公子姬丹已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艰难的稳住瘦小枯干的身子,满是血渍的脸上却露出无比轻蔑的谑笑,大声讥讽着面色铁青的太子赵偃。
一众少年们自是暴怒不已,大声呵斥着就要继续上前殴打。回过神来的李牧实在忍耐不住,便要出言喝止,不料太子赵偃却是领先一步,朗声喝道:“好啦!都给孤住手收声!”
连带李牧在内,在场众人皆是一愣。少年们却也不敢怠慢,急忙生生止住正要祭出的拳脚和斥骂,老老实实的默然不动。
“姬丹,你不错!”
赵偃早已收起了脸上的假笑,面无表情的淡然道:“至少比孤见过的所有燕人都要有……卵子!”
姬丹并未因赵偃言语中的些许赞许而改变态度,脸上依然挂着明显的讥讽神情,却又不急着出言,只是稍稍用长袖抹了抹嘴角溢出的血迹,便平静的望着赵偃,等他把话说完。
“今日为了保下这个舞姬所生的秦人孽种,你倒似当真要豁出性命,值得吗?”
赵偃倒是不为己甚,指着仍然蜷缩在地的赵政,口中啧啧有声:“你且瞧瞧,此人何等卑贱,宛如死狗一般,便是被打成烂泥,却也不敢呜噎一声,哪里有秦人的彪悍血性?你若心存算计,想要如当初吕不韦对嬴异人一般,认为奇货可居,意图趁他落魄时结交,待他日从秦国换些好处,怕也只是徒劳无功吧……”
“哈哈哈……”
姬丹未及听罢,便极为夸张的捧腹大笑起来,也不知是肆意的狂笑牵动了身上的伤口引发剧痛,还是他心中实在觉得赵偃的言语可笑至极,总之眼尖之人都能看到他的眼角竟笑出了泪水,混入脸颊的大片血渍中,化作数道凌乱的轨迹。
赵偃虽是少年老成,却终究不过是刚过束发之年的稚嫩少年,听着姬丹肆无忌惮的笑声,赵偃渐渐无法维持住脸上淡然的神色,面色开始露出几分铁青和恼怒。
姬丹却恍若未觉,自顾自的笑着,直到喘不上了气,才重重的咳了几声,粗重的咳声中多少显出他的疼痛感。待缓过气来,他高高仰起头,望着比他高出一个脑袋有余的赵偃,脸上交织着鄙夷却又无比认真的复杂神情,沉声道:“政弟唤我一声大哥,便是我一世兄弟。兄弟相交,只在意气相投,哪管诸多心思算计?!弟若有难,为兄者何惜命哉?!你若连这般浅显义气都不醒得,配得起头上的血玉武灵冠么?!”
“说得好!”
一声喝彩从不远处骤然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须发花白的老将军抬手命麾下侍卫止步站定,便独自一人徐步而行,缓缓行来。
老将军步伐虽缓,跨步却大,仿佛短短几步便走到近前,先是眼带赞许的深望姬丹一眼,方才向太子赵偃拱手作揖道:“老臣廉颇,见过太子。”
赵偃哪里敢拿架子,赶忙深深躬身,作揖的幅度硬是比廉颇还大了几分,恭敬回礼道:“上将军多礼,恁地折煞小子。”
众人更是不敢怠慢,除了李牧按照军规行了带甲半军礼,其余少年皆是一揖到地,甚至有人几乎被上将军不怒自威的冲天煞气吓尿了裤子,两股战战,似乎随时都会瘫软在地。他们大多是赵国朝中勋贵家中的二世祖,岂能不知在丛台营门喧闹的不妥,只是先前仗着太子赵偃撑腰,方才肆无忌惮,不料竟遇见上将军廉颇,心中自是恐惧万分。
廉颇阅人无数,怎会看不出他们的心思,一对虎目缓缓扫视过众少年,目光又落在姬丹身上,眼见他虽也拱手行礼,脸上却显出不卑不亢的倔强之色,心中不由暗暗赞许。
良久后,廉颇方才将视线转回太子赵偃的脸庞,意味难明却又极为明显的重重叹息一声。
赵偃本就一直在注意廉颇的举动和神情,心思又颇为细腻,自然知晓廉颇这一句叹息中蕴含着的深意。他面色羞惭如血,猛然扭头,望着满脸惊惧的众少年沉声喝道:“一群没卵子的怂货,竟连燕人都比不上!”
话音未落,他摆正脑袋,望着廉颇满脸肃穆道:“今日之事,是小子孟浪,即刻回宫向父王请罪,到宗庙领受鞭杖!”
廉颇不由赞许颌首,由衷的躬身道:“储君贤明若此,赵国幸甚!百姓幸甚!”
赵偃闻言,淡然一笑,却也不再拘礼,径直朝远处牵着战马的内侍大步行去,也无需内侍辅助,干脆利落的翻身上马,扬鞭绝尘而去。
“还不快滚!”
廉颇目送赵偃的背影远去,嘴边方才蹦出一声冷哼,“明日各自到都府请罪领罚!”
众少年闻言,皆是如闻大赦,虽说归家后少不得挨顿教训,明日恐怕还要做做样子,被都府衙吏打上几杖,但总好过被廉颇拉到军营里论罪吧,军营里的兵卒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少年们赶紧告退,迈着发软的双腿吭哧吭哧的逃个干净,只留下两个小男孩,还有仍旧拱手躬身,默然不语的李牧。
廉颇望着少年们的背影,蓦然长叹一声,似乎毫不顾忌一旁满脸崇敬之色的姬丹,自顾自的盯着李牧,直到他满脸赧然羞愧之色,方才出言问道:“若我大赵后人皆是若此欺软怕硬的鼠辈,你日后做了主帅,当如何自处?”
李牧猛然抬头,毫不退缩的望着廉颇,无比肃穆道:“若此独身无以报国,唯死国耳,何足惜哉?!”
“好!”
廉颇毫不吝啬的大赞一声,慨然道:“如今北方匈奴屡犯我境,代地雁门尚有我大赵十余万大好儿郎浴血奋战,老夫已向大王举荐,由你统兵迎击,你可敢去?!”
“有何不敢?!老将军无需试探,末将终究还是那句,死国无惧!”李牧挺直了腰杆,右手捶胸,大声回应着。
“好!好!好!”
廉颇连赞三声,随即转身望着神情复杂的姬丹,认真道:“自乃祖燕惠王逼得乐毅避难到我赵国,你燕国再无良将。他日你若当真做了燕王,只管挥师来犯,届时便是老夫已逝,仍有后人灭你燕军,围你燕都,灭你宗庙!”
“哈哈哈!”
廉颇仰天长笑,不待满脸恼怒的姬丹出言反驳,便是径自转身离去。李牧却是深深的望了姬丹一眼,方才跟上廉颇的脚步。然而便是这简简单单的临去一眼,却满含坚定和滔天战意,看得姬丹眉头深锁,宛如万刀临身。
“呼!”
姬丹紧咬下唇,倔强的硬扛着浑身伤口传来的剧痛,硬生生挺直了瘦小的身躯,直到廉颇和李牧领着麾下兵卒入了丛台,身影完全消失不见,方才双腿一软,宛如烂泥般瘫倒在地。
他艰难的扭过头,看着仍旧蜷缩在地,双眼呆滞茫然,却始终不发一语的赵政,轻轻咧嘴一笑,乐道:“政弟,为兄是不是很威武?早就跟你说过,有为兄护着,怕个甚么?!”
话音未落,姬丹仿佛用尽了所有气力,只觉眼前一黑,竟晕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