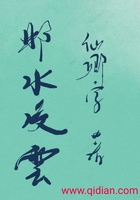栎阳城作为秦国迁都咸阳前的最后一座旧都,曾在短短的三十五年中,经历过商君卫秧的两次变法,见证了大秦由弱转强的艰辛历程。直到威压诸国的大秦东出函谷,将大半河西之地划入疆域,栎阳这座用来向天下宣示“秦君守国门”的边塞国都方才失去意义,被新都咸阳取而代之。
失去国都地位的栎阳并未彻底没落,反而日益繁华。只因当年在商鞅立主之下,秦国两代君王在栎阳开边贸降商税,引来各国商贾常驻,使得栎阳坊市成为秦国面向山东诸国最为开放的交易场所。经过历代秦王的百年经营,如今的栎阳城的商贸虽仍不如齐都临淄和魏都大梁兴盛,却也是天下屈指可数的富饶之地。
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曲梁身为赵国商贾,心中对曾坑杀四十余万赵卒的秦人虽没有半分好感,却也舍不得彻底断绝自家在栎阳城的买卖,毕竟族中数十老小全靠他行商所得来维持生计。
近来秦赵连番大战,两国间的商路时常中断,边贸难以维持,使得曲梁这类行商损失颇大。眼看着族中积蓄日渐亏空,曲梁自是心焦。所幸秦赵两国朝堂不知何故,大战方才稍稍止歇,便颇为默契的重新大力鼓励民间商贸,重开关贸商路。
得闻这天大的好消息,曲梁自是兴奋不已,东拼西凑弄到了数十金,招齐了人手,拉上十余车挂产自馆陶的上品黑陶,浩浩荡荡的运来栎阳。
(注:馆陶位于齐鲁燕赵交界之地,其时属赵。)
说实话,在前来的途中,曲梁心中多少有些担扰。虽说馆陶黑陶深受秦国贵人的追捧,但秦赵两国交恶之际,秦人未必还会如当年那般善待赵人商贾。
出乎意料的是,曲梁运来的十余车黑陶刚刚运抵栎阳坊市,短短数日间便被抢购一空。前来交易的诸多秦商几乎没有压价,便交付了大笔钱财,将刚卸下的货物重新装车,尽数运往咸阳。
赚得钵满盆满的曲梁实在是笑得合不拢嘴,心道秦人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憨直蠢笨。需知他的要价极高,本打算便是被压下个四五成,仍获利颇丰,谁知秦商竟照价全收,这笔横财赚得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昧良心了。
曲梁难得奢侈一次,让下人买来一壶昂贵陈酿,在落脚的馆驿里摆上酒宴,自斟自饮起来。随行的家老已拿着近日赚取的大笔钱财到坊市进货,丹砂之类的矿物,近年来引起了他国商贾疯狂抢购,曲梁自然希望能买上一些运回赵国。
“秦惠文王当年在韩国举国犯秦之时,力排众议,冒着两面开战的凶险,命司马错借机攻蜀,将巴蜀之地尽皆收入囊中。如今看来,实在是福泽后人的英明之举啊。”
酒过三巡,曲梁已然有些微醺,举着酒樽独自感叹道。作为商贾之人,他看不懂朝堂显贵玩弄天下的大谋略,却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识。
什么开疆拓土,什么攻城略地,在商贾眼中都不重要。曲梁羡慕的是秦人如今坐拥巴蜀,获得了丰富的铜铁和丹砂矿藏。不少当初囊中羞涩的秦商,如今早已身家巨亿,随手甩出的钱财,便足抵曲梁这类行商饱赚数年。
“少东家……大事……不好!”
便在曲梁憧憬着归家后的美好生活之际。房门却被猛地推开,历来老成持重的家老面色匆忙的闯了进来,粗气连连道。
“何事如此惊慌?!”
曲梁惊得手一抖,杯中佳酿撒到衣襟上也顾不得了,腾的站起身来,急切问道。
家老好不容易喘匀气,回答道:“老奴行遍城中所有坊市,却根本买不到货物。”
“嗯?某非是你不小心露了身份?让秦人知晓你乃我赵国之人?”
曲梁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先前家老出门前他就曾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装作魏国商贾,免得有些对赵人心怀愤恨的秦商坐地起价。毕竟韩赵魏三国皆出于晋,官话都是洛邑雅言,只要稍微注意口音,秦人很难从长相上分辨出来的。
“并非如此,其实便是我赵国行商,秦人也如往年般正常交易,并未另眼相看。老奴适才还看到几个与我们同来栎阳的同业买到了许多丹砂,价钱至少比邯郸城低了五六成。”
家老眼见曲梁脸色不豫,毫不停歇的急忙解释道:“老奴已询问过,秦人只是不再接受赵钱,不管是直刀还是方足布。除了金子和秦圜钱,便是用魏国的梁充釿,也显得有些不太乐意。”
“秦人是疯了么?!一车丹砂得用多少圜钱?他们秦人莫非能铸出百亿枚不成?!”
曲梁眼中写满不可置信,秦人若真如家老所言,实在是要自绝商贸啊。秦圜钱在诸国钱币中价值最低,一枚魏国梁充釿足可抵十枚赵直刀,百枚秦圜钱。单单栎阳城坊市每日交割的财货,便是将秦国现有的圜钱运来大半,都未必不虞使用。
“诶~~谁知道秦人是如何想的。据说是秦王下旨,秦境内以黄金为上币,以圜钱为下币,一金兑万钱。若无官府符券,严禁秦商私下勾兑他国钱币。尤以赵直刀,秦商许出不许入。违者枭首连坐!”
家老满脸苦涩,作为曲家老奴,他随着老少两代东家行商数十载,岂会不明了眼前面临的困局。
前几人秦商用来向他们够买黑陶的钱币,几乎全都是赵直刀。当时少东家曲梁见到这些成色品相皆属上成的新铸造直刀还颇为惊喜,自是来者不拒,十余车黑陶足足换来了数以万计的直刀币。
直刀若当真在秦国无法购货和勾兑,那便只能将其运回赵国。如此一来,虽远远算不得蚀本,但回程毕竟没有丝毫收益。对于信奉车不走空的行商而言,等同于少了五成收益,平白荒废数月。
“现下还有多少金子?”
曲梁好歹也是经久风雨,很快便冷静下来,皱着眉头询问道。
“当初前往馆陶购取黑陶时,带得金镒都已用尽,所幸途径魏境时为了轻便,将带的赵钱尽数兑为梁充釿,如今尚有千余枚。只是现下还要支应车夫仆役的每日吃用,再算上牲口的草料,若再无进项,只能尽速启程返赵了。”
家老无奈的禀报道,有些担忧少东家要将剩下的魏钱尽数支用买货,便隐晦的提醒道。否则若是到时身拥数万不可使用的赵直刀,却活活饿死在秦国,岂不冤枉?
“嗯?所谓财帛动人心,家老看是否能向一些秦人私下勾兑些金子或秦钱?”曲梁皱着眉头,压低了声音问道。
“万万不可!”
家老吓得差点瘫倒在地,急忙劝道:“秦人自卫秧变法以来,一直严刑峻法,刑律之苛简直骇人听闻。秦惠文王赢驷当初做太子时犯法,硬是被赶出王宫到民间独自游历多年,太子傅更被施以墨刑,割去鼻子。秦国从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敢以身试法?”
“嗯,家老提醒得是。万不能因贪图小利,误了自家性命。”
曲梁微微颌首,心中也是有些后怕,却又随即眼睛一亮,追问道:“家老适才说,秦王只是禁止秦商私下勾兑他国钱币?那别国商贾呢?他们管是不管?”
家老仔细想了想,方才答道:“倒是没有提及,适才还闻得不少我大赵商贾向相熟的魏商借贷了些金子和魏钱,在场的秦商似乎并不在意,只管收钱卖货。毕竟我等他国商贾若想勾兑金子和魏钱,只要离了秦境,秦人也是鞭长莫及。想来只要秦商自己不在秦地勾兑,秦国官府不会多此一举。”
“哈哈,如此便好!反倒是件大大的好事!”
曲梁闻言,不由抚掌大笑,满脸兴奋之色。
家老自是满头雾水,心道某非少东家是被秦人所为气得魔障了,只得硬着头皮劝慰道:“少东家某非是想用手中的赵直刀去寻他国商贾勾兑,抑或是借贷?他们定会坐地起价,不划算啊!还是先回返家中再做打算吧。反正此番也挣了不少,足以支应家中两三年的花销了,想来老东家也不会责怪的。”
“嘿嘿,自然要尽速回去。只是却无需返家,待得出了秦境,我便将直刀尽数兑作金镒,再回返栎阳,将之借贷给相熟的赵商,岂不是一本万利?!”
曲梁满脸坏笑,微微眯起的双眼中满是精明之色,复又道:“若是遇到邯郸的同乡最保险,可让他们用田宅房肆做押。如今我家娘舅已升任太子舍人,还怕他们赖账么?嘿嘿!”
家老呆呆的望着不住喃喃自语的曲梁,心中暗叹,少东家这货实在比老东家要狡诈多了,怪不得小小年纪便被定为下任家主,确实是注定成为奸商巨贾的好苗子啊!
(关于战国末期货币政策,是无良大体依据事实推测的,不相信的读者可查询赵孝成王末期被迫做的武阳货币改革,就可以倒推出秦国是不是用了阴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