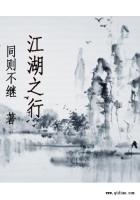约莫半柱香时间,钟离子文便提着酒葫芦,拎了菜盒走了回来,身后随个货挑子,扁担上挂了两坛酒。
到丁字号房门口货挑子放下扁担,讨了银子便自去了。
秋破烦跳起来哈哈笑道:“钟离公子果然痛快,知道我老叫花子爱喝酒便满满的打两坛子!”说着话便抱起一只坛子,搁在嘴边“咕嘟咕嘟”地喝起来,那酒坛子口倒比他那头还大了许多去,却无有半点酒滴在外面。
钟离子文一脸惊愕,从小见木爷爷用粗碗喝酒亦已佩服,今日见秋破烦抱着坛子喝,心中豪气大曾,笑道:“既然前辈喝得这般痛快,晚辈便舍命相陪!”说完抱起另一只坛子学着秋破烦的模样。
秋破烦喝得尽兴才将酒坛子放在地上,深深的打个嗝,伸出又粗又脏的大手摸摸嘴,道:“钟离公子这般爽快越发像老叫花子的一个故人了!”
钟离子文听秋破烦又说起故人,欲待要细问,却见秋菊扶了月儿站在门口,月儿正冲着自己微笑。忙到:“月儿姑娘,门口风凉,你刚痊愈,不可久站,在下卖了些小菜与你和秋菊姑娘,这就提到房中。”说完,便丢下酒坛,将菜盒送进去。
秋菊接了菜盒子一样一样取出摆在桌上,看看,是四甜蜜饯外加四样小菜,有挂炉山鸡、花菇鸭掌、莲蓬豆腐、玉笋蕨菜,一样点心是枣泥糕。对着月儿道:“姑娘,饭菜也还丰盛,快过来吃吧!”
月儿嗔怪道:“秋菊姐姐,菜是公子所卖,哪有我们先吃的道理!”转身对钟离子文道:“两日见钟离公子连救我数次,未曾谢过公子,却有劳公子破费,”说着话便将头低下施一礼。
钟离子文忙退一步,谦道:“月儿姑娘见外了,在下并无他意!”却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月儿见钟离子文如此,知他心底善良,愈加爱慕,看看门外的秋破烦道:“钟离公子豪爽,小女子不便推辞,老前辈何不一起吃?”
钟离子文也道:“前辈坐在院子里喝酒也不雅观,倒不如进屋就着小菜岂不是更好?”说完却又暗自好笑,秋帮主是乞丐的头儿,既然是乞丐便不会计较吃喝时雅观不雅观的
秋破烦将酒坛子抱住,环视一周,大声笑道:“钟离公子客气了,我老叫化子一生就爱个热闹,今天这店里注定是有热闹看的,躲也躲不开,再说这客人不出来我却进去也不是待客之道。”说完便哈哈的笑起来。
钟离子文听他这笑声甚是震人,欲穿人心肺,便知是秋破烦催动内力以声震人,忙回身护住月儿。
月儿武功不及钟离子文,再加内伤刚愈,秋破烦笑声起始顿感头晕目眩,筋脉跳动,整颗心脏似乎要爆破一般,不由紧闭了双眼,忽地感觉一股内力源源不断地从后心输入,霎时便轻松了许多,稍缓一口气,睁眼见是钟离子文,心中感激,报之以微微一笑。回头看看秋菊,见她却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这才放下心来。
院子里,秋破烦仍是不住的大笑,随着笑声几个穿堂的小二滚做一团,个个难受之极。
忽地满屋满院奏起一阵琵琶声,刚猛有力,声脆如碧玉落盘,颗颗威力无比,个个杀气腾腾。
钟离子文心中一惊,暗想道:“听琵琶声,此人内力在自己之上,应与秋前辈相当,这半天时光自己竟全然不知这野店内有这样的高手,怪道秋前辈说有访客!”思量不定,听听琵琶声,旋律甚是熟悉,猛然记起幼时师父常用玉箫演奏过此曲,自己仍是记得的,心中一动暗道:“‘碧落三叠’曲,奏这曲子必然是碧落宫之人,许是刚才打酒时被前辈撞见随了来的,我何不和上一曲,免得秋前辈误会,伤了和气。”忙从腰间抽出玉箫,撵着“徵”声吹起。
月儿听得明白,屋外笑声和琵琶声是在比试内力,先有笑声时便震得难受,后琵琶声响起却便好了许多,细听琵琶声时而压住笑声,笑声压住时而琵琶,便知二人内力应是旗鼓相当。
却又见钟离子吹起玉箫,声音混杂在其中,如长蛇一般缠绕在二声当中甚是震耳,明白是二声比试内力却不防玉箫占了上风。
却听三音声调低沉起来,猛地戛然而止,半空爆响一声,声到之处皆被震动,满屋灰尘飞起。
钟离子文住了玉箫,只见院子里早站了一老婆婆,怀里抱着半人高的朱色琵琶,一身青衣,垂到膝下,雪白银发挽在头顶,一双丹凤眼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秋破烦看看老婆婆笑道:“我道是谁呢,原来是金琵琶圣姑。”说完一屁股坐在地上抱起酒坛子,看看里面已是空了,便将坛口向下举起,仰起头对着嘴,坛子里的酒便一滴一滴落入口中。
金琵琶圣姑回头看看秋破烦,冷声道:“叫花子,三十年不见你,你的功夫可是大增,老身还以为你早死了。”说完回头看看钟离子文又道:“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拿着寒谷子的玉箫?”
秋破烦自顾撑着酒坛,道:“他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你碧落宫的玉箫在他手里,你不问他问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