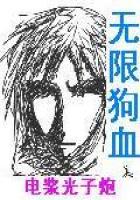朱娸吃得尽兴,等着傅洁开口,如果她吃完了还不说,那她就甩袖走人。视线一角一抹红色慢慢移了过来,朱娸静静的等待它的到来,待看清上面的字时,突然一震,却是强做镇定。
"我和厉轩下月14号结婚,也就是**节,希望你能来参加。"傅洁微笑着将请柬往朱娸面前挪了挪。
"好!"朱娸应得爽快,就好像在和好友约逛街一样,内心的风起云涌被藏得滴水不漏。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厉轩面前,谢谢。"傅洁依旧像个大家闺秀一般,说得十分的温柔优雅,字句却如此残忍,谢谢两个字狠狠刺中朱娸。
"好!"仍旧是一个字,朱娸将大红喜帖放入包中,喝完最后一口西米露,起身走人,傅洁也不在意她的没礼貌,反正,一切就快结束了,她也嚣张不了多久。
"记住你说的话,我手上有什么东西你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哎呀~现在的网络技术真是发展的好啊!"
身后传来傅洁邪恶的声音,最后那句似自言自语的感叹,貌似前言不搭后语,但朱娸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警告。身子顿了一下,然后大步离开。
朱娸走在寒冷的大街上,步子有些虚浮,就好像喝了酒一样,从吃了那碗西米露开始,头就昏昏沉沉的疼,而且越来越严重,心跳也不自觉家,呼吸也有些急促。
朱娸摸摸额头难道是生病了?冬天真讨厌,又让她生病了。不行了,头重脚轻得越来越明显了,恐怕是坚持不住了。朱娸扶住路旁的路灯,顾不了来来往往的异样目光,意识渐渐模糊,一点点往下滑去。
迷糊中几个身影聚集在自己身旁,迷蒙摇晃,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却能感觉到他们扶起了自己上了车,然后便是一阵昏暗,失去了意识。
冬日里的第一抹阳光划破天际,温暖包裹住郊外一间破旧平房。房间里地上铺着茅草毛毯被子,一个女生被包裹其中,没有要醒来的迹象,衣服凌乱的散落在周围,似乎在无声的诉说着过去一夜的往事。
日上三竿,裹在被子里的女生终于动了一下,睫毛颤抖了几下,渐渐睁开眼睛,一点点适应光亮,怔怔的看着天花板,毫无焦距的眼睛里盛满迷蒙。
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个巨大的空间里挤满了黑色,自己踏着黑色在无尽黑色中寻找,却又不知道在寻找什么,只是机械般的移动双腿。似乎有什么摇晃着整个空间,一阵阵的震荡,就好像轻微地震一样。
一阵寒风拂过,朱娸一个激灵,眼眸由空洞渐渐变得有焦距,却在触及那陌生的墙壁时再次怔愣,那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已经将一切都告诉了她,低头,不顾寒冷掀开被子,胸前那一个个张牙舞爪的红印在向她示威。
朱娸僵硬的爬起来,双腿间肿胀疼痛,缓慢的捡起地上的衣服一件件穿上,捡起最后一件外衣时,几个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朱娸盯着这几个方方正正的包装袋许久,突然之间狠狠的踩了上去,蹲下来发疯般的抓起它们丢向一边。一阵疯狂之后,朱娸瘫坐在地上,泪水再也无法抑制,大颗大颗滴落。
昨夜昏迷前的景象,那模糊的人影,那碗西米露和点西米露的人,一切的一切,怎可能巧合得天衣无缝。为什么自己明明什么事都没做,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伤害?贝厉轩是这样,傅洁是这样,就连老天爷也对她如此不公,凭什么?
朱娸对天狂吼,那么一瞬间,她真的不想再痛苦的活着,活得如此狼狈,还不如死得痛快。可是她若不管不顾离去,那妈妈岂不是什么都没了,她怎么狠心让妈妈一个人孤苦伶仃伤心欲绝?
哭得累了,泪水也干了,心死了,情也平复了。慢慢的爬起来,走过去捡起包包,坐在被子上打开,意外的是什么都没丢,反而多了样东西,一张纸条。
"这个礼物很喜欢吧,我就毫不客气的收录你的精彩表演了,祝你一路顺风。"
朱娸冷笑着将纸条撕成碎片挥向空中,凄惨的笑颜如此让人心疼,然而所有的痛都只有她自己承担。突然好害怕,好想找个人陪伴倚靠,通讯录翻来覆去却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找。贝厉轩不能找,而小凌,却一直无人接听。
朱娸放下电话,呆呆的盯着窗外,然后起身缓慢的离开这个耻辱的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