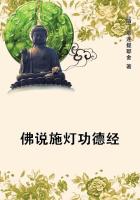她拉着我的手,引导我走出公园。最后我们从一条体面的小甬路离开公园,姐姐说咱们快回去吧,晚上这儿不安全,在这儿溜达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里还发生过暴力事件啊?
不止发生过,还挺经常的。常有人在这儿被抢,甚至被杀。几个月前一个女的在这儿被杀,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还被糟蹋,据说凶手好几个人。
我看她的表情不像在信口胡说,因为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与紧张的神色,她的手也握的紧起来,我于是相信有这件事,但还是有些不明白,压低了声音问她,这儿来来往往的很多人,谁那么大胆啊。
说起来,这的人真不是太多,这里大多是一些小公司,小商店,晚上下班了,关门了,打烊了。这儿住的人主要在那里,她指了指方才我们经过的一栋居民楼,楼上盏盏明灯,像点缀了黄金的象牙块儿,这么远,发生什么事谁听见?就是听见了,谁肯打开灯管一管?
对啊,只要打开一下灯,或用手电筒照一下就可以把坏人吓跑了,因为坏人都心虚啊,这么点小事他们问什么做不到呢?
唉,什么都不懂的小男孩!
我们又走在刚刚繁华一时的街道上,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了,但是还亮着灯,有时可以看见它们的主人在踌躇满志地踱步,留下晃动的身影在明亮的玻璃门上。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在盘旋,于是我鼓起勇气问她,上午那男的认识你是吧?
嗯,这和你有关系吗?
她停了一下,又疾步往前走。我被她牵着,只得相应地一停一走。我再没说什么话,只是看光景,很熟悉的了。
飞向新世界的雕像,如云的头发,飞扬的裙子。
影楼打打杀杀的声音。
那家饭店烟囱仍在冒烟,升入黑色的夜空中,我不禁回味炸鱿鱼圈的美味。
书画装裱,伏案的老头。
被吹得要风干了的岛民,呆滞的眼神,蓝蓝的烟。
黑洞洞的过道,软软的砖。
浓郁的气味,昏黄的灯光。
格子墙,半桶矿泉水。瓷盆,冰冷入股的感觉。
红漆桌,玻璃镜子,秀发,无数盘旋的小蛇。
最后,她说你得几点起床?我说周一早晨有升旗仪式,得早点去。姐姐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姐姐关了灯,黑暗以任何东西都无法企及的速度占领了屋子,仿佛一桶黑色的染料劈头盖脸从天而降。姐姐给我盖了盖脚,屋子里便静的只有气息的游荡。眼睛慢慢适应过来,察觉出屋外施舍来的微弱的光,跳动着,眼前像飞着无数只黑色的蝙蝠。我不断的翻身,觉得腿有些酸,但尽量避免碰她的身体。我怕万一碰了她一下,她触电似的一动,这虽有些滑稽,但忍不住笑起来不免有些轻佻。若不笑,憋着又难受,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困倦迷迷漫漫而来,它消灭了我体内的冲动,并且将我的意识的扁舟笼罩,令我招架不住地压下来,我进入了梦乡。最后我残存的意识告诫自己,睡觉老实点儿,千万不能滚到她身上去。
夜深沉。
事实上第二天我就向班主任提出走读的申请,班主任是个矮胖的人,正如他所讲的数学,他处事的方式总是充满了逻辑。他的前瞻性的从容————那其实是一种自信————用他的方法总能或曲折或顺利地推导出结论。因此他总是不急不躁,按部就班。
我虽然看上去有些心急,但向这样一位老谋深算的老师提出申请毕竟需要很大的勇气。
怎么回事儿,住不惯宿舍还是宿舍纪律差?他戴着阔边眼镜,但看他的学生,却从来不通过眼睛,而是扬起眉毛从眼镜的上方看,很幽默的样子。
我在这儿有一个亲戚,她说冬天了,宿舍冷。。。我支支吾吾地说。
冷都冷,不能因为你一个开了头,都爱上哪儿住就上哪儿住。再说冷对你是一个锻炼。见我不支声,又说快回去吧,好好想想。又看了我一眼,手一扬,说快回去看书去!我出了他的办公室,满脸的沮丧。
我想起了我昨晚的梦,好像是我回了家,爸爸妈妈,奶奶,三叔等人一股脑儿梦过一遍,至于情节,说不清楚,乱七八糟的。
我于是给家里打了电话,妈妈接的。她高兴地说让我回家一趟,捎点苹果回来,又说城里苹果贵,想吃不舍得买,正好家里苹果下树了,还是个丰收年呢。我说星期六我回去,还有六天。
打完电话,我仍然保持着对电话的新鲜感。家里的电话是刚安装的,妈妈说方便和亲戚联系,再是我在外读书,将来上大学,有个什么信儿,就必须得有电话。于是爸爸去报了名,安装电话。那号码是别人家的,那家人搬外地了,把号码转继给我家,那个号码我研究了一下,虽然表面上没有6啊8啊的,但是把数字两两加起来,整个号就成了三个8。我也是根据这三个8迅速记住了家里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