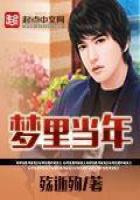眼看着夏侯府的车行慢慢消失在人海车群中。萧确方转头对厌说:“晋南王行事风格真是另类。连个内侍护行都不带。若碰到歹人盗贼,可是把皇室贵胄的脸面丢尽了。”
厌还没从夏侯云重莫名敌意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只低落道:“天子脚下,有何惧怕。”
萧确的双眉便立起,怒道:“这话若我说还罢了。可你这样懦弱之人,就该学着临城公、衡山侯他们,自重自保。”
厌刚要说话,突见前方人群骚动起来,呼一下涌将过来,将几人都挤得立身不稳。萧确家奴护着他只向后退,随后就见有数匹怒马奔来,将闹市的人群商贩冲得七零八落,惊叫声不绝于耳。怒马冲开路途后,又有几匹慢马随后而来,马上武士手中拿着皮鞭,抽打清理着躲避不及的行人。然后才有奴隶来立杆支起幕帐,那些奴隶们锦衣华服,左颧骨上都烙着一个醒目的“贺”字。萧确与厌被拦在幕帐外,与人群挤在一起。
萧确便道,“这临贺王!平日排场就罢了。节日里也如此做派,可不是扰民。”厌也知道这临贺王萧正德,此人本是六叔祖临川靖惠王三子。在幼时曾过继给当时尚无子嗣的皇祖父,待后来父亲与诸位皇叔相继出生,便又命复其本家。但是皇祖父仍已慈父之心待其如已出,很是宠爱,也三番四次包容其罪过。所以,实际上这位堂伯父的地位与众皇叔父不相上下。
萧确忍无可忍,命家奴冲开人群,拼命向前挤行,厌也便跟随他前行。萧确扯断了幕帐,一只脚刚踏上官道,临贺王府的豪奴便执木杖拥上。萧确的侍从在京中也有凶悍之名,便拔剑迎上,口中喊道:“永安侯在此!不要命的就来受死!”
那几名临贺王府家奴大概也知永安侯萧确之名,便放下了木杖,但仍拦住不放行。
两相便僵持着,只听得帷帐后有孩童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一位临贺王府奴官便吩咐,去将嚎哭的孩子扔远些,别让王府贵人听着烦心。有两位家奴得令去了。厌见那些豪奴只向着孩子嚎哭的地方狠踹了几脚,孩子哭声未止,又添成人的惨叫。又见他们掀开幕帐,也不细看究竟,手执木杖便向里猛扎。厌顿时火冒三丈,边高声喝止边向里行。厌这一冲,临贺王府的家奴便和萧确的侍从交上了手。临贺王府的奴隶哪里是萧确随侍的对手,只片刻就都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去寻孩子的两个也跑回来助战被打倒在地。
厌忙掀开帷帐看那孩子,果然见一个角发的男童夹在人群中号啕大哭,手指还死死拉着一个男人的裤褶。那男人有些惶恐的掰着孩子的手指,口中嘟囔道,我不认识这孩子。厌见周围人都神色冷漠,似都不是这孩子的亲人。便走进去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那孩子似乎也很害怕厌,又不敢反抗,只哭得快要背过气了。厌仿佛抱着一个烫手山芋,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助萧确。萧确瞪眼看他,口中道:“你,你抱他出来做甚?”厌只好说:“堂兄,您能不能命随从抱孩子去寻他家人。”萧确瞪视他片刻,终于妥协,无奈命一名侍从接过孩子。那侍从似乎不太相信听到的命令,边看萧确脸色,边犹豫不决的伸手。萧确立眉怒喊一声:“快去!”那侍从才迅速接过孩子,钻进了人群。
临贺王府的先行内官下马察看状况,王府武士也围了上来,见是萧确几人也不便处理。片刻后,临贺王萧正德的依仗车队便滚滚而来。行到几人身边时,华盖主车停了下来。车帘卷起。座中人金冠华服,豹目鹰鼻,正是临贺王萧正德。
萧确与厌上前行晚辈礼。萧正德笑道:“我说是谁呢?只有仲正贤侄你敢踢我的场。”
萧确朗声道:“小侄莽撞冒犯,又伤了几名奴隶,请堂伯父恕罪。”
萧正德笑道:“仲正贤侄是我萧家的武曲,那几名奴才死在你剑下也不算什么。”
萧确道:“多谢堂伯父宽宏大量!”又笑嘻嘻说:“节日里连圣上都登门楼与民同乐,堂伯父也该下凡走走。”
萧正德笑道:“正是呢,我在玄武湖瀛岛边上摆上楼船阵,酒肉佳肴随百姓取用,你们也随我玩玩去。”
萧确笑道:“能有船登上瀛岛的,定也非平民了,哪里还需要您的布施。”
萧正德哈哈一笑道:“你也会说这话,这京城的僧人、寺庙都富得流油,圣上不还是带着百姓布施。不过是心到佛知罢了。”萧确也哈哈一笑。
萧正德又打量厌:“晋南王可是又长高了不少。果然昭明太子的儿子个个都身量高,又都封王爵。”说完又是几声笑。厌面色恭敬严肃,默然不答。
萧正德又笑道:“你兄长岳阳王可好?”厌只闷声答好。
萧正德便说:“晋南王心内可是有不快之事?说出来听听,看伯父能否帮你解忧。”厌便低声道:“堂伯父家业广大,家奴众多。难免会有刁奴仗势扰民,损害堂伯父的民声众望。还请堂伯父管束家奴部曲,莫闹市纵马,莫虐伤人命,莫劳民伤财。”萧确面带讥讽的斜看了一眼厌。厌又一次不合时宜,失礼逾矩了,那句劳民伤财哪是说奴隶,分别指责了长辈临贺王。
果然,临河王萧正德面上露出怒意,只道:“你还在乳娘怀里时,我王府家奴便如此做派!你如今真是长大了,竟敢质疑长辈的治家之风。你这目无尊长的风格是在哪家学的?”厌还要开口。萧确忙道:“他向来言语不经心,堂伯父莫生气。不过您府上的马匹武侍真是豪壮,不与别家同。可是北驹北奴?真让小侄羡慕。”
萧正德这才神色稍缓:“北马粗烈只配奴隶骑乘,哪有咱们南朝的矮马金贵温驯。不过,你若喜欢,伯父这就送你一匹北驹,你留着玩玩吧。”
萧确便笑谢,又道:“我可要亲选,若选了伯父所爱,您可不许舍不得。”
萧正德朗声大笑道:“随你选,选中哪匹,我立时让马上人下来。”萧确便果真去挑选。
萧正德便也对厌说:“七贤侄,你也去选一匹吧。你还未满周岁时,伯父就看过你,这骨肉亲情岂是说忘就忘的。”厌只得道谢,也随便选了一匹。
萧确与厌牵马在路旁看着临贺王府的车队经过,赫赫扬扬足用了半个时辰才通过。萧确看着厌神色依旧不佳,便说:“大丈夫当立志豪阔,若拘泥小节便是腐儒妇人之态了。”
厌却说:“小仁尚且不全,大志也是空谈。”
萧确气道:“你怎么总是这样论调?我们萧家怎么就有你这小家败气的子孙?”
厌冷然看他道:“身为皇家子嗣,若不知自律爱民,多大的家也得败了。”
萧确气道:“你以为皇室子孙就你一人懂齐家兴国。是就你一人成日里挂在嘴边。”
厌又皱眉道:“您的侍从出手也很凶狠,那几个奴隶不过是遵主命行事,何至于伤其性命。”
萧确忍无可忍,怒道:“要不是他们,你能连剑不拔还毫发无伤?就你这样不自重早晚有被贱人侮辱那天。你自己不顾脸面,别连累宗室姓氏跟着名誉扫地。”
厌也道:“我按自己心中的准则言行,一切后果自然由我一身担当。”
萧确怒道:“我平生最恨嘴上功夫滴水不漏的伪君子。有本事咱们见见真功夫。”
遂指着前路道:“临贺王现成的路障直铺到玄武观。咱们现在就比比。一样路况,一样光线,一样生马,看谁先到玄武门。”说完翻身上马。
厌却不动,只说:“这有什么可比。”
萧确怒道:“少废话!上马!我若赢了,今后只要有我在,你不许说一字什么家国高论。你若赢了,随便你说,我再不驳你。”
厌也意气上涌,据鞍翻身上马。
两人一对视,同时打马。两骑北驹便似离弦之箭,扬尘并行飞奔。萧确窄袖劲装,身姿十分轻便,但因本怀轻视之心,自认胜券在握。行不多时,见厌只落后半马身,骑术实不算弱,便狠急打马。厌身穿长袍大袖的正装,身姿很是累赘。但好胜心已起,也拼命跟随。两骑几乎紧贴而行,虎虎生风。眼见玄武观已在眼前,两骑依然相差不多。城门官道上,临贺王的幕障已经收了。行人见高头烈马疾驰而来,纷纷避让。两驹便直冲进玄武门,可城门里行人却来不及避让。厌刚过门洞便已醒悟,忙强力收缰。马受惊后扬,厌直跌到马下,顿时一阵剧痛袭来。几乎同时,就听到城内门一阵惨叫惊呼,厌不顾己伤,忙奔向内门。就见内门也是人仰马翻,萧确躺在马身侧,旁边还躺着一位门吏。萧确挣扎着起来,满面痛苦状,也是跌的不清,而旁边的门吏却满头血迹毫无动静。
萧确看见厌,却似找回了力气,几乎跳起来对厌怒道:“这回不算!不超你两马身都不算赢!下次再比!”
说完怒气冲冲的拉过马身,又咬牙挣扎着爬回马背,拿出身上的名牌扔给站在旁边不知所措的另一位门吏,道:“好生医治受伤之人,明日到邵陵王府领赏!”说完打马离去。
厌这才发现自己膝盖上的血迹已经透过了裳裤,身上又有好几处传来剧痛。他慢慢回身牵起马疆,默默向同泰寺走去。
次日,御史中丞弹劾两位皇孙。然而罪名非闹市纵马,骚扰平民,撞伤门吏,而是纵马驰骋,性情狂暴,有违圣人教导。此非针对皇孙,当时所有贵族,凡纵马者均会被以此缘由弹劾。因南朝以优柔温润为君子相,以心慈面软为贤者相,凡有暴戾凶恶之苗头,必予以重罚。故南朝贵族无人敢当众骑马,便是行猎时骑果马,也不常任意驰骋。而使部曲驱赶猎物至眼前,方射之。且常常箭无尖锋,以示慈悲。厌与萧确两人,也因此事,各自领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