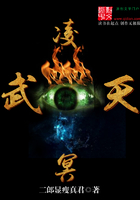一张巨网封住了去路,路中一个小门,网后布满了弓箭手,齐齐整整几百号人,同时站起,弓拉满,待号令下发同时射出,四个人将变成筛子。
杜二道:“列位请慢,我等有通行令牌。”说着右手拿着令牌高高举起。
为首的大胡子直至耳根,右手一伸,道:“拿过来,我瞧瞧!”说话神气无比。
杜二将令牌掷将过去,大胡子看过后,交与左右,又翻看了一番,均都点头。
各人闪在两旁,大胡子打开门,抬头高声道:“过去吧!”
四人前行,翻过山岗,又下一个小坡,面前出现一座山峰,山峰直上下,两条链锁自上而下。
杜二拉过锁链用力拉试,铁链铮铮想了几声,漱漱尘土下落。
杜二回头看看这三位,呵呵一笑,道:“华兄弟,我先上,你随后”
没等华中月回话,杜二已经向上攀爬几丈之高,再看时,已成一个黑点,片刻间杜二不见了踪影。
华中月看了看铁链,用手拉了一下,铁链几乎没动,他只感觉这铁链甚凉,应该不是寻常材料打造的,只听后面哧笑一声,原来是杨岩看他的样子,眼里甚是瞧他不起。
杨岩道:“华兄弟,你还是在此等候吧,我们先上去。”话间没正看过华中月一眼。
华中月也是呵呵笑了一声,道:“别眨眼睛,看清楚了。”
这话刚一出口,华中月右手一搭铁链,那铁链仍是一动不动,可他人却已是几丈之高,再一纵身,杨岩只能看见一个黑点了,他的笑也凝聚,因为他只听说过飞檐走壁,这次是亲眼所见了。
华中月上得山来,出现面前的是一个五层楼阁,再看四周,荒凉一片,却寻不见杜二的身影,想必是已经进去了。他也没有多想,也健步走上前扣门,门内无应,他轻推门扉,门没锁,吱的一声开了,正对着楼梯,右边是一红帘掩盖的床,左边是妆夯等物。
华中月道:“晚生冒昧打扰,有人吗?”
只听床里传来女人的呻吟之声,华中月连忙道:“误扰清梦,晚生告退”,说着就要退出房门,正要退出之时,“且慢,既然来了,何必那么快就走”,床里传来娇弱妇人声音。
床帘开处,一只雪白的腿穿着秀花小鞋露了出来,华中月看向楼梯,显得不自然了许多,不知如何是好。他从来都没有正视过女人的脸,更别说腿了,这些年来的寒窗,养就一身浩然之气,更是非礼勿视。
那女人道:“相公是何许人也,何故到此啊?”
华中月听着声音抚媚,穿着妖娆,本就知道这是守关者中的一位,见此情景更加谨慎小心。
外表透出来的刚强并不是无懈可击,棉里藏针才最叫人无从下手。
华中月定了定心神,将所有的礼节全盘抛却,正视这女人,下裙短不过膝,上身只肚兜不护体,两条小腿和手臂完全裸露,眼神里带着微笑,摄人心魂。
华中月道:“晚生误到此处,朋友走散,来寻朋友。”
那女人道:“朋友?什么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华中月道:“是一位中年男士。”
那妇人道:“哦!是男朋友,那就是没有女朋友?”
华中月道:“同行只我二人,并无其他人。不知是否来过,还请明示。”
那女人道:“你既然没有女人,那我做你的女人怎么样?”
华中月心想这女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只顾自的说词,根本不回答自己的问题,说不出来一个结果,心想不必在此浪费时间,还是去二楼看看如何,是不是杜二哥已经上去了。想着也不答那女人话,径走向楼梯上走。
那女人看华中月不回自己言语,径直走向楼梯,连着呵呵呵呵笑了几声,道:“你要走了?”
“嗯”华中月脚步没停,嘴里应了一个字。
那女人道:“可惜,你走不了的。”
华中月这次没有说一个字,脚步却停了下来,心想这女人想必不是在开玩笑,这黄红岗上哪有吃闲饭的人,这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只是表面,这楼阁的第一层定是她守着的,过不了这一关,这二楼是肯定上不去的了。
那女人续道:“因为你的命从进到这个房间里就已经死了。”
华中月听到此话,身后一片冰凉,但他迅速转为镇定,经历过这么多,他已经学会了在新环境中学习和适应,因为一面是生,一面是死,他想要活着,就必须克服自己种种恐惧,恐惧源于无知,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的黑洞里将问题想像的无比强大,将自己显示的无比渺小,最后被活活的压死,大部分人的死就死于自己的心灵,心先死,身后亡。
华中月冷冷的道:“可是我现在还活着。”
那女人道:“你也说了,是现在,过了现在你就会死。”
华中月道:“只要活着,现在就永远不会过了。”
那女人道:“我需要男人,你要想从这里活着出去,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做一回我的男人。”
华中月看了看她,从上到小,仔细打量了一番,摇了摇头,叹了一声。
那女人道:“你看不上我?”
华中月道:“我看得上你的人,但看不上你的心。”
那女人道:“人是可以看见的,但心是看不到的。”
华中月道:“看的时间久了,人就是看不清了,但心却看的越来越清。”
那女人的眼神里已经不见了原来的抚媚,两个眼睛冷若寒冰,整个人也凝固了,华中月心神一紧,知道她要出手了,因为她的确说不过自己,她的人生活的还没有形成系统,无法自圆其说,而愤怒之后,必将会大起杀意。
华中月道:“你如果再不动手,我就要走了。”
那女人依然没有说话,华中月摇了摇头,向楼梯走去,还差一步就踏到楼梯时,一道寒光出现在他面前,华中月侧身闪过。
华中月转过身,发觉自己被一个人抱住了,抱得很紧,他想挣开,却无法挣开,那女人道:“不要走了,做我的男人吧。”
华中月脚尖点地,身体一纵,向后倒去,那女人迅速离开,华中月右手在地上轻轻一划,重新站立,那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紧紧贴住他的前胸,道:“抱着我,抱紧我。”
华中月用力将他推开,那女人被推开后,又回到华中月的胸前,他再推,她再次被推开,但只要他的手一缩回来,她就又抱上来。
华中月双手将那女人震开,使了一招飞檐走壁中的风卷残云,那女人再想贴在他身上时,无从下手,华中月整个人像是旋风一样,在空中旋转。
华中月心想这种打法无法取胜,这女人根本没有使什么绝技,她只是贴着我身前身后,就令我恼羞成怒,对,让我恼羞成怒就是她的目的,心乱而神慌,比武比心。
华中月站立,目不转睛,他看着这女人,这女人也一动不动,他心里清楚,她在等他动,他动就会被她跟着走,所以华中月也一动不动,那女人看自己的技俩被识破,右手出现一枚金针,极短极细,笑道:“我这个人,最怕见到血了。”
华中月哼了一声。
那女人道:“但我又非常喜欢杀人。”
华中月道:“那你还怕见到血吗?”
那女人道:“怕,怕极了,但是我又喜欢杀人,也喜欢极了。”
华中月道:“哼,杀人不见血?”
那女人拍手道:“你还真是聪明,对,杀人并不一定见到血的。”
华中月看着她手里的金针,心想:这种暗器,如果在打入人的穴位上,的确见不到一滴血就可以将人杀死。
女人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手里不死无名之辈。”
华中月道:“你没有机会知道了,因为你根本杀不了我。”
女人已经愤怒,道:“狂妄之极!”
那女人的脸开始狰狞,只听嗖的一声,这声音微弱极了,就像蚊子的声音,不在暗夜里根本无法听见。
华中月有意激怒她,他听师父说过,使用兵器越小的人,技巧越是高难,越是需要平和心态,如果心境不处平常,则使用起来不仅极难伤到敌人,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华中月身悬半空,针从身上滑过,针还在那女人手里,原来针上有极细的细线,当针飞出后,再用细线将其拉回。
针从四面八方飞来,华中月左避右闪,上下翻飞,躲过针,还要避开针后的弧线,被一个碰到,非死即伤。
华中月灵机一动,轻飘飘落在地上,不得不说他的轻功是这女人见所未见过的,那女人也没有出手,也是欣赏了一番,立定神后,她的针又一次脱手而手,像一枝离舷之箭,速度之快,目光不及。华中月冷冷的站在那里,仿佛在接受着死神的宣判,那女人也是一愣,他怎么一动不动,躲也不躲,难道是想找死,还是先前已被我刺中?
针离华中月不一米,只见他右手的笛子轻轻在眼前一挥,笛子又在他的手里转了几圈,那女人情知不好,急忙拉线,华中月手里的笛子又在飞速的旋转,细长的线在笛上已然缠绕出一个细棱。
那女人再向后拉线时,华中月只是不动,她自然无法拉动,华中月哈哈大笑,那女将另一端脱手而出,华中月应声而倒。
那女人哈哈哈哈大道:“蠢男人,活该你死。”
那女人来到华中月身前,从身抽出一把匕首,上前要割掉华中月的头,华中月整人向后平滑然后站起,道:“好恶毒的女人。”
那女人道:“哪里恶毒?”
华中月道:“人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割掉头颅?”
那女人道:“人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留着头颅?”
华中月只知道这个理论不对,但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于是也答言,只是道:“我不想杀你,只想从这里上去。”
那女人道:“你不杀我,怎么从这里上去?”
华中月每一次胜出,都不出杀手,那女人也不依不饶。
那女人突然道:“我现在给你第三个选择,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上来,便不再与为难。”
华中月道:“好,一言为定。”华中月心想,十年寒窗,别说一个问题,就是十个一百个问题,我也都能回答的让你满意。
那女人眼睛突然空洞,生无可恋,道:“人为什么活着?”
华中月的心也沉重了,他的确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但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突然之间,他仿佛什么都不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人为什么活着,他也在问自己。
那个女人看着华中月怔怔的出神,默默的道:“我原来自以为,人为了快乐而活,从我这个房间里走出去的人,无一不是和我睡过觉的人。”
她续道:“要么和我决战,被我杀死,但没有人选择这条路,要么和我睡觉,这些人中,要么直接就钻进我的床里,要么就是和我决战后再钻进我的床里。那时我以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快活。”
华中月直直的看着她,怔住了,他看不起她这种女人,他帮不了她,因为他回答不了她的问题,她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者是微薄的认识,但无论如何,这种追逐都将不会有结果,这种追寻注定没有答案。华中月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
突然一支血注喷涌,她最怕血,但她选择了死,连死都已经不怕的人,就不会再害怕其它任何东西。
华中月怔住,许久方醒,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轻易的选择死。
有些问题本就不该问的,不该问别人,更不该问自己,因为有些问题的答案,想不通,活着苦不堪言;想通了,也就不想活了,有些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