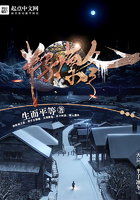在一片静谧的大海上,海面如镜,映衬着幽蓝的影子。
甜美的歌声响起,似乎在倾述着她的故事。
许啸站在沙滩上,望着那抹鲜艳亮丽的蓝,那是少女的彩裙,蓝中带着一抹墨黑,那是少女乌黑及腰的秀发。
许啸听着那如同新生儿初次尝到母乳般甜美的歌声,看着那令他向往的背影,不由地痴了。那甜美的歌声疯了似的化作了一道道有形灰黑色的音符朝着许啸砸去,许啸还未回过神来,就被砸了个正着。随即便沉入了第二个梦乡,在那里,只有静穆的黑暗,这使得许啸睡意愈发昏沉了。耳边再次响起了那位少女的歌声,而这歌声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小黑屋,打开了许啸尘封的心。
许啸睁开了眼,看见了阳光,来自窗外的阳光,阳光很刺眼却带着他遥不可及的寒意。许啸伸出手,想要触及那来自窗外的阳光,而寒意却沿着他的手漫溢入心。
许啸缩回了手,拿手紧紧地捂住眼睛,手上的青筋慢慢变粗,手掌不停地随着眼睛微微颤抖。许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明明知道哭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可眼角的泪水却一个劲地往外流,似乎这眼泪并不属于他,它们推着挤着要夺眶而出,它们快乐而汹涌地从许啸狭窄得连自己寒毛都容不下的指缝间流出。
许啸不知到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不堪,在一场不知所云的梦后,在梦醒时分不知所以的哭泣。或许是因为寒气冻厉了他,或许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做梦,或许是因为这梦中的少女是他这几年来唯一一个陪他度过漫漫长夜之人,再或许是因为在他以前的岁月里从未出现过眼泪……而今日,终于泄洪。
许啸慢慢松开了手,任泪水顺着他那线条感十足的脸庞簌簌流淌。他慢慢地在床上半坐,半弯的背部轻轻地靠着床屏,眼泪从他的脸庞滴落至被黑色被套套上的白色蚕丝被上。许啸突然猛的一下势欲起身,上半身挺直得如同一把未开刃宝剑,而宝剑传来了磨锋之声——许啸重重地给了自己左脸一个耳光,耳光的“啪”声在这栋空旷的别墅内传得极为悠长。
耳光止住了许啸的泪水,却止不住许啸的冷酷。
他的面容又恢复到往昔,俊俏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却就能给人一种自己与他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感觉。他似乎有一股寒意,如冰神一般;一种杀机,如杀神一般。
许啸伸出修长的手拿起放置在床边的、散发着淡淡木药清香的、泛着乌黑光泽的、龙形的、人高的、棍状的乌木雕塑上的白色的厚浴袍,将它套在他不着半褛的肌肤上。
起床,许啸踩上白色的厚拖鞋,走到对着床的那个射进阳光的窗户处,推开纱窗,窗外却飘着星星点点的小雪,将头伸到窗外,抬头看见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以及小黑点与小黑点空隙间的阳光。由于窗户上方有一个龙形的华丽窗檐,雪花并没有落到他的身上。
今日的阳光不及夏日那般刺眼与炙热,也不及冬日那般刺骨与严寒,它带着一股别样柔和,一股别样的震慑。许啸伸出修长手,一粒小米状的小雪轻飘飘地落在了他的手上。
“难道这就是妈妈所说的晴雪日吗?,原来世上真的有这么奇怪的天气。”
“妈妈,你说过,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天气出生的,你说那日天空晴朗,天上却飘着小雪,你说那叫晴雪日。而我如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天使在那日降临,你说那日后,你改变了很多,他也改变了很多,妈妈,你和他现在在哪?我当时不信,以为你是骗当时年少无知的我的,现在我信了,你和他会回来吗?你还没有告诉我名字的由来,你说要在我十八岁成人礼的时候告诉我的,可你和他都没有来参加我的成人礼,而我的十八岁已经过了一年之久,可你还没有告诉我答案,我等了好久,门前的那棵载着我们一家人幸福回忆的小梨树的腰都长得比我粗了,个头也长得也比我高了,它结了好多果实,我一个人都吃不完,你和他快回来陪我吃吧。”不知不觉间许啸说出一段自己都觉得幼稚的话。
许啸突然变得呆滞,似乎沉湎于过去美好的回忆之中。
片刻后,充满磁性的特色嗓音又轻声低语:“是否我也将在这样的晴雪日之后改变?我不愿改变。”
而人的内心往往是不会骗人的,其实他真的很想改变自己现在一尘不变的生活,重复着上课下课,上学放学一个人孤独的生活,而他生活的最主要的部分,只剩下学习。其实他想要的生活,哪怕是现在变得只有当初生活幸福的十分之一,他都会欣然接受,而且也不会变得现在这般,冷酷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了。或许他现在所需要的是一颗太阳,而这颗太阳的光一定要发得亮,发得炙热,发得久,才能够融化他这颗不知何时被自己一步一步的悄然冰化的心。
“一切都回不去了。”许啸对着窗户放声长啸,啸声断断续续的向前方传播,似乎空气都对他的话表示认同。
许啸看向掌心的雪花,对着这个没有生命的雪花一反常态异常温柔的说:“对吧,小雪花?”小雪花回应了他的话——消融在他的掌心。许啸青筋四起,紧紧地的握住了这滴雪水,而雪水在他的掌心消失的无影无踪。
刚刚对小雪花说话的人的脸色从异常温柔秒变高冷,他关上了窗子,拉上了灰黑色的床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