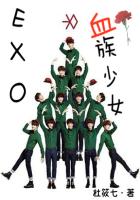她的母亲极其喜欢风信子花,窗台上叮叮当当放着玻璃瓶子,就为养那几株花花草草,有时放书的地方被占满了,刘氏就把手中的书随便放在一旁,欢天喜地的找别人家的孩子玩。
那是一个春天,按照惯例鼻尖缭缭悠悠弥漫花香,刘氏又逃出门。
“小氏你给我回来看书!”父亲的吼声是最准时的。父亲不准她做一个无能的人,父亲初时想当个文人,他的书房有琳琅满目的毛笔台砚,就是不准她碰,好像就怕弄坏了他的宝贝疙瘩。
“我不要!”刘氏扭头对父亲挥手,头发上的簪子是随便插上去的,弯弯扭扭算是绕了个结,不至于散下来弄脏头发。转身又对身边的女伴说:“今天山上是不是有庙会?”
女伴叫小芽,声音婉约,轻轻柔柔地好像相隔天涯,又像近在咫尺,你不想听也能钻到你的耳朵里,让刘氏经常想起风信子的花香,听到了:“是呢,清河寺有庙会呢。”
小芽是父亲当初捡到的,听他说过,当时的小芽小小一只,数九寒冬里身上一层薄薄的毯子,被冻的硬邦邦的,来不及想是谁家的父母如此狠心,就把小芽抱回府,外面是寒冷的冷风,雪不愿意出来,因为脆弱的雪花与之比实在太柔软。
庙会人群熙熙攘攘,不知道是哪个戏班子建起的一个平台,叮叮哐哐是锣鼓的声音,震得心一颤颤的。
“走吧,”小芽拉她的衣袖,力道很小,引起刘氏注意的还是那布匹打着风的猎猎声响,聒噪不能宁静,致远更与之不沾边。小芽的脸色是死白的,发梢在轻颤,像是惊的:“走吧,不要在这了。”
刘氏不置可否,她常会有这奇怪的时候,说来就来像七月的风雨,来的让人猝不及防,走时却又悄无声息:“你又何事?”
“走吧……”声音细小,再好的东西,盯久了,也是会厌的,好比小芽的声音。
“好好,走了!”刘氏烦躁说,任谁被打断都不会高兴。
“谢谢。”又是那种小小的声音,数十年如一载地听着,真的是厌了。
“嗯嗯,知道了。”刘氏说,不甚在意的语气让小芽搅起了衣服的袖口。
湖边。
还是春光。
今天刘氏很不舒服,手里端着的茶水凉透了,脸映在水里,细碎的星星点点的茶沫也应在茶水之上,就像洗不掉的麻子。晦气,刘氏摔下茶碗,咣当一声了砸碎细瓷茶杯,终究还是碎了。
小芽弯身去捡地上的碎片,鞋面踩在碎瓷上有破碎的声音,想捡起来,却又因为太细碎而扎了手,只能用手绢把大的碎块包好,略带歉意看向坐在后面的掌柜:“对不起……”
掌柜看着那一堆碎片,肘上撑的算盘打的噼啪作响,之后才晃悠悠说:“收你二十个铜板。”
“二十个?”一般的碗怎么可能会卖二十个铜板?
“你爱交不交。”掌柜端着的算盘向桌上一砸,引的四周的茶客们纷纷侧目。
“我来交吧。”从身后走来一个人,是个男子,温润如泉中玉。罩着一身素雅的纱衣,袖口针脚细密够勒出繁杂的纹路,头戴银冠,眉眼素净。
好干净的一个人。这是躲在后面偷看的刘氏对徊泽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