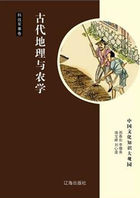值此国事危急之际,天子知道以杨忠的能耐,是应付不来的,只好勤政起来。
今天,小朝会,侍中沈盈、李知本,中书令杨忠,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奇,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程节等人都到了。
小朝会在偏殿里举行,地方略小,但比大殿舒适得多。
天子坐在御座上,杨忠、沈盈、李知本坐在小凳子上,刘奇、程节则站着。
旁边放一个沙盘,上面有山川地理模型,由能工巧匠所制,略具形势。
沙盘里,插着旗子。黑色的代表朝廷大军,白色的代表反贼和叛军。
白色旗子遍布黄河北岸、淮水北岸以及河南道东部,而黑色旗子则在洛阳附近,以及黄河南北两岸。
刘奇知兵,自从郭敬死后,兵部尚书空缺,他以侍郎领尚书事,拜同中书门下三品,可以参与议论政事。
他说:“据报,反贼黄密正在渡河,而反贼高翔则被朝廷大军困死在黄河北岸,指日可灭。那时,十万大军一起东进,要剿灭叛军不费吹灰之力。”
“为何现在不东进?”杨忠问。
“还是谨慎一些的好,毕竟是……那个人的部下。”
刘奇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众人都知道那个人就是指宋融。天子不喜欢听到他的名字,每次听到都要生气,故而就以“那个人”来代替。
“宋……那个人的部下又有什么了不起?他都被囚禁在木笼里了,还能怎样?”沈盈非常不满,好歹在这里的是满朝英才,杨忠不算,岂能怕一个被囚禁在木笼里的人?那不是笑话吗?
刘奇咳嗽一声,不敢多说。万一败了,就是他的责任,他宁可稳重,也不愿意冒险。如果有人要冒险,就让他出头好了。将来出事,算到对方头上,反正不会找到他。
沈盈按捺不住,走上前,接过刘奇手里的细棒,指着沙盘说:“北岸,朔方军和范阳军对付反贼已经足够。只要稳稳守住,反贼蹦不到天上去,必死无疑。”
“南岸,朝廷六万大军滞留在此,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向东进,逼迫叛军。否则,白白延误战机,让叛军四处攻城略地,日益壮大,这简直就是……就是……平庸。”
他说到最后,本想说“简直就是纵敌”,后来觉得这个词太重,就想改成“无能”,然后觉得还是太重,就改成“平庸”。
天子连连点头,六万大军坐视叛军壮大,实在是太过拘谨了些。
刘奇往后一缩,不说话。反正他只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不是尚书令,没必要与沈盈争锋。
远处传来钟声,众人都听到,同时抬起头。
这些钟只在紧急的时候才敲,例如前方送来加急的奏报。
钟声从很远处传来,渐渐地越来越近,当然是近处的人听到钟声,立即敲响种。直道上的行人车马急忙回避,将道路让给报信的使者。
天子和大臣们无心说话,纷纷走出门外,向宫外看去。他们当然看不到什么,但是不免暗自揣摩。有人猜测反贼被剿灭,有人猜测反贼投降,有人猜测出了意外,但意外究竟是什么,他们又猜不到。
一骑从直道上奔过,来到宫门前,高举一个盒子大喊:“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前线战报!”
禁卫们早就准备好,连忙打开宫门,让他闯进去。使者跟随着带路的内侍,在宫内策马疾驰,一条笔直的大道上,空无一人。
高士早就等候在玉阶之下,使者到了玉阶前,翻身下马,滚落在地,顾不得疼痛,连忙将盒子递过去。高士接过,转身就跑,磕碰一下,摔倒在地。左右的内侍连忙将他扶起,拽着他往上去。
高士紧跑几步,跟上步伐,来到宫殿外,将盒子高高举起。天子一把抢过,懒得查验封口,打开来,撕开信封,抽出文书,一看,勃然大怒,随即大笑。
众人看着他的脸色,暗自揣摩,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如此发怒,又让他如此大笑呢?莫非,前线大捷?
看了看大臣们的脸色,天子将文书交给杨忠,杨忠大喜,这表示他依旧受宠。
大臣们看了文书,都笑了起来。
高士没有资格看,但有资格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抓住一人撬开他的嘴巴,让他说出来。
杨忠说:“这个全禄,胡闹!”众人听了,又笑起来。
高士向杨忠打个眼色,杨忠会意,说:“全禄好歹也是一方节度,怎么脑袋还是不开窍,明明是反贼的反间计,他却以为自己了不起,拼命给自己吹嘘,以此要求升官,岂有此理?”
高士明白,想到全禄的傻样,偷偷捂住嘴,笑了。
天子摇摇头,回到御座,说:“你们想个处罚,让全禄安分些。不过,北方确实有些艰难,他每战必奋勇在前,受伤十几处都不退下,难为他了。让他……节度河北道。”
杨忠等人面面相觑,心想:我的乖乖,还真是升官了?!
过了片刻,天子问:“宋融,现在怎么样了?”
大臣们纷纷摇头。
天子微笑,对高士说:“你去看一看,如果他有悔意,肯服输,就给他换个舒服点的地方。如果他还是嘴硬,就将他带来,让他看一看现在的形势,我想听一听,他还能说什么?”
高士领命,当即去了。
来到御史台外,看到杨勖,高士立时明白,杨妃来了。
杨妃走入御史台牢房大院,那里有一个木笼,宋融站在木笼里。木笼不高,他站起来,直不起腰。他就弯着腰,歪着头,向外看,姿势十分古怪。
木笼外,放着一个破碗。碗里有一摊黄水,还有两块手指大小的黑色东西,看不出来是什么,发出一股馊的味道。
宋融伸出手,手指很脏,黑乎乎的,要拿破碗。狱卒头目老豺伸脚去踢一下破碗,破碗发出几下脆响声,远离木笼。宋融把手伸得笔直,肩膀陷入木条缝隙,侧着头,脸被木条挤压得变形,还是够不着,只好收回手,坐下。
杨妃咳嗽一声,老豺等狱卒回头看去,连忙退开,低头看地,不敢做声。杨妃走近,提着裙摆,弯腰拿起破碗,闻到一阵剧烈的恶臭,连忙把破碗丢下。
宋融伸手扶住破碗,拿起,收回来,反转手臂,从木笼底下的缺口递入,用另一只手接住,举起。
天上下着小雨,雨水从没有遮挡的丁山飘落,滴在破碗里。宋融捧着破碗,吹了吹,仿佛里面的黄水很热乎,或者有茶叶碎末漂浮。他慢慢抿一口,微微仰起头,咂咂嘴。他的嘴唇干裂,肌肤往外卷曲,边缘发白。
杨妃心酸不已,一个宫女趴在地上,四肢着地。杨妃顺势坐在她背上,接过手帕,擦了擦眼角。另一个宫女打着伞,站立在旁。
天上打雷,闪电发出耀眼的亮光。几只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飞落笼内。宋融举起破烂的衣袖,为它们遮挡着雨水。衣袖上开了十几个大小洞,几乎不可能遮挡住任何东西。
他右手拿着一根木棍,点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用木棍指了指右手边第一只鸟雀,说:“跟我念,上善若水。”
“顿。”
他又指着右手边第二只鸟雀,说:“跟我念,上善若水。”
“等。”
鸟雀发出一下低沉的“顿”,又发出一下高亮的“登”。“顿,登,顿,登,顿,登,顿,登,叮咚……”他敲一下破碗,发出叮咚声响。
趴着的宫女偏过头,说:“竟然是《高山流水》?”
宋融抬起头,对她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他抓住块黑乎乎的东西,放入嘴里,用力咬,嘴角流下汁液,还用力猛吸,生怕漏掉一点。
杨妃看得恶心反胃,伸手捂住嘴,生怕吐出来。
过了片刻,杨妃感到好受些,才说:“宋融,你认输吧,我会给陛下求情,陛下会饶你一命。”
宋融微笑,说:“母后,不必担心,我有办法。”
杨妃叹息一声,说:“陛下是天子,你向他低头,没什么可丢人的。”
宋融挥动木棍,“顿,登,顿,登,顿,登,顿,登,叮咚……”,演奏《高山流水》。
站立的宫女凑到杨妃耳边低声说:“高士来了。”
杨妃回头瞥一眼,站起来,接过一个小皮袋,放在木笼边。宋融拿起,打开一闻,满是酒香。他将小皮袋放下,塞好。杨妃说:“喝吧。”
宋融摇头,说:“喝了,别的东西就喝不下去,又得闹肚子挨饿。”
杨妃扭头走了,宫女急步跟随。她看了看高士,高士微笑。杨妃略微放心,离开大院。
高士走近,举起袖子捂住鼻子,说:“把他拉出来。”
守卫们打开木笼,将宋融拉出来,推倒地上。
宋融的头发、胡须很长,扭曲纠结在一起。他的脸很脏,看不出本来肤色。他的衣服破了数十个大洞,东一片、西一片地挂在身上。他的身上长着脓疮,流出黄水,散出恶臭。脚上戴着铁链,行动不便。
他抬头、挺胸‘伸腰,站得直了,然后又变成歪头弯腰的怪模样。
高士闷声问:“宋融,陛下让我问你,你可服了?”
宋融歪着头看高士,说:“将反贼高翔围住了?忍不住要来炫耀一番功绩?”
高士大怒,吩咐左右:“将他关进去。”左右上前,将他关进木笼。
高士走几步,忽然回头,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气糊涂了,赶紧把他拉出来,我要带他去见陛下。”
守卫们又将宋融拉出来,高士见他实在太脏,让守卫用洗地的水泼在他身上。宋融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样子。
高士以为宋融必定走不了多远,就让人弄来牛车,将他载了。高士连声催促车夫快行,免得天子久等。
来到宫殿外,高士吩咐禁卫们将宋融看住,到里面禀报。
天子听说宋融竟然不服,大怒,让禁卫将他提进来。
宋融还没进到宫殿,一股恶臭就传进来,众人纷纷用衣袖掩住鼻子,用目光责备高士,怪他怎么办事的?
高士很委屈,照宋融那样子,洗半天都洗不干净,你们能等半天吗?
禁卫们将宋融往地上一丢,他顺势坐了。他站着的时候,弯腰歪头,模样古怪。坐着的时候,肩正腰直,举止端庄。想来,他在木笼里混那么久,练出一点本事。
天子端详宋融,点点头,很满意他的窘迫,问:“宋融,你可服了?”
宋融摇摇头,没有说话。
天子向刘奇示意,他就上前解说现在敌我形势,好打击宋融的信心。宋融闭着眼睛听,不停点头。
等刘奇说完,天子又问:“宋融,你可服了?”
“不服。”
天子大怒,不动声色,举起手里的奏表,说:“那你猜一猜,这又是什么事情。”
“火烧白马渡!”宋融不假思索说。
天子、大臣们、高士大笑,宋融猜错了。
“我还以为你真是神算呢?原来不是,上次只怕是碰巧猜中的吧?啊?!”
宋融见众人不似作伪,有些迷惑。照他猜想,杨英必须火烧白马渡才行。他从来不去考虑她能不能做到,只考虑她想不想做到。
没人任何人比宋融更加清楚杨英的才能。他一直压住杨英,就是不希望旁人说她借助宋融的帮助才成功,让她背负一辈子都洗不脱的包袱。只有当宋融不在的时候,杨英将才能发挥出来,众人才愿意相信她。
远处传来钟声打断众人的笑声。
听到钟声,众人心里生出隐隐约约的不好感觉。他们互相对望一眼,从对方眼里看到犹豫、担忧,立即转开头,不敢多看。
刘奇受不住沉默,勉强笑一声,说:“或许是禅院的钟声。”
“当!”再次传来钟声,这次近了些。刘奇脸色立即变了,抿着嘴唇,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