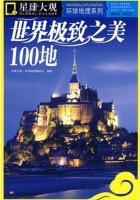我的心却是在疼,越想余高人那八字箴言,再想实行那八字箴言后的事情,便开始疼。
本来一个人安静地疼会儿就算了,偏偏这时候面前站了一个人,什么话都不说,就只是站着,这人皮鞋很亮,皮质看着很是细腻,明显不是龙骁,我就又有点心疼了,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其实龙骁都没有在过我身边,这么一心疼,又拿起酒精给膝盖扫扫,结果前面那人还是没走。
这人怎么对这个位置这么固执呢?于是,我决定抬头,给他些照顾老幼病残的建议,现在我是又病又残。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永远会让你觉得他不是你这个世界的,人以群分其实是一种天性,经过多少代的进化,人一直将这个能力发展完善,所以我只是一眼,就知道这人不是自己同类。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那双眼睛深入潭水,又纯澈宁静,带着独属于桃花眼的三分笑意,却又是不动声色,于是,不到三秒,我便败下阵来,心里又舒了口气,垂头将花瓶端下去,自己也往边上挪挪,“您要坐就坐吧。”让位置给你还不行,说着又把放花瓶的位置用手擦擦,又低头继续给自己扫酒精。
他便在我身旁坐下,看着我面无表情地扫酒精,声音是男人的低磁场,一个声音一个节拍的修养和几分歉意,“很抱歉,我的车撞倒了你,希望你能跟我到医院检查一下,医药费我会负责。”
我正里外兼修的疼,说了句不用,便不想与他说话,这车撞的力道还不如龙骁给我后踢的一腿,至于膝盖,谁让自己没事儿穿裙子出来作,老老实实活着夏未至,一步三个格的走路,哪来的车能撞倒自己,这样一想,心里反而舒服点了,便准备合上酒精走人,结果找不到盖子,他俯身捡起来给我,“你的膝盖会留疤痕。”
“不会的。”我很笃定的模样,拧好酒精,丢进花瓶里,又掏出口袋的手机,钱,一同丢进去,想着要不要与他说再见,这个男人已经起身,他的个子和龙骁差不多高,很给人压力,尤其是这样西装革履,我便下意识地后退一些,男人说,“我的教养让我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抱歉,我的车可以送你回去,希望你不要拒绝,否则我会十分不安。”
这样一个气度修养的男人在面前,又这样真诚地表达歉意,最后又是你不答应就是欺负人的模样,我只想帅赖皮地蹲下来好好接接地气,不说话把他给气走,只是膝盖太疼实在蹲不下来。
这车就是大概一小时前撞我的那辆,黑得像是钢琴烤漆,亮亮的,那个年轻人笑得很歉意地过来给我开门,我受宠若惊,心想还是第一次上车时候有人给我头顶护一只手,道了谢谢,他一副折煞小子地笑着,又去给这个男人开门。
上了车只觉得奇怪,分明大众的车牌,车里却是比游畅那辆奔驰精致舒服。
车上一直是一种淡淡的香味,只觉得混合海水,花朵,果实的芬芳,清新而又自然,我下意识地找一下味道的来源,眼神一下子碰到后视镜里教务处主任的眼睛,那眼神太奇异,我略过后又想看看,就听到男人的声音,“齐理事,麻烦你安排买一些药送过去。”
车便停了下来,齐理事下了车,鞠躬着说着您慢走,车门就合上,真的慢慢开走,理事大叔还是鞠躬的模样,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下车的的那个人是我。
但是既然在车上,我决定不乱看乱瞄,安心当个乘客。
男人问了地址,我说了附近一些的。
“希望可以具体一些,齐理事找的时候也多些方便。”
想到刚刚那位下车的理事大叔,于是我就说了具体的,他点点头,好像早就知道一样,让司机给齐理事打电话,换了个方向翘着二郎腿,那淡香又飘了出来,但是我长记性地决定不看他,视线一对上,他就能找到话题,当然,视线不对上,他还是有话题。
先是从花瓶开始,说些自己也准备买花瓶,不过样式什么的需要斟酌,再到我把手机什么的一咕噜放进去,问我要是有人联系该怎么办。
不会有,我依旧笃定,然后回到花的上面,他问我葡萄会不会开花。
这个问题就像鸡蛋是大头出还是小头先出来,把我问住了,我摇头,说这个得好好观察一次葡萄才知道,又说应该是开花的吧,有果实的东西,不都是开花的么?
男人低低笑着,其实没笑声,只是眉眼都是笑的模样,“有的果实,不开花也会结果。”
“无花果么?”我问他,他高深眯眼却又换了话题,问我在哪里读书,什么专业,就像是两人没话找话那样随意,我便说了,只是把学校换成了离学校挺近交大,专业没改,化学这专业也没必要藏着,反正每个学校都有。
“我还没去过交大,只听说那里的花树很受欢迎。”
按道理我是要接下去,但是交大我也不过去过一次,又是冬天,他说的话花树在哪儿根本没看到,便顺着说了句确实很好看,又听他继续道,“海大去过几次,赶上春天花开,很是漂亮,你去过海大了么,在里面读书还是很享受的。”
“确实,学校饭菜也很不错。”
“你经常过去?”他的声音带着些那我们多谈谈的味道,我刚想哭丧脸一下,这话题便突然止于此,那声音变成了一种试探的关切,“你很焦虑的样子,腿是不是很痛。”
“没事儿,就是看天黑了。”我往门靠靠,手摩挲着花瓶,一点震动的兆头都没有,这个时候我是矫情的,女生受伤的时候矫情一些很正常,所以到现在龙骁也没打电话问问为什么还没回来,让我有些,嗯,也许就是这个男人口里的焦虑,也许他还没有回家,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总觉得这车开的时间赶上我走路回家,司机小哥说有的路不能进去,只能从外面走,最后车也是停在了院子入口处,刚下车那个理事大叔就已经在了,对车鞠了个躬,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他是怎么在那些大众中将这辆认出来的,下车时候我想也许是这辆车太干净。
膝盖上的血迹干了,下车时候正好又撕开一下,我抽了口气,人也往前踉跄着,便被一双手接住,那阵淡香又袭了过来,更加浓郁些。
他很礼貌地待我站好之后,便退开些距离,接过理事大叔手里的一包药盒子给我,一副神教徒坚守信仰的安然,“谢谢你。”
他声谢谢叫我觉得自己都高尚起来,飘飘然地不好意思,做好事还真能缓解心情,我回身抱着花瓶,他突然便投了个东西进来,当然不是支票之类的,我透着大孔看了看,名片,背面就是个商标,名字被压在了下面。
“如果你的腿出现了什么情况,可以打这个电话,齐理事会负责你的治疗。”
我笑着想我肯定不打,人生不过一期一会,客套话还是得有的,以后我走地上,他坐车里,谁认识谁呢,不过也学着他礼貌的模样说,“我知道了,拜拜,先生。”
“再见。”他说。
龙骁还是没有回来,游畅打电话过来说龙骁在他那儿,可能会晚回来。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躲我,没准担心我精神分裂严重,半夜梦游起来,对他磨刀霍霍,其实他完全是庸人自扰,我虽然不是心境通透之人,做不到大彻大悟,却也自知之明,知适可而止。悬梁刺股不过是为了大脑清醒,我已经膝盖血肉模糊,尴尬狼狈,再做不到几分清明,我那苏州小母亲必然是要将我塞回娘胎重造。
我抹下自己翘着一边的唇角,闻到手指间的一阵清香,自然平静的味道,原来是那个男人手上的味道,还真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不过也是个可怕的聪明人。只是那么点时间谈话,便是如同在对峙一盘棋,他进退得度,有礼有节,丝丝入扣,不动声色,掌控着节拍和节奏,我只能坚守城门,挂着休战牌子。
肥皂洗到手指没味道,我才出来,龙骁还是没回来,也没有电话,其实他本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汇报的习惯。
倒出花瓶里的东西,乱乱的都堆在沙发上,这让我心安。
将花瓶盛满水,按照百度方法加了些白砂糖进去,又将那依旧开得茂盛的蓝色妖姬一支一支插试管似的放进去,满意地收拾地上的花叶,好看的花就是这样,怎样都是好看的。
还好这世上,没有不好看的花,只有不好看的人罢了。
我开始整理沙发上的东西,钱一张一张抹平,放入钱包,钱包里放着我和夏未央的大头贴,高中拍的,我们已经很久没一起拍过照片;将花店发票撕了,丢入垃圾桶,屋子太过安静,这声音叫人感到兴奋,也许我真有当变态的潜质;将酒精和棉签放在一旁,准备待会儿再用,那个待会儿我待了很久,因为我一直在对这张卡质的名片发呆,因为背面简单写着的六个字,总设计师叶霖。
夏未央那部剧里的男一号,叶先生。
那一刻,醍醐灌顶,假作真时真亦假,自作多情必自毙。
只有未央那样才能接触到那样的人,喜欢未央那样的人又怎么会喜欢上我这样的人,也许拗口,却也明了。
龙骁,不会真的喜欢夏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