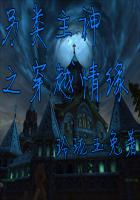我做了一整晚的梦,醒来的时候已是早上九点多,全身疲软,我记不清自己梦到了什么。但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是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我总有一种预感,昨晚的一直延续到清醒过来的那个梦是不好的。我的眼睛黏黏的,似乎还是哭过的。
但是谁要继续修补一个已经忘了的梦境呢?况且还是在明显预感到它不是个好的梦的时候?今天是我二十九岁的第一天,我要过得有意义一点,我要去书城挑书,去唱片行挑几张新发行的唱片,然后买些食材回来自己做饭,我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要不断给它们注入新的动力和养料,切不可让它们荒芜了。
我挑了一身知性的装扮,我里面穿了浅色羊毛衣配粉色衬衣,外面搭了深卡其色的风大衣,下身穿了靴裤,穿了平底的褐色鹿皮流苏短靴,最后还搭了我最爱的大红色羊毛围巾。把头发拨起来在脑后勺松松地挽了个髻,在两侧留下一缕卷卷的碎发,戴了最大型的那种银饰耳环,最后再化了个淡到看不出来的小淡妆,涂了点薰衣草的润唇膏。镜中的人依旧是很漂亮的,姣好的身形,纯真的面容,依旧对生活抱有希望的眼神,除此之外,还有对生活的智慧的挖掘不遗余力,努力践行幸福人生的观念。
盯着镜子看了半分钟,我终于清醒过来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审视过自己了,我发觉自己其实也很在意时光的流逝,也害怕有一天自己不再年轻,不再有吸引力,害怕那时还是孤苦一人,那时我要怎么捱得过去呢?终于还是拿了包出了门。
“小姐,去哪里?”出租车的大叔问我,我看了他一眼,意识到其实他的人生应该也是很无奈的,然而,他把青春献给了这份载人的工作,人上人下,与他有何相干?这个社会真的需要他吗?没有他这个社会不是继续照常运转吗?没有他,那么必定也会有另一个类似他的大叔来替了他的位置,他的存在就像他的消逝一样,没有凭据,没有大风大浪的影响或者意义。这不就是人的悲剧和限制吗?我又能逃脱的了吗?
“去书城,谢谢!”我的日子像流水一样消失,我抓不住的,迟早有一天,我也要变成街上拎着购物袋的走路蔫蔫的大妈,我也要头发稀疏,由今天的青丝变成灰白的秃顶,我将终有一天失却了自己的这一身荣耀,如果那一天到来,我还可以留下些什么呢?
很快就到了书城,我开始随意挑些书籍,我倾向于当代一些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的散文,或者一些哲学书籍,人生哲学之类的也开始吸引我的眼球,与其说吸引了我的眼球,毋宁说是我的心渴望这些精神食粮,企望它们能带我走出人生的困惑。
随意挑到一本西方的哲学书籍,是叔本华的著作,我随手翻看着,不觉被吸引着一页页往下读,站累了,不知不觉就找了个书架的角落坐在地板上开始看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走着,他在走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可是一觉得的时候,他早已走了好远好远,有时候要不是习惯了这时间的无意间走的太远的事件,我们恐怕是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自己的面目,自己的声音的改变,自己的认知,甚至自己的一切。
挑了三本好书,结了帐走出书城,已经饿了,饿得很。找了一家真功夫,等候上菜的过程中,肚子一直不争气地责怪说怎么这么慢,快饿死了。那时侯,我来不及想食色性也的话,我只是想早点吃一口米饭,如此简单而已。后来吃饭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嘴里的食物特别地美味,我觉得很感激这一盆饭带给我的饱腹感和美味。如果不饿,也是要吃饭的,因为要维持生活,这是必需的。但长期按时吃饭,吃饭就可能变成一个必须去做的任务,就像家务,必须按时清理,不然就要面临不洁带来的不适感。但很少有人会真正品味出食物的味道,直到经历过真正的饥饿之后,才能觉出食物的美味。这也就是要有个对比,好坏的对比,才能学会不对日常的事物感到厌倦,或者习以为常,而是以一种珍惜的心意,感激的心意享受每一件事物。
搭了地铁去到离家比较近的一家唱片行,挑了几张店长推荐的几款新碟,在一旁的试听机上试听,闭上眼睛,静静享受耳朵里充满律动的音乐,血液都要沸腾起来的新生,人生不止是要悲伤的情歌来酝酿自怜自艾的情绪共鸣,也需要耍掉一切羁绊的单纯洒脱,我情不自禁地开始轻轻摆动自己的身体。
突然有人蒙住了我的眼睛,由最初的惊讶到最后的开心,我想我知道是谁,“喂,别玩了。”
“你知道我是谁?”他帮我摘下了耳麦,轻轻在我耳畔说,我羞赧地回避了一下。
“不就是你咯。”我始终都没转过身子来,我知道那就是凌江,我也很想回转身看着他,可是,我竟然还是不能,做不到。我僵在原地,终于,他把我扳了回来,正对着他。
“听我说,小雪,我不想再同你兜圈子,也不想再和你一起互相捉迷藏,我今天就要一个答案,我喜欢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他真诚地对着我眼睛说,我想自己是喜欢他的。
“嗯,你容我再想想啊。”我还是没有机会学会在这种被求爱的情况下当下就应下的能力,尽管我心里是百转千回地想要立刻就答应了的,然而,我就是没法说出我愿意的话,口无法对心负责,我真有点恨自己了,怎么这般懦弱?
“还要再想?嘿,好吧,就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怎么样?好吧,现在我们去哪里好呢?”
“嗯,明天,我再告诉你我的答案。我们要去哪里?”
“小雪,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所以我们得提前一天适应一下怎么当个完美的男女朋友啊?要不先去看场电影?不,太俗套了,不过,每对恋爱的人都不会觉着这老套的,因为只要两人在一起,无所谓干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小雪,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不想去看电影,上次才看过啊。要不去我家吧,去我家做饭,我要去菜市场买些新鲜的食材,你不介意的话陪我一起去吧?”
挑了两张不错的碟,一张是刚试听的那张有激情的碟,一张是凌江为我挑的全是林夕作词的歌曲荟萃合集,我们买了各种食材回家做晚饭。
我们像所有刚开始的情侣那样温柔缱绻的眼神,一言一笑皆是充满柔情蜜意的,幸福的厚度愈来愈厚,我们什么都不说,却足以说明一切,我们对彼此的感觉掩饰不了,也似乎到了不再需要互相试探,互相隐瞒的矫揉造作的阶段。
我和他为着一餐晚饭,精心且热烈地切切洗洗,仿佛在为着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在努力一样,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但我们确实就是如此满足与对方在一起的时间,甚至空间。
“好了,终于可以吃啦!给你筷子,嗯?”
“给谁筷子啊?”他不接,却一脸温柔地笑问我。
“你。”
“我是谁?”他还是不接。
“你就是你咯,你不要算了,我自己吃了。”我气得收回筷子,拿了筷子,自己开吃。
“生气了?”他站起来,绕到我身后,俯下身来,贴在我耳边轻声吹着气,“雪,叫我江,我一直都想这么叫你的,事实上我在心里这么叫过你很多次了。你呢?有没有想过叫我的昵称?”
“嗯,没想过。”我很诚实地回答了他这一问题。
“呀!”我被他敲了一记,“很痛啊。”我撒娇,揉揉自己的头。
“给你点颜色瞧瞧,居然连这个都没想过,显然是真没把我当回事啊,那好吧,看来我也不用自作多情了,你自己一个人吃吧。”说着真要拿衣服走人,我看着心里想道歉,却又觉得他肯定是在逗我的,我才不要这么乖输给他呢。
他似是在等我开口挽留的,十几秒钟过后,他在寂静中走向了门口。我应该要开口说不要走,留下来陪我一起吃饭的,可是,那样的气氛,竟还是不习惯开口挽留,不习惯露低姿态。
他一走,我吃着这顿本来闹哄哄的饭,突然觉得索然无味。我收拾完餐桌,冲了澡,时间尚早,翻出今天新买的书来看,书中讲到人生短暂,何必花这许多时间来彼此试探,彼此怄气,到头来一切都将随风而逝,为什么不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让心做主,考虑那么多有什么意义?谁在乎你是否经过百转千回的思量才做的决定?谁又在乎你是否要为着这些前思后想而焦虑不安?谁又在意你是否能拥有真正的快乐幸福?毕竟,这一切都是这样短暂,谁能保证它是永恒的?谁能用他的经验告诉你什么是永恒的吗?没有人。
我突然间像懂得了什么一样,我立即找来电话,给他打电话,我想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我愿意,我是没想过叫你的昵称,可是那绝不是因为不想,或者不屑的缘故,而在于我不敢去想。我从来都害怕往下深想,怕没有结局,自己要失望,怕自己失望后,再不敢抱任何希望。
手机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接着继续拨打他的手机,一次,再一次,我急切地希望为自己解开这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在心里祈求他不要再生气了,接电话吧,接电话啊。
打了一晚上,终于还是没有人接。我蓄积的勇气跟力量都渐渐消耗殆尽,我想明天再说了,于是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江,我愿意!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愿意。请快点联系我吧?”
我等不了了,已经12点四十多了,我实在想不出他会这样冷漠且坚决地对我的原因,虽然我让他有点点小不愉快,但我很确定他并不真的为着这个事情而生气,他只是怪我让他太被动,下不来台罢了。我想或者有别的原因也未可知,我决定先睡。奇怪,我一挨着床,就开始胡思乱想,但又很快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我竟然知道自己在梦里。我开始做梦了,又一次清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