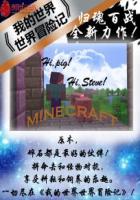-
心中千百句抱怨说不出口,夏宛峙抬眼看着项重君的眼睛,缓缓问道:“那么,对墨初吟和他做的事,你是什么看法?”
他第二次问出这个问题。
可这一次,得到的回应大不相同。
项重君半垂了眼,睫毛轻轻颤动。除此之外,有如雕塑。
薄云滑开,月光洒落的一片朦胧渐渐清晰而温柔依旧。
仿佛仅仅一瞬,又仿佛有千年之久。
久到夏宛峙开始后悔追问这个问题,开始后悔之前把想说的话聊完了以至于现在想更自然一点地转移话题竟一时想不出。
此时,项重君却开了口。
“对我来说,他……很任性,很残忍。”
项重君站起,转身背对着他,缓步走了几步,抬眼,蓝色花瓣已经近在咫尺。再往上抬头,看着被月光晕染的薄云边缘,目不转睛,仿佛这样,就能压下涌起的热泪。
皞天三个姓楚的,唯他最残忍。
眼泪不曾淌下,埋藏在过往的那一片血色却蔓延了整个眼眶。
在他的视线之中,夜下大片大片分不清颜色的枝和叶,月光衬着的摇曳着偶尔飘落的淡蓝花朵,都蒙上了那一层血色。
是他持剑缓缓拔出后,滑过剑身在剑尖滴落的鲜血。
一块微光流动的杏木雕坠摔落在地上,项重君冷漠看着眼前,淡蓝长裙的女子紧紧捂住腹部的伤口,无力地躺倒,她将急促的呼吸尽量放平缓,可泪水却止不住地一颗颗淌下,模糊不清的视线紧紧追随着他,不曾有一瞬挪开。
她的旁边躺着一个孩子,胸口下的地面已经积了一滩血,闭着眼,如沉睡般安详。
她颤抖着嘴唇微微张了张,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倾诉,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或许说了,他没听见。
因为项重君随即便甩落剑上的血珠,转身离开。
竹子和木头拼接成的小屋子,屋外围着蔷薇花爬满的篱笆。
他来时开得娇艳,走时瞬间凋零干枯,像徒然被抽空了所有的生命,皱巴巴地贴在篱笆桩上,了无生气。
走之前他往右前方看了一眼。
墨色玉冠,银底乌边、繁复精致的长袍,衣摆翻飞间,天地山川草木的双面暗纹若隐若现。
有人站在那里看了整个过程。
亲眼看着,他最爱的妻子,还有他和妻子共同的孩子,就这么毫无防抗地死在了他剑下。从头至尾、无动于衷。
这是项重君第一次见到楚银墨,但他并没放在心上,既然没有阻拦,就不必理会。
或者说,那时候的他,没有心。
-
第二次遇见。
束发之物换成了灰色束带,衣服简单许多,一眼看去只有三层,镶了墨色绲边,长袖衣摆见也只有山川草木的乌色纹绣。那人躺在树枝上,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块坠子,察觉到他的到来,便随意地瞥了一眼。
项重君终于得知对方的身份和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后,辗转多年一直寻找,却不想在几乎无望的时候,竟在他于凡间漫无目的行走之时偶然遇见。
“楚神君为何在此?”项重君看着对方,有些不可思议。
很多年后,项重君才知道,这个他以为的偶遇并非偶然,他孤身一人苦求多年,最后是上界的家主为他走了一趟。而那种境界的神明心通天地、如为一体,有诸多玄妙之能,想要见到谁,谁便在冥冥之中被指引走去他所在的方向。
所以对方反问:“不是你要见我?”
“是。”项重君心情沉重道,得偿所愿的惊喜终抵不过心中悲苦,“敢问神君,我的……妻子……临死前持有一物,不知是否是能与神君交换一个愿望的杏木雕坠?”
“是啊!”对方转头看见他,勾起一个轻浅而没有阴霾的笑,有如清风。第一次见,如沐春风,而以后每每想起,叫他如坠深渊。
项重君心中忐忑,口中却迫不及待地问道:“神君可否告知在下,她交换了什么愿望?有没有提起……别的什么?”
那时候的他,满心绝望,满腔恨意,可是谁也不能恨,只能恨自己。
纵然对方明明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却袖手旁观,可这时候时的项重君并不恨他。
那件事太过复杂,即便地位如他也不好插手。
想到或许妻子临死前能夙愿得偿,他对对方是感激的。
都是造化弄人。
坠子在那人手指中转了几圈后消失,楚银墨跃下了树枝,道:“她问能不能帮你什么,问你为什么会变成那样,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解决你的问题,未达成交换,第二个愿望是她儿子能否好好活着,若仍不能,能否下辈子让他有个圆满的家庭,同样未达成交换。”
项重君错愕,甚至来不及愤怒:“为什么?我的家事你无法插手也就罢了,一个母亲临死前想让自己孩子过得圆满违背哪条天条哪类道义了?”
对方轻笑,“愿望没有什么问题,可她将死之人能以什么条件交换?下辈子吗?那等下辈子再许愿好了。”
信道之人修今生,不修来世,福报恶报应在自己今后甚至后人身上,不寻来世。今生之事,本就不应由忘却前尘、重入轮回的来生承担。若没有往后,才会寄托于来生。
前尘尽逝,重入轮回,即便有幸得回前生记忆,也不过像旁观另一个人的人生,与今生全无关系。轮回是属于天地的力量,世间生灵谁也无法抵御。强大的法力、高深的境界也只是让他们逃避轮回,一旦陷入,万物平等。
至于神仙的转世的历劫和修行,不过直接投入临盆的胎儿中降生,未经轮回。
那样的“来生”原本就还是今生。
可若意识投入得彻底,同样会有自我认知改换的隐患。
在同一个轮回,即便记忆失落、容颜改换、性格转变,再没有一点相似,可仍然还是那个人,就像成长,哪怕面目全非再不是当初的自己,也依然是自己,从未改变。
一旦进入了轮回,哪怕因为灵魂的延续、成长环境的相似,容颜不变,性格不改,可那也只是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人。侥幸得了前世的记忆,也只是观看了一场别人的人生。
来生?她没有来生!
项重君知道,对方所作所为无可指摘,可心中恨意已然吞天噬地,吞没了他的理智、他的意识。
不能不恨,尽管他的孩子同样没有所谓的“来世”,可那是他唯一所爱兼亏欠之人这一生最后的安慰!
——她没有能力完成你的条件,你可以来找我!等到我清醒那日对你而言也不过弹指一挥,为什么不找我?为什么,要拒绝她?你怎么忍心,怎么可以?!
既知来生不做数,他又怎能不为此心神俱碎?
如果应天理当灭人欲,他为何求这仙途?!
昏迷之中,身体连着意识仿佛飘飘摇摇,终于宁静之后,似乎有人在身旁谈话。
那声音有熟悉、有陌生。
“……皆已突破,明虚境。”
“但愿……”
“……可惜,是我等强求了。”
终于醒来,只觉不知今夕何夕。
项重君茫然睁眼,竟不知这一生要怎么走下去。
……
-
项重君回过神来,察觉几片花瓣落在了肩头,他抬手将花瓣拍落,转头间,只见两片花瓣悠悠扬扬从头顶飘落。
“重君,”夏宛峙端了满杯的两杯酒,递了一杯给他,“喝茶,还没多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份礼。”
项重君接过来,道:“不过举手之劳。”
若是凡人必然要辛苦数日,但以他的道行,真是举手之劳。
夏宛峙一笑:“敬你这‘举手之劳’。”
项重君笑了笑,将茶一饮而尽,然后一怔,“墨神君给你的安神茶?”
“……你、喝得出来?”夏宛峙神色变得有些微妙。
他是不是弄巧成拙了?
每次火冒三丈地去那人那里,将心中愤懑一股脑地倾诉后,坐下喝杯水他心情就好多了,那人送了自己不少,说是清泉去火自己火气太大没事多喝点。他恨得咬牙,到底还是收下。
——原来这东西居然是茶?还是能喝得出来历的茶?
谁家的茶跟水一样一点味道没有?!谁家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茶’还能把来历给喝出来?!
大约是安神茶起了作用,项重君灵台一阵清明,只觉因陷入回忆所引起的心中阴霾散去,他开怀一笑,转着杯子道:“当然可以,但凡踏入仙途,用心去做一样物品,总会有自己的道意融入其中。”
夏宛峙:“……”
“道意融入会影响物品本质,我们这些境界低微的还好说,到了神君那个层次……能达到那个层次的总是专注于单一一道的多,一不留神真是做什么神器神药都弄成那样效果。神君的安神茶也算闻名遐迩,静心之效天界无出其右。”
出自墨初吟之手的物品,掌控情绪之效当真举世无双。
“我对他并不多了解,只能简单说说。墨神君其行事干脆利落,方法多是简单至极,但成效甚高。”说起来那三位姓楚的处事方法各有偏好,但理念却惊人的相似,简单得有时候另一个当事人都不知道怎么成的。
“其言辞真假难辨,”项重君回到桌前做好,简单至极、毫无修饰的石桌上多了一个茶壶,他将杯子放下、满茶,再以过来人的口气沉痛道,“信或不信,皆是迷局。”
夏宛峙跟着坐回了原位,十分认同地点头,他懂。
轻风裹着淡蓝花瓣墨绿叶片在他们各自背后回旋飘舞,烘托着他们刹那间萧瑟的内心。
“神仙多是自在逍遥、超然于物外,但墨神君给我的感觉或许更像凡间传言中的另一种天神,着眼于万物,人世间任何感情都无法令他动容,”项重君道,“他的心太淡漠,表现出来的随和或许另有图谋。”
“……何以见得?”夏宛峙皱了皱眉,借着慢慢饮茶的功夫数度沉思后,问道。
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冲突?
本来之前项重君说他“很任性”加上这能喝出来历的安神“茶”已经令他有七成确认了是墨初吟,但项重君此时偏又这么说,他又迟疑了。
“我没有证据,只是自己的一点点推断。”项重君敲了敲桌子,抬眼看向远方,唇带微笑,目光渺茫,“墨门我尚看不出有何阴谋,但,墨、仙、教,已入局。”
何止墨仙教?就连他自己,亦已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