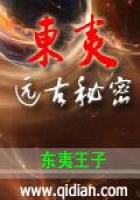银溪心里七上八下上了路,好在小白兔找回来了。
祖修的确不是灵光的人,但佑樘眼神太明显了,谁都看得出来。
祖修:“朱公子看你的眼神,太奇怪了,他一直在斜眼看着你。”
银溪:“我当然知道了,没看我离他那么远吗,他不止是偷偷瞄,正眼死盯也是不少的。”
祖修:“你还要护送他那么久,你们俩总离这么远不方便吧。”
祖修和银溪骑着马走在一起,佑樘离老远跟在后面,还躲闪祖修和银溪的眼神。
祖修:“你瞧他那个样子,你是不是对他做过什么?”
银溪:“我能把朱公子怎样?倒是他……我觉得他看出来了。”银溪一脸忧心。
祖修:“你说,你是说,他看出了你,那个?”
银溪:“我觉得是,要不他怎么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佑樘在后面是离得远,但完全在他听力范围之内,我看出什么来了?这对兄弟真是……怪啊。这几日反倒是祖修和佑樘说的话多一些,银溪根本就不怎么接近佑樘。
三人赶路久了,下马到河边喝水,银溪想趁此时跟佑樘把话说清。佑樘正蹲着取水,银溪出现在他身后,秀丽的脸庞倒映在水中。佑樘注视着水中的玉面,当真是镜花水月,让人觉得不真实,已经决意抛却过去,却出现这个与故人如此相似的人,讽刺啊。银溪发现佑樘只盯着水中的自己看,先是不自在,又看,看出来了吗?知道我是女子就不该这么盯啊,无耻,枉我还要护你周全。越想越气不过,银溪索性踹了佑樘一脚。佑樘没有防备,栽进河里,上半身都湿了。这一脚算是踢光了佑樘所有幻想,怎么可能是崇龄!他是男的不说,还如此蛮不讲理,生性暴戾,我这几天是中了什么邪!佑樘好不容易爬起来,甩甩身上的水,正视银溪,眼里再无柔情,满是不满。银溪掐着腰,没有道歉的意思,一副很爽的样子。
佑樘:“你干什么?!”
银溪:“原来你也能这么大声说话啊,失敬失敬。”银溪扬了二正,一脸轻蔑。
佑樘:“你干嘛踢我?”
银溪:“你干嘛看我?”
祖修在一旁连吃带喝,反正劝不住银溪,就当看戏了。
佑樘:“那都是你长得像我一位故人。”
银溪:“故人?死了的故人吧?看到我跟见鬼一样。”
佑樘:“谁说她死了!”这么多年,佑樘从不相信张崇龄死了。
银溪:“不要鬼扯了,看出来我不怪你,但你不要一直盯着看啊,淫贼!”
佑樘:“刚才你们说话我就觉得奇怪,我到底看出什么了?哪里淫贼啦?”
银溪:“你,你还,你还偷听?你什么耳朵?那么远你也?”
佑樘:“刚才的距离算什么,再远我也听得见。”
银溪:“你这小人!”
佑樘:“说清楚!干嘛踢我?”
银溪见佑樘面不改色,完全看不出有何隐瞒,银溪:“你真不知道?”
佑樘:“该知道什么?你说啊?”
惨了,踹错了,不是吧,这小子听到谈话了也没猜出来,木头啊?这下怎么收场?银溪语塞,不知如何是好。
银溪:“这个,这个,不打不相识,柳大哥我,是看你太腼腆了,所以跟你亲近一下,你不要这么认真啊。”银溪搂佑樘过来,还拍拍他肩膀。
佑樘不满于这个解释,可又不是一个爱纠缠的人,也就算了。佑樘也是个聪明至极的人,现下是崇龄之事使他内心烦乱,还有就是涉世未深,是男是女分辨得不尖锐,尤其是他自己就生得像女子,五官秀气,睫毛又长又密,对于女子说,佑樘个子高了点,可他瘦弱,看起来更像女子了。归根结底,佑樘是随母亲多一点,所以长得很女性化,也比一般男子漂亮。
祖修目睹了全过程异常开心,平日里银溪总仗着自己聪明过他许多而取笑他,今天聪明反被聪明误,罕见罕见,真是精彩。
重新上路,银溪也不敢再冷落疏远佑樘了,三人并驾同行。
祖修:“朱公子,我们同行也快一个月了,我还有事在身,送你们到前面的贵阳府,我就要去办自己的事了,以后的路还望朱公子与银溪相互照应,刚才我弟弟多有得罪,还望海涵。我弟弟对你有所误会,今后必定举案齐眉。”
佑樘心想:举案?还齐眉?是不是又在捉弄我?
银溪:“朱公子不要惊慌也不要见怪,我哥书读得不好,经常用错成语,但是他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我是不会再欺负你了。但是你也不能一直盯着我了。”
佑樘:“两位如此帮我,是我该谢谢你们……”佑樘话说到一半没了动静,在马上左摇右晃。
祖修:“朱公子,你,你怎么了?”
银溪眼见佑樘要跌下马了,一把扶住他,见他脸色苍白,一摸额头,真是烫,“他在发热啊。”
祖修:“你刚才把他弄那么湿,他是得了风寒吧?”
银溪:“还真是体弱多病。帮我抬他上我的马,祖修,你牵好他的马。”
祖修:“还是让他上我的马吧,你,方便吗?”
银溪:“还管那么多?他都没有意识了!”
祖修:“知道了,”祖修翻下马,把佑樘扛到银溪马上,“你也不怕累到小白兔。”
银溪:“快跟上来!”银溪骑马快奔。
祖修:“要不要这么快?你摔过马,慢点!你是有多紧张他?”
宫中,太后午觉惊醒,一下从床上翻起来,“来人啊,给哀家把皇帝叫过来!”
皇上匆匆赶来,身边还跟着万贵妃。
太后:“皇帝啊,哀家让你来,你又把她带来干什么。”
皇上夹在老娘老婆中间一向不好做人,说:“也没什么是贞儿不能听的。”
太后:“哼,那哀家就说道说道,要不是这妖妇挑唆,皇帝不会想废了樘儿,樘儿也不会离家出走,生死不明啊。”
万氏:“太后当时不也没有出面阻拦吗?”
太后:“你……”太后指着万贵妃说不出话。当时太后确实没怎么为佑樘说话,太后的确疼这个孙儿,尤其她还亲自抚养过佑樘几年。可谁都是自己孙子,四皇子她也疼,应该说是更疼。谁做皇太子都是自己孙子,自己都是太皇太后,她何必引火烧身。
皇上:“最后敲板的人是朕,母后还是不要责怪贞儿了。朕已经派了锦衣卫暗中调查。”
太后:“暗中?下令到各府各州,仔细找。”
皇上:“万万不可,太子出宫要是被其他歹人知道,只会是更危险,这件事只能暗中办。”
太后:“今个儿咱娘俩要说句公道话,你如今不止有樘儿一个儿子,你要传位别人,哀家也说不了什么。但樘儿活到今天不容易,丢了宝座也就算了,不能再丢了命,你要把他接回来,封个王,然后锦衣玉食一辈子。”
皇上:“儿臣明白。”
祖修和银溪带佑樘进了贵阳一处医馆。
大夫:“他不只是风寒,舟车劳顿,再加上他身体本就不好,所以才会昏倒。他也真能挺,早就该昏过去的。”
银溪:“他是太想找到他娘了。”
祖修:“大夫,那他多久能好?”
大夫:“状况好的话,也得卧床三五日,一定得悉心照料,他这体弱是天生的,你们万万要注意。”
三人住进一家客栈里,银溪和祖修在旁照顾。
祖修:“夜深了,我自己看着他,你去洗洗睡吧。”
银溪:“你去休息吧,他这个样子我有责任,他恢复意识之前,我绝不离开。”
祖修:“女孩儿熬夜对皮肤不好。”
银溪:“得了得了,睡觉去!”
祖修:“知道了,有事叫我。”
祖修一向了解银溪性格,很倔强,也敢作敢当,认为自己错了就会负责,拦也没用。
银溪一直在旁边照顾佑樘。佑樘说起了梦话,他几乎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数了个遍,最要命的是,他喊出了父皇、母妃之类的词。虽说是烧糊涂了说的话,也听不大清楚在说什么,银溪已经察觉不对了。一个从小进宫的公公,有个世侄?朱孝刚才是说“浮华”?“复还”?还是“父皇”?他,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这种种的一切,都指示着银溪,他是……
佑樘的汗越出越多,银溪看也快到早上了,要是佑樘有换洗衣服,就找祖修来换。银溪拿来佑樘的包袱。包袱里,没有衣服,只有盘缠,还有几本书,仔细一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要不要这样?多大了读这种书?银溪又发现一个绸缎小长袋,打开里面是一支毛笔,摸摸上面还刻了字——张崇龄。“张崇龄”三个字让银溪恍如隔世,头晕目眩,呼吸急促。银溪翻开《千字文》,里面的字写得和她写得好像,天下间有几个字迹相同的人呢?
佑樘刚开始用的书是崇龄亲手抄的,崇龄的笔都由张峦刻上“张崇龄”三个字。这些都是银溪过去最熟悉的东西,触动了银溪不愿揭开的回忆,可银溪就是想不起来,头痛欲裂。
佑樘清醒了点,扭过头来看到银溪手里攥着书,自己包袱摊开着,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管他什么风寒。
“放下,放下,谁让你动我包袱的?”佑樘白天被银溪踹下水也没有这么生气。
银溪也感到抱歉,“我不是想翻你东西的,”银溪马上放下了书,“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换洗衣服。”
佑樘拿过书来,整理着银溪刚弄的褶皱,“不要动这些东西,记住。”佑樘眼里布满血丝。
“不好意思,以后不会了,可是你怎么带着这些东西?”
佑樘原想告诉银溪缘由,一看她那张很像崇龄的脸,就退却了,在他面前讲崇龄的事,更痛苦。“读书人,带些书在身边,奇怪吗?”
银溪:“您都十四岁高龄了,还读这种识字书?”
佑樘:“怎么,不行啊?不知道深入浅出吗?”
“那你比祖修‘厉害’,这些他都不看了来着。”银溪发现佑樘没穿鞋。“这都入冬了,你不要光脚在地上。”
佑樘小心翼翼把东西装起来,手捂在上面,不想放手。
银溪:“不回去吗?等柳大哥抱你啊?”
佑樘瞄了银溪一眼,气呼呼转了身想回床,转得太急,头一晕,脚一软,眼看要倒地。银溪一把搂住佑樘的腰,佑樘下意识转过头来看银溪,四目相对。佑樘烧红了的脸更红了,银溪也因为没这么近距离看过一个男子,脸上发烫。
祖修刚好醒了,一开门,天啊,我是在做梦吗?这俩人,搂在一起?!还是银溪搂着朱孝?!祖修给了自己一巴掌,不是做梦啊!
银溪:“你干嘛打自己?”
祖修:“你还是先把手松开吧。”
银溪这才松手,佑樘丢了魂儿,直接坐地上了。
祖修:“他这是怎么了?怎么觉得更严重了?你们不会一晚都这么过的吧?”
银溪:“说什么呢?还不过来扶?”
祖修进门来,“朱公子啊,你这脸未免太红了吧?你熟啦?”
佑樘还很恍惚,银溪和祖修扶,他都没有起来的意思,我是怎么了?心怎么跳得那么快?我都认清他跟崇龄无关了,他是个男人啊,难道我……“啊,啊!别碰我!”佑樘噔的一声起来,几步回到床上,用棉被包住自己,嘴里念叨着:“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我一定是烧糊涂了!”
祖修:“他到底怎么了?银溪,你把朱公子怎样了?”
银溪:“没有。”
祖修:“那是他把你怎样了?”
银溪:“那他还有命在这里发疯吗?好了好了,你去街上买套男装,从里到外都要,他浑身都湿了。”
祖修:“那大小?”
银溪:“他跟你差不多高,就是没你壮,买瘦一点的。”
祖修:“那我去了,你看好他,我看他有咬舌的兆头。”
银溪:“快去吧,不要醒着说梦话。”
祖修和银溪轮流照顾,佑樘恢复很快,四天后,又一次准备上路。祖修告别银溪和佑樘两人,独自前往万里石塘,银溪与祖修相约京师柏府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