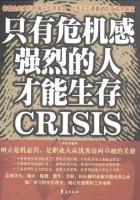虽然雨目找人补习打的是我的主意,但她还是会偶尔拿着不会做的题屁颠屁颠地去找靳唯一。靳唯一从来不会拒绝,他会让雨目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他自己坐在桌边,弯下腰,一手撑着桌沿,一手拿着水笔在草稿纸上细细地写下解题步骤。
靳唯一和我一样,极其清楚雨目几乎是数学小白痴的事实,所以他在讲题时,不会遗漏每一个细节,讲解时,也是不耐其烦,即使是草稿,他的字迹也清晰地可以与印刷体媲美。
他们讲题时,我就那么靠在窗下边的瓷墙,静静地望着他们,“忧郁得像个失了恋的小孩。”这是一次禹禾偶尔路过我们班看到我这副样子突发的感慨。
其实,望着他们的我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告诉靳唯一,其实他讲那么多,写那么详细,都是没用的。
因为雨目问他的那道题目问完他后还会再问我一遍,他讲的那些话,写的那些极其详细的步骤,我都会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甚至会重复二遍,三遍,甚至更多。
因为靳唯一讲题时,雨目从来不看题目。
只是不同的是,我讲题时,雨目就会认真地盯着题目。
悲哀如我。
之后
不知是靳唯一还是我的功劳,
雨目成功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杀到了前四百
最后一场中考适应性考试,雨目稳稳地站在了前三百五十名的排行榜。
我,依旧是年级第一。
而靳唯一,那个扬言要考崇德的小孩,却考了年级第五。
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但事实上,我们开始放假。
七天后,
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