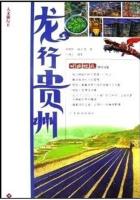老孙烧烤,坐落在鸟不拉屎的工人租房区,既不毗邻大街,也没有什么响亮招牌,甚至四周就没有一条能让超过三个成年人并排还能走得开的街,但因为小区落后,各种没有规划的建筑坐落于此,倒是小路四通八达,不熟系的人,只怕能迷路在里边,饿个半死。
但偏生这个店主顾虽少,但从来没有经营危机,只因这个地方是B省黑帮大佬秘密集会的据点之一。就如今天,马家扶植起来的八大帮派的扛把子有六人就坐在那吃烤串。
bai粉柄:“马老鬼这回真的成鬼了,现在马家老的老小的小,大姐马玲镇不住场子,诸位老大,我最小,就直接开口啦。马家的顶子我是不认了,今年的钱,我不交了。”
麻将发:“说的是,现在,马家基本名存实亡,手里还TM有几个人?咱们八家,单对单确实是干不过他,可他们还以为能凭着几个老弱继续只手遮天?要我说也不用多,咱们在座的六家联合,他们就TM不敢惹,我也不交钱了,诸位大哥,也该是咱们出头的日子了。”一时间觥筹交错,除了年纪较大的白头翁之外,可谓应者如云,就算是含糊其辞的,也都是默认了的。一时间雄心壮志,便是早该到的跛虎老董没到,也没心思理会了。
大富豪酒楼,B省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的字号,天台是个好去处,交错摆着十几张圆桌,安静闲适,风雅的很。天台边也摆着一张张不大的圆桌,红酒烛光,夜景美人,最显眼的是七号座,与别的桌上红男绿女不同,只有个四十多岁的胖子。
马司徒一个人上了楼,便直向七号桌走来,西装革履衬托得他更加挺拔,虽然娃娃脸显得过于清秀,但从内到外,自有一股气度,引人侧目,“二少,在下马司徒,不知可否与宋少同饮一杯?”
“你就是马家新当家?看来马家是真的没落了,让一个毛头小子出来站台啊,哈哈哈哈”宋少一点都不年少,剪裁得体的阿马尼西装也掩饰不了他那“度量”非凡的将军肚。四十多岁了还涂脂抹粉,这个人谈吐粗俗,胸无点墨,看上去就是个酒囊饭袋,可谁要是真把他当酒囊饭袋,恐怕就会死的连坟地都不用找,两百多年的家族,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独当一面的,更何况这个大腹便便的宋家二少是呼声最高的下任家主竞争者。
“二少说笑了,比起二少赫赫威名,我当然只能算是毛头小子,只是老话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想来二少对此该是深有感触。”小小拍了个马屁,马司徒不卑不亢的应答倒是让宋二少刮目相看。
“说吧,有何贵干?”
“二少见笑了,贵干不敢当。只是有事相求于二少罢了。”宋二少示意继续,“马家一直与宋家相交甚笃,自先父入行以来,也是坚定的盟友,如今二少初掌江南,B省重新洗牌,想来还是知根知底的自家人好用一些,单说马家的底蕴实力却也不是那几个废柴比得了的。”
“那又如何?”宋二少显得颇有些不屑一顾,“与我关系似乎不大。”
“关系总是一来一往慢慢交出来的,如今二少主管江南,我们马家正是时候尽一份力,”马司徒笑容有更加灿烂几分,说着拿起桌上82年拉菲给对面添了一杯,“二少贵人事忙,单单为了B省花太多心思不值得啊。”
“哦?”宋少似笑非笑,语气飘忽,却不端杯,说了句,“那我为什么要帮你那?支持你和支持他们相比我恐怕不见得少花多少心思吧?!”
马司徒已经不只是微笑了,他现在笑容灿烂的能吞下一个婴儿的拳头:“不劳二少大驾,马家家事自然由司徒自己处理。来,小弟敬宋少一杯,先干为敬。”“干。”两人相视而笑,不需多言。
“二少,容老奴多嘴,这个马司徒非池中之物,只怕养虎为患啊。”马司徒刚刚告辞下楼,隔壁八号桌站起一个老者,恭敬地对宋二少说。
宋二少笑得很有些高深莫测:“无妨,这世上从不缺少良材,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这个人的所要的远不足以与他的能力相比,我搞这么多,就是为了把他逼出来。”宋二少端起酒杯透过红的似血的酒,看着楼下缓缓开走的法拉利跑车,又抬头看看老者,“松叔,这个人不好得罪,有一个人,跟他关系很好,她若是跟宋家杠上了,宋家上上下下都不会好受。所以若是招惹了,就得先下手为强,还要一刀捅到底,不留任何尾巴,不然若是运气不好,让他逃了,就算只他自己,就后患无穷。说不得宋家都得给他陪葬。”说着幽幽叹了口气,“这世上从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谓“松叔”颇有点不以为然,宋家这一代兄弟六人,除了五少爷不愿涉足家族生意,其他几位个个都分管一到两省,家中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又岂是区区一个崛起不到百年的家族可比。只是他区区管家,不敢也不会去质疑主上决定罢了。
另一边,保时捷上,司徒看了看时间“九点半了,阿坤是时候上菜了。”拿起了手机。
烧烤店里,做bai粉的阿柄和开赌档的阿发喝的面红耳赤,划着拳谁都不理了,刚刚火鸦毛三吵着吃火锅,嘴里还抱怨着手下手脚慢,骂了两句娘,转头看见了白头翁一言不发,“翁叔,一晚上了,没听见您说句话啊,怎么连烧烤都不吃啊,难不成吃不惯考的?没事,待会咱一起吃火锅,哎,tmd这群没用的东西,总算是弄来了。”毛三看到火锅端进来了,立马转移了视线,没有看见白头翁脸上本来就苦的脸色,变得更苦了,【尼玛,吃,我tm今天能吃下肉去吗?!】
要说被压了几十年,早些年白头翁也曾想过有朝一日马家日落西山,为此他不惜忍辱负重,为马家鞍前马后。各种脏的黑的不惜身,可正是因此,老马把他当了心腹,看得多了,知道的多了,可知道的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不敢动手,甚至不敢牵扯进来,他今天来也不是因为被请,而是被派。眼前用煤气炉子加大铝锅将就的火锅里,那不时翻起的豆腐和大肠之类,白头翁不敢看,他怕他忍不住吐出来。
白头翁最后终究还是没忍住,吐了一地,自然没人敢笑他,就是同坐的老大们,无非是说了句翁老年岁大了,才喝了没几杯就醉了。
“彭”的一声,酒瓶落地的声音,摔得粉碎,bai粉柄捞起一块“猪脸”,只是那句“好大一块儿”的儿字还卡在喉咙里,他说不下去了,整个人立刻酒就醒了,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似乎所有人的话全都变成了鱼刺,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cao,是老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