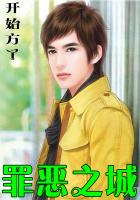安念说:“我知道她也恨我,因为我害死了我爸……”
“我姑一边打我一边骂,说我不是人!我害死我爸,又扔下我妈不管……让她到死都是一个人……”
他情绪更加激动,趴在那不肯抬头,手里的酒瓶更加用力地敲击桌子,那“咔咔”的声音砸得我的胸口也跟着疼。
我再次去抓他的手,他用力地把我甩开,继续使往桌上砸。
“我不是人!我他妈不是人!我他妈就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他那样狂暴地骂,似乎骂的是他最为痛恨的人。
他把心里对自己的恨意凝聚在右手上,手里的酒瓶狠狠地、一下接一下地狠敲,敲得桌面响得吓人。
“咔”
那个我认为很坚强的桌面终于承受不住他的疯狂,发出一声轻响后碎成很颗粒很均匀的一片,大部分掉在第二层的玻璃上,边缘的散落在地,像一块块冰糖。
一直伏在上面的安念被闪了一下,终于抬起头来,我看到他满脸的泪水,胳膊上粘着几块碎玻璃颗粒,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有没有血流出来。
我连忙抢下他手中的酒瓶过来扶他。
服务生再次被剧烈的响声引进来,表情明显比前两次不好,还没开口说话就看到桌上、地上极其晶莹的碎玻璃,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担心他说出指责的话会惹恼失去理智的安念,连忙示意着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赔,你都记在帐上,过会儿再有什么声音也别进来,损东西我们都赔!”
服务生又关上门走了,关门的声音有点重。
我拉了几次也没拉起安念,只好用果盘和啤酒罐把他面前的玻璃推向一边,免得伤到他。
即使这样的事故还是没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坐在地上,双手向后撑着地面,按在玻璃颗粒上恍然未觉。
他歪着头脑袋侧耳听隔壁的唱歌声,那眼神像一个精神病人。
听了一会说:“你听,他们在唱歌,多他妈快乐!可是我他妈这辈子连快乐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这么死皮赖脸地活着……活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这条命还给我爸和我妈……”
直到此时我彻底知道,他从前表现出来的不在乎生死,每一次都真的,他不是不珍惜生命,而根本就是想放弃。
他的故事我不了解,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妈妈有多恨他,根本无从去劝解,只想尽快让他醒酒或者是直接睡着,这样他就不会在这种情绪中越陷越深。
我挎起包儿,再次来到他身边拼命地往起架他。
这次他的意识终于跟随我一次,自己扶了下茶几站了起来。
我架着他往门口走,吃力地打开门后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他的钱包和车钥匙掉在沙发边上,又让他扶着门框等我一会儿,回头去捡起来塞进我包里,这才又架着他往出走。
他似乎又反应过来点,问我:“去、去哪儿?”
“回家。”
“我没家……”
“你喝多了,去我家睡会儿。”
“我没喝多,我今天比哪天都清醒……”
我不理他,架着他来到前台结帐。
前台MM没再用怪异的眼神看我,在计算机里看了看,叫我稍等,然后用对讲机问道:“经理,三个六的客人结帐,打坏的桌面怎么算?”
对讲机里哗啦哗啦地说:“桌面和地板算两千,其余的正常算。”
我在一旁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想到会要这么多钱。
前台MM又看了一下电脑后说:“桌面和地板的价格你也听见了,加上酒水和零食,一共三千七。”
我不解地问“桌面是我的砸的,我们赔,可是为什么要我们换地板?”
“玻璃掉在地上肯定会砸坏地板,而且更换期间那个包间也不能正常使用,收您这些钱已经很优惠了。”
我无话可说,暗骂安念不知要的什么酒,竟然贵成这样。可恨我根本没有多带钱的习惯,只能看看他钱包里有多少了。
我把安念从肩膀上移到吧台上趴着,掏干自己的钱包又翻他的钱包。
前台MM看着安念趴在那儿哼叽,一个劲催我:“女士您快点,不要让他吐在我们这儿。”
我终于凑够了三千七百块递了过去,然后架起安念出了歌厅大门。
出门走了没几步,被凉风一吹安念真的吐了起来,好在他还知道向旁歪身,没有吐到我身上。
来到他的车边我才想起,他醉成这个模样根本没法儿开车,于是又把他放在车边跑回歌厅麻烦他们帮忙存车。
交了存车费后再次出来,攥着事先准备好的零钱拦了一辆出租车。
这家伙还算争气,没有在出租车里吐。
回到家后又苦力一样把他架上五楼。
进到家门时已经过了十二点,苏佳红已经睡下了,看我把安念带回来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身上拽被子,问:“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喝成这样还不得吐得满屋子都是。”
我说:“没事儿,他在外面都吐完了。”
“那也不行啊,他一个大男人,我们两个女人,这在一个屋里住着也不合适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又不让他和你住一屋,扬扬不是还没回来么?”
苏佳红狠狠地翻我一眼,用被子一蒙头说:“行,随你便,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住扬扬那屋给你们倒地方……”
我气结,一边往里屋架安念一边说:“你都说什么胡话呢,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他扔你身边,他喝多了可没准真兽性大发……”
苏佳红又把被子掀开,冲我喊了一边串“滚!”
好歹把安念扔到扬扬床上,我累得胳膊腿都在打颤。
虽然刚才口无遮拦地和苏佳红调侃,但是再看到安念那苍白的脸时心里还是一阵疼痛。
这样一个放浪形骸的男人,谁又知道他的过去是怎样的,他心里装着的痛让人无法想像,相比起来,我为我那一点不值得的、有原由的痛而没完没了地伤怀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