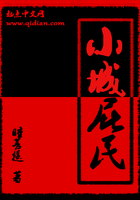明万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夜。
一条商船,趁着月色,静静驶入福建的大岞湾。甲板上的水手们有条不紊地转舵、收帆,将船靠向码头。
船老大站在船头,打量着一片沉寂的港口。海湾内星罗棋布地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渔船上微弱的渔火,随着海浪的起伏,上下摇曳,明灭不定。海湾深处,是大明福建水师的营寨。营寨中火把高张,明亮的火光,将营寨分割成一块块或明或暗的区域。巡营的兵丁,不时从黑暗中走入光亮之处,随即又隐没于黑暗之中。
看到远处巡营的兵丁,船老大似乎是松了口气,长嘘一声,随后走入船舱,一直来到底舱,走到一扇暗门前,轻叩三下,对门后说到:“朱义士,我们到啦。”
门后之人,听到通报,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呆滞片刻后,才颤抖着双手将灯火调亮,收拾好自己的物件,又从船舱的夹壁中抽出一封信来,信封上赫然写着“御倭急报”四个大字。这个人将信拿在手中,出神地盯着信封凝视片刻,喃喃道:“国安兄,我总算不辱使命。”遂将信揣入怀中,打开门,跟着船老大走上甲板。
来到甲板上,这位朱义士凝望着宁静的码头,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涌起一种悲喜交错的心绪,哽咽着说道:“十五年了!想不到我朱均旺还能活着回来!”船老大也不无感慨地说道:“是不容易啊,从日本回来这一路,真是辛苦朱义士了!”
朱均旺听了,赶忙向船老大一作揖:“哪里哪里,倒是要船老大冒险把我从日本带出来,将这一船的兄弟都卷入危险之中,才令在下惶恐,在下实在是无以为谢……“
朱均旺说着便要拜倒,船老大忙伸手托住他,说道:“朱义士不必多礼!林老板交待过,一定要安全护送你回来,何况你是在做一件为国为民的义举,我等虽是粗人,可也晓得匹夫之责!”说罢,船老大向一个黝黑健壮的年轻汉子喊到:“海伢仔,你带几个兄弟,护送朱义士去水师大营!”
“好嘞!”黑汉子应声而去。
船老大又对朱均旺说道:“朱义士,不知今后作何打算?林老板的意思是,如不嫌弃,可以在我们商号里为你安排个差事。”
朱均旺感激地说道:“请代我多谢林老板的关心,不过朱某确实不想再给林老板添麻烦了,况且在下多年离家,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个什么光景,报官之后,我想先回家看看,至于以后做什么,到时候再说吧。”朱均旺说完,不自觉地叹了口气,船老大也不愿再勉强,便拍拍朱均旺的肩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勉强朱义士了,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尽管到我们商号来。”
不一会儿,那个叫海伢仔的黑汉子便拉来了六七个水手。朱均旺看看这些年轻人,再次向船老大一拜:“大恩不言谢!日后若有朱某效劳之处,在下听任吩咐!”说罢,离船登岸,在那几名水手的簇拥下,向水师营寨走去。
“十五年,不容易啊,不容易……”船老大望着朱均旺远去的身影,兀自嘀咕着……
数日之后,一支商队出现在由安徽前往河南的驿道上。此时已近黄昏,这支商队已经是人困马乏,一个挂刀的护卫忽然从队首勒马后撤,立在商队一旁,待队伍中另一个骑马之人来到身前时,方才策马与之并驾齐驱。护卫舔一舔干涩的嘴唇对那后来之人说道:“邱掌柜,我看这太阳落山之前怕是走不到县城了,不如到前面先找个宽敞的地方休息一夜,明日一早再赶路。”
那位邱掌柜伸长脖子四下望望,所见之处看不到半点人家的影子,心中略觉得有些不安。
护卫看出了邱掌柜的犹豫,便说道:“放心吧,这条道我走了十几趟了,从没出过贼人,没事儿。“
邱掌柜前后看看押运的兄弟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却又满脸期待地望着自己,只得叹一口气说道:“好吧,前面找个平坦的地方,让大家休息。“随即人群中响起轻轻的欢呼声。
不一会儿,商队便走到了一处平地,邱掌柜吩咐大家休息,于是众人忙卸下行李货物,点起几堆篝火,埋锅造饭。
入夜之后,赶了一天远路的众人早已疲倦不堪,很快便沉沉睡去。护卫见几个手下也是哈欠连连,便让他们也都睡了,只留下自己只身一人在营地周围放哨。不一会儿,他自己也泛起困来,于是就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心想着这清平世界,哪有那么多贼人,便闭上眼睛打起盹来,很快,就响起了鼾声……
夜半三更,一片黑云遮住了月亮,营地的篝火在林风的撩动中摇摆不定,商队的号旗在火光映照下不时变幻着诡异的影子。晃动的光阴中隐约可见号旗之上,写着“永诚”两个大字。围绕着营地的树林之上忽然一阵轻微的响动,几个人影从树上落了下来,一袭黑衣,黑布蒙面,仿佛鬼魅一般佝偻着身子,悄无声息地向商队围拢过来,各自来到一个熟睡的伙计身后,右手从背后抽出匕首,轻轻抵向伙计的脖颈,突然左手猛地捂住伙计的口鼻,右手匕首迅速一划,割破伙计的喉咙。一阵短暂而轻微的抽搐之后,黑衣人放下伙计的尸体,悄悄转向下一个人……
护卫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努力睁开惺忪的睡眼,朦胧之中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他刚想眨眨眼睛看得清楚些,只觉得喉间一凉,似乎有什么热的东西流了出来,之后身体便无力地倒下了。闭眼之前,他看到几个黑衣人匆匆离去。几箱货被他们打翻了,白花花的东西散落了一地,护卫最后还在想:这么好的盐,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