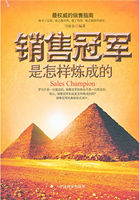51号走后,大个住了进来。他进来时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冤”,冤大头的冤。用他的话说:“没钱的人还得这种富贵病。”医生大致给他说了一下他的病情:“胸内有积水,肺部阴影不明显,是否结核还须进一步确认。”大个没有任何医保,属于纯自费人员。我总是看到他为住院费发愁。医生只对他说:“既然来了就安心住院,我们尽量帮你控制住院费用。”
大个住了两三天后,直闹着要出院,因为前期的住院花费很高,他已经用了四五千,而且医生好像还不能确定他的病情,他老是说:“住不起啊”。
大个几乎和病房里的每个人都聊得来,特别是病友的家长,几乎都很喜欢和他聊天。我得知病房里许多的事,几本上都是通过大个和她们的聊天得来的。他来的第三天早上,起床时痰中咳出了血,他赶紧叫来了医生。医生观察后,对他说:“你的分析结果昨天晚上出来了,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是结核,必须做纤支镜,从肺里面抽水化验。但是不管是不是结核,先给你结核药吃上,万一是结核也可先控制着。如果以后检查发现不是的,那再停药。你看怎样?”“要做纤支镜啊,那是干什么玩意的?”,期间他听病友提起过,做纤支镜不好受,费用也好像蛮高的,他不太乐意。“就是用支细管伸到肺里,看看肺里的情况。”“那费用多少?”“第一次大概要个八百,第二次就要便宜许多了。”“能不能不做啊!我觉得没必要。”“你这个不做不行,我们只能尽量让你少做几次。”大个没有说话了。沉默了十来秒,医生还是让他好好考虑下,必竟身体要紧,再者纤支镜是很紧张,要预约。
医生走后,大个就和做过纤支镜的病友聊起了天,几本上都在请教。我洗完漱,吃完早餐,聊天还没结束,各个有经验的病友,你一句我一句各抒已见,都有点小吵的感觉。打点滴的过程中,时不时大个也补充的问他们点问题。我只在想:他也太仔细了,不是他性格啊!打点滴的中途,医生过来诊断病情,他同意了让医生给他预约。在中午的时候,医生过来对他说:“已帮你预约了,我把你的情况跟他们说了下,为了尽量控制你的住院时间,他们同意让你插个队,你明天早上就过去做吧!”“噢,好。谢谢医生!”这一次又引爆了他的神经,他又向病友们请教起来。我在想:问多了还不如做一次,做一次不就全知道了吗。不想再听他们聊这个话题,我去走廊上看电视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大个趴在床上恶心的在吐。我心想:可能是刚吃药了,副作用。记得医生说过,每个人对药物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嗨,要么换药,要么药量减少慢慢适应吧。
第四天早上刚八点他就过去了。十点钟时,他带一点难受的样子回来。也无法吃早餐,先打起了点滴。休息了一会,病友才问他:“感觉怎么样?”“今天差点把我弄死了,妮吗医生什么操作,我都口吐白沬了”,大个有点生气。“怎么回事?”病友们都很好奇。“医生没叫深呼一口气,直接就给插进去了。完了,我感觉我喉咙出血,口里一股血腥味。我就嘟着嗓子跟医生说:‘先拔出来,我感觉喉咙出血了’。医生说:‘不要紧,擦破点皮是正常的。’然后继续,我真是难受的不行了,呼吸也呼吸不好,很恶心,忍着。一会我感觉他好像往我肺里喷了点东西。”“那应该是药!”病友们插了句。“顿时感觉好像溺水了,肺里的东西一下涌了出来,口里全是白沬子,直往外流。我憋着气跟医生说:‘呼吸不了了’。医生好像也有点担心了,马上把纤支镜拔了出来。对我说:‘深呼吸’。妮吗我嘴里全是沬子,喉咙里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呼吸,差点给背过气了。还好沬子流完了,我脸都白了,躺在那一点力气都没有,只知道喘气。最后那医生还在那说:‘起来,起来’。妮吗那会我动都动不了,怎么起来。那个医生太差劲了。”“纤支镜插进去后,你有没有乱动啊?”一个做了几次纤支镜的病友问他。“我都不敢动。”“我看你脸色还有点白”,黄毛插了句。“你要是没动,那不会呀,我做了几次都没什么感觉,只是一点恶心啊。”“会不会是你觉得你没动,但实际上你动了,只是你没注意罢了?”病友们想着各种可能。“给你做的时候是年青医生还是年老的医生?”大个问到。“有时是年青的,有时是年老的,年青的做的也蛮顺的。”“说不定给你做的这个是个实习医生,加上你是第一次做,有点紧张,所以才搞成这样了”,另一个病友道。正在这你一言我一言,病房里的实习女医生过来了,她对大个说:“刚才纤支镜室打电话过来了,他们说你做纤支镜的时候太紧张了,纤支镜镜头花了,看不清你肺里的情况,但是给你喷药了。这次没做成功就不收你钱了,你过两天…星期三再去做一次。”“是不是那个医生不熟练,我差点没背过气?”大个问。“他们说是你太紧张。这样,不管这次做的怎样,你星期三再去,必须要有化验结果,医生才能判断你的情况。”“…好。”
实习医生走后,大家又讨论了起来。“免费的,管他呢。反正喷药了,难受的总归是有点回报。”“我看还是你紧张了。”“说不定那医生欠操作。”“星期三再去看看,再做一次,这次是什么个情况差不多就知道了。”
总之他来之后,病房里整体开始比较活跃了。我这才知道他是东北人,怪不得隐隐约约感觉他说话有一股“大爷们”的味道,性情比较豪爽。他尤其和黄毛聊得来,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上班。渐渐地,他们就成了“哥们”。他来的第五天,吃完早餐就和黄毛一起出去了。晚上七八点回来后,就相互叫起了各自给对方起的外号:“大个”,“黄毛”。病房里还一个人和他们比较聊得开,他是付,也是这两天来的。他们三个人就聊起了出去的事。“你们今天回光谷了?”“他去他痁里看了下,后来就去游戏城玩了下”,黄毛说。“你们还玩游戏?好兴致啊。”“我在玩游戏,他在玩宝马奔驰。”“就是那个赌游戏币的?”“好像是的。”“他不是说他很历害的吗!怎么样?”“刚开始我以为他只输了一点,我去看的时候他只说他输了两百。我看着他最开始买了两百块钱的游戏币,那时他还有200多分,我想估计是一百块可能兑几百游戏币。一会我再去看的时候他有1000多游戏币了,我想本可能回来了,就让他回去,他说他再玩会,让我再去玩会。我最后去找他的时候他有3000游戏币了,最后全兑成钱了。我以为他只赢了三四百,谁知他告诉我他赢了八百。原来是一百块钱对200分,他第一次兑的400分输了又兑了1000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他输了六百了。”“那最后不还是赢了。”“我没想到他玩这么大,早知道我早拉他走了。”“你看吃饭的时候那服务员对你什么态度,你气都不哼一下”,大个打叉了。“服务员一般都这样。你看他染个头发,穿的又随便,加上看上去年纪又小,服务很会看人的,”沉寂了几秒后,付说道。“那我也没办法呀!”黄毛说道:“你那样对别人发彪也不好,别人只是个服务员。”“真是势利。告诉你,对付这种势利的人,你就直接把钱往桌上拍”,大个气还没消:“就给她看,谁瞧不起谁!”…
大个来的第六天,医生又给他抽胸水了。第一次抽是在第二天。抽胸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术,在病房里进行。只须给病人打点麻药,一根针插到胸腔里,再利用真空医用袋的负压吸出胸腔内的积水就行。说真的,看到那根长针筒,我的胸口都疼。每每有这样的情景我都会刻意避开,但有时手术在打点滴期间进行,那就没办法了。记得一次,医生给一个身材比较瘦小的人抽胸水,最开始胸水比较“清澈”,后来越变越黄,再后来就像黄泥巴一样,有点恶心了。最后在那人的胸腔内抽出了950ml积水,当时几乎整个在场的病人都惊叹不已:“真看不出来胸腔这么大”、“一下就少了两斤,多久才能补回来”、“两斤水在胸腔里,没水声么”、“真是不可思议”、“我估计整个病房他能排上号了”…
这几天下来,正常的费用应该有六七千了。大个开始为住院费发愁,医院已给他下了两次催款单。从他与病友的谈话中,加上他经常定医院外的外卖(这个外卖非常不经济但味道比医院的好多了。我定过一次三鲜汤,一点点磨菇,一点点白菜,加上估计不到一个鸡蛋,12块钱),我觉得这点医药费不应该难得住他。病友们的家长偶尔和他谈起家里,大个总是嘴不离“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在W市买房,把自己的爸妈接过来。后来他才说现在的这个住院他勉强还能承受,其实他家里还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
晚上的时候,大个经常躺在床上和他的女朋友打电话(他的女朋友听他说好像是去年在他老家认识的),再就是和黄毛聊天。也许是住得很久,大家都处于一种莫名的焦燥之中,晚上息灯时间慢慢提前了。刚开始只是大个、黄毛和付在聊,慢慢的整下病房的人都开始说话起来。我突然觉得有种卧谈会的感觉。话题主要是个人的经历,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部书。大个十七岁就从HLJ来到W市打工,主要是在餐厅的厨房里打下手,时常的被餐厅里的其他人欺负。那时他兜里从来不放一分钱,他说:“放了,也是他们的。”餐厅里的活他都是抢着做,这样过了两年,他师博终于收他做徒弟了。然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从那时起他的生活才有了起色。现在他在光谷的一个痁里当厨师,月工资3000元,再干个一两年就有资格拿到痁里的股份。他平时很喜欢交朋友,黄毛工作的美发痁也在光谷,黄毛的同事好多他都认识。经常听得见大个对黄毛说:“他可以深交”,“他只能做一般的朋友”,“最好不要跟他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