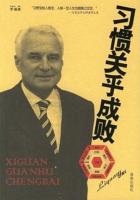时光荏苒,又是两年。
这两年间,大殷的皇帝逐渐年迈,遂由子息行使监国之责,边境外的番邦游民闻之蠢蠢欲动,却又慑于北国大皇子南征北战的声名。一时间,时局像是引而不发的箭,安静中有种骇人的气息。
边境问题中,最叫北国苦恼的,便是北漠骑兵的时常挑衅。这些游牧民族凶悍野蛮,没有稳定的政权和统一的信仰,无法有效地盟约或是和谈。
为这问题子息也曾禀报过君王,可衰微的君王坐在殿中,勉强撑着脑袋,挥了挥手:“一切交由你吧。”
子息知道,这一刻,他的时代来临了。
然而微妙的是,还不待子息稳稳地走上最高权力的舞台,北漠那边就急急快马来报——
“沙漠之狼”趁夜奇袭,一举歼灭了七族二十八部落,他们的王蘸着二十八颗首领头颅的血,学着教化之民,写下了向大殷请愿的婚书。
联姻,于国于民,再好不过。子息欣然接下了婚书,只是不曾料想到,打开这充满杀戮之气的红纸,里面赫然写着的是——“求永安”。
是求北漠永世长安,也是求北国永安公主。于一于二,大殷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
重华宫的大门从内锁上了已整整两年,当子息派人从门外询问公主的意愿时,门内的宫女一层一层传达着,好不容易等到细碎的脚步声,却只从门缝塞出片风干的红杏叶子。传信的内侍接过树叶,一时不知所措。
叶子上没有只字片语。
子息翻动着杏叶,嘴角一丝苦笑。“看来她是不肯再给我留下一言一字了。”随后叫来内务局的官员,“开始准备吧。”
一旁奉茶的棉鹿抓着脑袋,“殿下,奴才不明白……”
子息高举着泛着锈色的红杏树叶,正午的阳光透过轩窗,把叶子干枯的脉络照得透亮,金质的光沙仿佛血液般在枯叶中流动。
“杏,取‘行’之音。”
此刻望着手中枯叶,子息有所动容。她宁可老死荒漠,魂不归故里,这般决绝,可想北宫人事伤她有多深,自己负她有多深。
“枯叶赴黄沙,何苦这般折磨自己……”
十日后,皇城内张灯结彩,送嫁的队伍从重华宫沿着甬道一路纵深,一直列到了城门口。
适逢初雪,城中天地皆素白,衬得道上迎面走来的陪嫁宫女异常得显眼。红色的裙裾,黑色的双髻,像一株株只生长于山中雪顶的树……那是名为“鹤顶红”的山茶。难掩的哀戚浮在她们的胭脂上,坠在银色的钗环上,铃铃作响。她们是行走的无根之树,从山林走向荒漠。此去一别,再回故土便是来生了。
随行的仪仗队适时吹奏起庄严肃穆的礼乐,霎时间,钟鸣鼓点声响彻天际。
巨大的鸾轿被十六个轿夫抬起,在宫女的簇拥下前行着。
娄夙坐在重重红纱的轿子里,望着外面黑压压的人头、红得刺眼的衣裳,感觉自己像漂浮在黑色的海面上,又像绑在火树银花的枝头。真是讽刺,这一生都在他人的摆弄中颠沛流离。
她摩挲着鬓角垂下的红鸾流苏,轻笑到自己也曾被不甘人后的父亲唤作“凰儿”。娄夙的“夙”,本就暗含着百鸟朝凰的美意。如今,却连这样的名字也被剥夺了。
临行前,子息除去了她在史书上的正名。人们只知道,和亲的是位封号“永安”的公主,她怀着美好的含义,自愿成为了和平的使者。人们将永远怀念她。
这似乎是子息的初衷。曾经忠烈也好,忍辱偷生也好,悔恨也好,求不得也好,抹去了她的过往,也许就能还她一个新的人生。
---------------------------------------------------------------------------
鸾轿行至宫墙一隅,一缕清扬的琴声穿过负雪的藤枝、厚重的礼乐,与轿中人不期而至。
娄夙心有所感,命人停下轿子,隔着层层藤枝问道:“谁在弹奏?”
闻声,琴音戛然而止。等了片刻不见有人回应,娄夙心中一凛,一把扯住座下一名轿夫的衣襟:“快,背我进去看看。”
众人皆是大惊,却没人敢忤逆这位公主,只好等在积雪的甬道上。
拨开宫墙上盘踞的枯藤,墙内是一方隐蔽的空间,里面随处摆放着各式盆栽,只是入了冬都枯萎了,显出一种落寞的味道。正中的紫藤结得尤其好,枝条虬结出一片天然的帷幕,隐着下方一张安放妥当的藤榻。
娄夙示意轿夫把她放在榻上,“你在外面等我。”
轿夫退下后,她轻轻躺入榻中,望着头顶坠在枝结上的雪,对着虚空淡淡道:“是你在为我送行么?”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也不知是在问别人,还是问自己:“我一定是产生幻觉了吧,怎么会还有人挂念我呢……”
一小团雪轻轻抖落在娄夙脸上,她睁开眼,正对上一个久违的笑容。
来人从枯藤白雪的阴影处现身,带着点局促:“我本想静静地送你一程的,未想到你会找进来。”
子元看上去消瘦了很多,好在不见了那日分别时的病态。
“我也未想到,我害你如此,你还愿意见我。”娄夙抬眸,眼中难掩长久未释怀的罪恶感,望着那个低头对他微笑的青年转言道:“背上的伤可好透了?”
“两年,什么皮肉伤不能好透?倒是你……”子元触着自己的胸口,“心里的伤好透了么?”
娄夙撇开目光,“好不了了,如今都烂透了,倒也无所谓了。”她突然咬着牙,眉头轻蹙,“我不信你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为何要揽下全部的责任……还……”又顿了顿,“……编出那么蠢的瞎话!”
被提起那个狂热的谎言,子元面有绯色,“是有很多种办法,只是……”他的神色突然认真了起来,望着藤榻里依旧十指丹蔻、眉眼锐丽的女人,“想到你曾经那样烈性地以身殉陈,后来又那样败坏自己的声名……没人能这么轻易地放弃过往的自己,尤其骄傲如你。其实,你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尊严,即使毁了,你也想毁在自己手里,不是么?”
娄夙猛地把头一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他。
子元有些尴尬,笑了笑:“幸而我识时务,乖乖收拾了自己捅的篓子。万一也被你记恨,惹你再从我东宫墙头跳一次以证清白,可就不好了。”
子元自觉失言,沉默良久,又低声道:“瞧我这记性,我早已不是东宫太子了……”
许是风太过寒冷,许是落在脸颊的雪太过冰凉,娄夙躺着望着苍白的天空,目光再次被子元温和的眼眸吸引……
那夜他微笑着敬酒的样子,
他忍痛背她走过花荫的样子,
他坐在她床沿满身伤痕的样子……
他拆穿她的样子,
他调笑她的样子……
未曾见过的、他弹琴的样子……
再也见不到的、他以后的样子……
突然不敢想象,没有他这些样子的北漠,是个什么样子。
情不知所起。娄夙不由得伸手触上子元的脸庞,有一丝冰凉从指尖缓缓传来,传到心里。
在她还是陈郡郡主之时,总喜欢在冬至的午后避开守卫和侍女,一个人攀着梯子爬到寝宫的屋顶,背靠琉璃瓦躺在屋檐上,仰望微凉的天空,伸手触摸冬日的轮廓。
在西南之地,那是一年中最后一次出现的太阳。叫人倍感珍惜。
娄夙抚着子元的脸,弯了弯嘴角,“于我看来,太子殿下还是当年的太子殿下,做储君做皇子做到你这么傻,也是独一份了。”她的笑容还是那样淡,樱唇白面的盛妆上没落下一点暖色,却是她笑得最真的一次。
子元大笑,“彼此彼此,做郡主做公主做到你这么烈,也是独一份啊。”
娄夙何尝愿意这么伤人伤己,又何尝不知道子息对她是愧疚的,因而他想尽办法都要保住她性命。可他永远不明白,在她心中有样东西比性命更重要,它不亚于爱情。
似乎只有子元明白,只有子元懂。
惺惺相惜,戚戚别离,这样的场景一旦再混了个“情”字,就是混着剧毒的酒。
“为何……我最初认识的不是你呢?”她的手指微微颤抖,鲜艳的指甲轻划过子元的下颚,最后跌落在自己漆黑的长发中。
破城那日,她也不曾哭过,因为觉得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今日她更没想过要哭,因为觉得这次真的要结束了。
可是!那日子息却救下了她的命!
今日,你殷子元又……
“你们两兄弟都是疯子!!”她突然歇斯底里,泪水毫无办法地涌出。她猛地坐起身,垂下的手又紧紧扣住了子元的腕子,十指丹蔻生生掐进了他的血肉。红色的血从他白色的衣料里渗了出来,融进她火红的嫁衣里不见了踪迹。
她连声音都在颤抖,“同情一个人就这么有趣么?”这般绝望的……许是她一生最后一次渴求被爱了。
“……我不知道。”他轻轻拢着她,任由她发泄。他用衣袖附上她的脸,不去瞧她哭泣的样子,“我也不喜欢被人同情,所以也不会去同情别人。况且如你所说,做人做到我这个样子,又有何资格去同情别人。”
娄夙渐渐平复,“那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不知道。”子元从没深想过这个问题。或是,不敢想。
忽而风起,紫藤上轻雪抖落一地,惊得一旁踩着金钩的鹦鹉振翅呜鸣。
她突然吻了他。
藤上的金钩又轻摇了一下,鹦鹉歪了歪脑袋,啄去翠羽里洁白的雪花。
他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