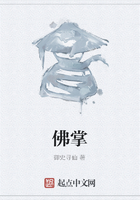一路柳暗花明,山清水秀,冰雪已经完全消融了,草色遥看近却无,鸟儿的鸣叫也清脆透亮起来。浮玉城已在眼前,不想转眼就是一年多,浮玉城主的音容笑貌还清晰浮现在鸠雅脑海里。
浮玉城如今是鸠嵬领地,虽经一番修理整顿,但还是残留着大战过后的衰颓,城墙上斑斑血迹煞是扎眼,有几处来不及修补的残垣断壁,在春日暖阳中更是残破不堪,就连影子也有些哀怨悲愤。
鸠雅隐藏在面具之后的脸上,肌肉不住抖动,眉毛拧成疙瘩,看到迎出城门的鸠嵬一脸笑容乱颤,他差点就没忍住,几乎想要上前拼命!
“啊呀,宗大统领,不想自上次一别,竟一年有余!大统领别来无恙乎?”鸠嵬上前牵住宗彝坐骑,不顾身份为宗彝牵马执鞭,口里不住说着,“我听得大统领亲自前来贺喜,整日望眼欲穿哪!大统领助我夺得浮玉城,我还没来得及致谢,今天定要一醉方休哇!咦,不知这位……这位兄弟却是何人?”
鸠嵬看到鸠雅戴着恐怖无比的面具,骑在一头似马非马的野兽身上,与宗彝并辔而行,心中好不惊异,可也不敢得罪,对着鸠雅硬生生挤出一抹笑容。
宗彝解释道:“鸠大将军有所不知,这位小兄弟乃是侯爷心腹,只因一场大火毁去容貌,故而终日戴着面具,不便以真面目示人,还望大将军莫要怪罪!”
“哪里,哪里!可惜,可惜了!”鸠嵬听宗彝如此一说,更不敢怠慢,急命小厮来给鸠雅牵马。不想那应龙刚烈异常,怎容得外人触碰,一甩头竟把小厮顶翻在地。鸠嵬却不在意,骂几声“蠢材”,便大笑着打头走进浮玉城去。
夜宴在丝竹管弦声中进行得很热闹,歌姬舞女都使出浑身解数,歌喉婉转,舞姿曼妙。鸠雅无心欣赏,悠扬的乐曲在他心里化作悲恸的挽歌,轻盈的舞姿则是沉重的招魂舞,他躲在面具后黯然神伤,一杯一杯复一杯,只想尽快灌醉自己。
宗彝对鸠嵬说道:“鸠大将军,此种靡靡之音,我等军旅之人无福消受,何不找人舞剑助兴?”
鸠嵬拍手道:“好啊,大统领真英雄也!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剑士,剑术独步天下,正好能为大将军助兴!”
歌姬舞女退出场,一人昂头挺胸走上前,他身体修长,手一扬剑已飞出鞘,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此人腰一弯,右手一探,稳稳接住长剑,剑尖朝上,左手捏一个诀,却是长右门剑术招式“祝融迎帝”。这招往往用来表达迎客尊客之意,他做得潇洒自如,又得体规矩,众人都齐声喝彩!
乐师们早已止住丝竹管弦,改敲大鼓。鼓声铿铿锵锵,如雷震长空,又如战马奔腾,直教人血脉喷张;剑士和着鼓点,如长鲸吸水,又如蛟龙飞天,舞得酣畅淋漓,让人目不暇接。舞至精彩处,众人眼里只见处处有剑士身影,飘忽不定又逍遥自在;耳朵里全是密集的鼓点声,人如亲临其境,仿佛处处都是刀光剑影。
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鸠嵬双目发亮,洋洋得意,看得如痴如醉。鸠雅站起来,大声道:“如此剑术,令人心生仰慕,我且和之,助诸公雅兴!”
宗彝想要阻拦,却来不及了。鸠雅已飞身到了场中,一运气,腰中宝剑自行飞出,悬浮在空中。鸠雅未曾学过剑术,当下以气御剑,将“黑蟒神功”招式使将出来,那宝剑也顺势飞舞,倒也气势如虹,一时和着鼓点与剑士舞在一起。
场下之人,见他二人一个洒脱轻灵,一个鬼魅阴沉,倒也配合无间相映成趣,别有一番滋味,立时又鼓起掌来。鸠雅瞥眼看到鸠嵬,心头之火又复燃起来,故意踩错鼓点节奏,让那剑士剑风一带,顺势手中宝剑就朝鸠嵬挥去。
只听得一阵惊呼,宗彝大叫着“不可”,鸠雅剑身一偏,从鸠嵬脑袋上方拂过,削下几缕头发。鸠嵬面如土色,呆在席上。鸠雅收住宝剑,冷冷道:“在下学艺不精,一时鲁莽,还望大将军见谅!”朝着鸠嵬鞠了一躬,心中却暗道,先留你项上人头,且用这几缕头发来祭奠老城主和稷柱氏族吧!
鸠嵬尴尬地坐着,笑也不是,骂也不是,最后迁怒到那剑士身上,吼道:“还不退下!怎能与客人争一时之胜,全无待客之礼!”那剑士只得悻悻而退。
次日离去时,主客又恢复了一团和气。鸠嵬将宗彝一行人送至城门外,悄声对宗彝道:“大统领,我昨夜写得一封书信,如在国中遇到麻烦,你可持此信去见我弟弟鸠炎,他正好掌管使馆事务。”鸠嵬又要派一队兵士护送宗彝车马,被宗彝婉拒了。
宗彝道过谢,带人前行。鸠雅行至鸠嵬面前,还看到他朝自己谄媚一笑,觉得更恶心了。
路过山伯葬身之地时,恰巧又是黄昏。此情此景,竟与一年前如此相像,鸠雅怕宗彝怀疑猜忌,故而没有下马祭奠,只是忍不住看那土堆之上摇曳着的青草和野花,心里默默祷告。
倒是宗彝大度,对鸠雅说:“去看看吧!我们在前面等你。”
鸠雅摇摇头,一行热泪在面具后流淌,慌忙紧咬嘴唇,催促着应龙一阵烟似的奔往前方。
又过得几日,快至夏州国都祝融城时,宗彝吩咐众人扯起一面旗帜,上书“龙侯国使宗彝”,大张旗鼓地投宿到驿站里去。子夜时分,宗彝和鸠雅乔装打扮,悄无声息从窗子里跃出,直往祝融城奔去。
两人渡过黑水河,站在城门下暗影里。鸠雅看着祝融城,心潮起伏不定,一年前差点丧生黑水河,如今又回到了这里,不禁涌起世事无常的感慨。
不一会儿,就有一人迎了过来,原来是国师瞿父派人来接应二人。宗彝和鸠雅随着那人沿着城墙曲曲折折走了一段,在一道小门旁停下,那人拿出国师府令牌对守卫说道:“国师府公干,速速开门!”
三人有令牌在手,一路通行无阻,半个时辰后就来到了国师府中。鸠雅二人被奴仆领到一处僻静石屋中,这石屋里没有什么奢华摆设,只是在中间矗立着一座丹炉,鸠雅还能感受到炉火的热量。
只听得一阵“笃笃”之声,国师瞿父拄着青木拐杖走了进来。瞿父依旧跟鸠雅印象中的一样,身体佝偻,头白如雪,唯一不同的是,他今晚脸色红润,似乎很激动。
宗彝和鸠雅躬身行礼,瞿父老态龙钟地道:“老朽等候尔等多日了,虚礼免了吧。侯爷可好,我当真想念他哪!”说着眼光久久停留在鸠雅身上,显然对于戴着面具的鸠雅感到很好奇。
宗彝也不客套,道:“国师不光想侯爷,也想这个吧?”说着从怀里掏出东君蛩交付的信封和一方木盒,递到瞿父眼前。
瞿父接过来,拆开信件匆匆浏览,眼里也露出喜悦之光,直到打开盒子,眼里光芒更炽热了。瞿父合起盖子,把盒子紧紧抱在怀中,恢复平静说:“侯爷盛情老朽心领了,国使尽管放心,接下来的事情,老朽一定办到!”
“侯爷说了,先让我将此物交给国师,等事成回国之日,再把这一份送上。”宗彝又从怀里掏出一册泛黄竹简,鸠雅看到上面写着“飓风术”三字,心里惊疑起来。这“飓风术”乃龙侯国武学秘籍,东君蛩竟舍得奉送给瞿父?那盒子里又装着何物,想必也不会逊色于“飓风术”秘籍,瞿父怎会对他族武学秘籍有了兴趣?
这些疑问一连串闪过鸠雅脑海,心想此次夏州国之行,果然没有白来,自己参与到一系列隐秘事件中,只能说明,离真相大白的时日不远了。
宗彝和鸠雅告辞后,又回到驿站,只等天明时再正式以使者身份入城。
瞿父却怎么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在石屋里朗声大笑,直笑得连连咳嗽才停下来。他走到丹炉旁,就着炉火再次仔细端详盒子中的事物。
瞿父将此物取出来,却也是一册竹简,竹简上赫然三个大字“寒冰咒”,原来竟是昆仑族秘典!瞿父将《寒冰咒》凑到眼前,逐字逐句审视,看到后面,见刻着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最后写着一个“羽”字,却是昆仑族奇才陆干羽钻研此经心得!
瞿父看到此处,确信此经不假,慌忙走到石桌旁坐下,拿出许多空白竹简,模仿《寒冰咒》上字迹一字不漏刻录下去,忙得一夜,已是筋疲力尽。待刻录好,又将竹简浸润到特制的药水中,最后取出就着炉火烘烤干,那竹简立时就泛黄颓败起来,与原件一样真伪难辨了。
瞿父来不及休息睡觉,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石屋,将仿照的《寒冰咒》交给一个下人,低声反复嘱咐几句,那下人就一刻也不停留地赶往国使馆去了。
瞿父重又回到石屋中,贪婪地读起《寒冰咒》,待读得熟络了,掩起屋门,打开密道钻进去,来到地下一间密室里修炼起来。
鸠雅一行人是在中午进入国使馆中的,他们沿着官道一路招摇而来,引起很多路人侧目。那些路人知道新世子订婚大典在即,四大部族使者陆续来到,都饶有兴味围在路旁对使者们评头论足,同时也对他们带的贺礼多少暗中进行比较,小老百姓总是对这些琐碎之事乐此不疲。
国使馆靠近国主宫西侧,两旁绿树成荫,又清幽又气派,可见当初修建时是花了一番心血的。这国使馆修建时,正值四大部族关系融洽之时,因而才耗费了不少力气,如今外面还维持着体面,屋里陈设已经老旧不堪,服侍的仆人也都漫不经心。
鸠雅才在屋子里坐定,就听到外面一阵大吵大闹,仔细一听,原来是昆仑族使者尖着嗓子训斥仆人:“狗奴才,你夏州国把我昆仑族看成什么了?竟然用这样的饭菜来招待使者,去,给我把馆长找来!惹恼了我,老子一把火烧了你这破使馆!”
鸠雅推开窗子朝下看,那昆仑族使者正在吹胡子瞪眼睛,觉得心中火气没有发泄够,不想抬头看见鸠雅脸上恐怖的面具,立即喝道:“你是什么人?戴个如此丑陋的面具在此装神弄鬼,吓唬到老子,你可担待不起!还不速速缩回****去!”
鸠雅不想节外生枝,正要忍气吞声,不料旁边的宗彝却回道:“睁大你的狗眼,我们乃是龙侯国使者!怎么,得了狂犬病,见谁都要狂吠几声?”
鸠雅本要劝阻宗彝,宗彝却低声对他说:“鸠雅,激怒此人,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鸠雅也骂起来:“疯狗,你在楼下等着,爷爷现在就下来宰了你下酒!昆仑族,我呸,不过是深山里的野人!”
说着,提剑冲到楼下,眼见一场冲突就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