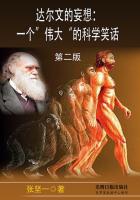周清听得那声吼叫声,便觉不好,正要发声,院门土墙轰然炸开,粉屑冲腾而起,土木幌噹倒塌。
一个巨大的兽影在烟尘中隐现。
大汉打着激灵跳将起来,手握钢叉,口中发出吼叫,是让里屋的妻儿快些逃命!
烟尘笼罩之下,看不清来者为何,但见其身形,竟是一前所未有之庞然巨物,更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荒山妖怪、洪荒猛兽!
他已经没有逃命的念头,只望妻儿能快些逃离。
吼叫声中,他还想要让周清快些离开,说不定还能逃脱得了性命,但在他嘶吼当口,身旁青年已经窜将出去,钻进尘雾之中,似要与恶兽搏命!
大汉拉扯不及,心中惨然,嘶喊一声,举起钢叉,加快速度冲刺过去,欲与之一起一搏性命。
三股铁叉刚插到半空,便被一股巨力拉扯,进退不得,好生难受。他心中更是绝望——不想这怪物竟如此厉害,只怕那青年已经丧身兽口了——自己怕是也难活得性命。只望妻儿能逃得快些。
大汉绝望万分,待要舍了铁叉,再行搏命。这时,烟尘土灰沉淀,身前的人影兽影逐渐明晰。
他看着眼前手抓住他钢叉的人影,不由惊然愕然。再看那巨兽,分明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只是这大虫比他曾见过的更要大上半拉躯体,几近两丈身长,蹲在那里,便是一座肉山。
虎兽就这么蹲坐在地,眼光瞟过他的身形,满含不屑。即便这样随意的一瞥,也让大汉寒意遍体!
他见着斑斓老虎不似要伤人的模样,又看着抓住他铁叉的青年,心中惊疑不定。
周清放开铁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这些日子就和他作伴了。前些时候出了点意外,没有走到一起,不想这畜生生跟了过来,还把你家墙给撞坏了。”
周清看着这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思及当日被顶下悬崖的狼狈,心中一恨,狠狠的往虎屁股上踹了一脚,“滚远点!”
老虎被重重一踹,惨嗷一声,闷声闷气的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挪了挪屁股。
它塌倒在地,用爪子指了指肚子,又嗷呜一声,指了指嘴巴,似在说“我饿了,要吃东西。”
周清看着这个吃货,有心不去理会,但又怕他继续撒泼捣乱。这虎兽已经成长得颇为强大,在空间外面,想要制住他,即便以周清愈发非人的体质,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他大汉歉意一笑,道:“我先将这畜生带出去安置好了。”
很快,周清又走了回来。他自是将“阿黄”收进空间了事。至于狠揍一顿,自然是免不了的。
空间愈大,空间里的各种动植物衍生得愈快,“阿黄”也不再拘泥于吃水果了。毕竟长久的肉食习性是改不了的;况且,空间里各类禽兽滋味也十分不错;随着空间里各种动物愈多,它偶尔偷食一些,周清也装作没有看见,倒是这老虎自以为得计,每次藏着掖着,吃完的骨头都要扒个坑埋上。
周清回到院子里,看着一片狼藉的庭院,还有院子里惊悸莫名、面面相觑的各人,心中更觉尴尬。
庭院的破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只是木门确确实实是被顶开顶破了,需要重新钉上,一部分土墙也要修补一番。
经此一番变故,众人虽然待他仍旧热情,但这份热情之中,免不了带上一些别样的意思。周清自觉强留无趣,便留下一大包鲜果,以作谢意,星夜北去。
周清精神,因着空间的变化,即便再累,只须三两小时休息,又复健旺。星夜奔程,待第二日早晨,东方渐露鱼白、晨露沾衣的时候,便见一条大河浩浩汤汤自西北而来,直往东南而去。
周清看得这条大江,心中有些奇怪:那猎户明明说是要走上五六天才能到江边,怎么我才走了一天就到了?
他倒不是怀疑那猎户骗他,而是在想自己是不是又走错了路。
此江正是猎户所言之**。
猎户当日从此处往南,携家带口,一路蹒跚,又躲避野兽,胆战心惊,哪里比得周清骑着从风之飞虎之迅疾?他所行之五六日,便被周清在一夜之间跨过!
周清自然是没想明白这其中缘故。但见此处平阔,一条大江滚滚之下,心想这大水之畔,必是文明发始之处,“我沿着这条河往下走,就不信找不到人迹。”
老虎的体态实在不适合乘骑。即便“阿黄”身庞体巨,他坐在上面,仍要费不少心才能让自己不再那不时的纵跃之中被抖落下来,故此颇有些疲惫,浑身骨骼,都像被抖落了架似的。
他进空间休息一阵,吃了些果子,才出了空间,准备继续上路。至于“阿黄”,自然是留着空间里,免得再吓坏了人!
周清出得空间。
此时红日初生,白雾濛濛,江面上一片茫茫然景象,不时水波与河岸撞击的声音传来,给这副静态画面平添了一股生气。
就在此时,一声唱和自江面上远远传来。
周清听不懂唱得是什么,唱得也不算好听,但声音却极宽阔旷远,远远的在江面上荡漾开去,回荡在四野之地,显得极为朗阔,竟与这初生之大日、宽广之江面还有那远远的青山应和出一副奇异的声色美景。这股声音就如同融入了这大自然之中,成为了天地之声,化作绝响,渐渐消散开去。
在周清还没回过神的当口,那迷茫的江面上,嘹亮的声音已渐渐远去,若隐若无,终至消失不见。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看到那江上之船、船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