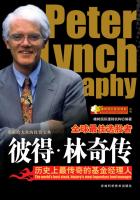春阳移近正午,暖色在漠林间徐徐铺开,温意无尽。
淡金色光辉穿透稀疏的枝桠洒落入空气,光光点点。
李星云微微抬首,缓阖双目,将身心暂埋于这片光影,让突然被尘封记忆惊扰的思绪,缓一缓息。
他一直以为,几年的寄篱生活足以令他将曾经的记忆放下,他也学会了沉着冷静。可眼前这个突兀出现的前辈,毫无预兆被挑起的儿时回忆,那颗骤然紧缩过了许久仍怦怦直跳的心,让他发现原来自己也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人,他所能承受的,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多。
这个年纪,他本该在父亲身边勤练武艺,勉习纲礼,再通过父亲的指点精益求精。
幼时的场景,时隔数年,却清如昨昔。他依然记得父亲看他的眸光,那样的温柔和蔼,欣慰悠长。
就像此刻顶上的阳光,散发着金色的暖意,庄重神圣,令他恍然将之与父亲重影。
若父亲还在,看到如今一无是处的自己,怕是失望透顶吧。
李星云心头泛起苦涩。
那片沉浮在他心中厚重的云层,那道紧捆着他喘息不得的血色锁链,那番午夜惊醒辗转难眠的无可奈何,全部化成一腔热血在他心头萦绕,却始终找不到出口宣泄。
他能听见身体里的每一处都在喧嚣,在呐喊,直至耗尽他的所有气力,再动弹不能。
对父亲的离去,他不愿承认,一心逃避,却也自知是自欺欺人而已。
他努力变得成熟,表现出超过本身年纪的沉稳,不是因为雄心,更没有什么大计,而是他想让自己能靠父亲更近一点,更像父亲一点,仅此而已。
原来,他极力想要逃开的一切,他从不曾弃之离去。
空中的光芒越发耀眼了,宛若一尊君主,俯瞰这片苍茫的大地。
李星云睁开双眼,将无尽金辉尽揽眼底,迸射出琉璃光彩。
逃得开如何,逃不开又如何,他李星云既有那般万人敬仰,至贤至明的父亲,他怎能闷着头浑浑噩噩颓然蹉跎。
能报得大仇固然是好,即使不能,也要潇洒快意活着。不追功名利禄盖世无双,但求顶天立地问心无愧,方不辱没了父亲英名,辜负来这世间一遭。
李星云眼中愁色怅然逐渐消失,取之将天空的万丈光芒映入瞳孔,敛进深处。
他本性聪慧,只因年幼方走错岔路对过去趋以逃避,如今千思万绪顺理清晰,混沌灵台清明如洗,整个人在明辉下破茧重生,神采飞扬。
不过半个钟头的时间,李星云像是变了一个人。之前的他谨慎机警,满怀心思,现在则是心无旁骛,坦荡洒脱。甚至连隐隐郁于眉心的阴云也消散了去,可见他是真的把一切想通,不再纠结于过去了。
老者将李星云的蜕变纳入眼底,暗暗称许。
以他毒辣的眼光如何看不出李星云心有郁结,需得开解。只是他想不到李星云竟能在短短时间内想通别人甚至十几年也难以放下的心结,果然是个慧智灵根的孩子。
也许他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让这孩子有了破茧涅槃的机会。可说到底他终究并非池中凡物。
或如山岳拔地而起,或似蛟龙一飞冲天,在不久将来,他必将以夺天姿态闯入江湖,掀起一阵暴雨狂风。
哪怕这天地风摧雪落,草木摇霜,他也能有闲庭信步,笑看山河的襟怀。
老者看着李星云在辉日璀璨中内蕴星辰外衍乾坤,心中笃定。
李星云收回心神,发觉自己刚刚竟然有股荡气回肠的豪迈之感,仿佛身在江湖闯荡多年,经风雨洗礼已然千锤百炼,志笃意坚,不再如从前那般畏葸难前。
虽然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模样,可心性却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如一污潭几经沉淀,去糟取精,留下清流澄净,再不与世俗合污。
又如久困囚笼的雀鸟,一朝振翅,直逼苍穹,凌甚垂天之云。
一转头,李星云发现那前辈正对自己眯眼笑望,不免有些羞愧汗颜。
自己刚才一番胡思乱想太过投入,竟忘了身旁还有个前辈存在,倒是让他看了笑话。
李星云却不知道,正是他刚才的一番胡思乱想为自己寻明了方向,这前辈才真正对他有所青睐。
李星云起身躬身一礼,道:“既然前辈事成,那晚辈就不打扰了,就此拜别前辈。”
这前辈虽是父亲旧识,但他行事果决狠辣,令人心惊。
若非他认出了自己,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想来他并非善茬,还是赶紧离开为妙,毕竟人心难测,不可不防。
李星云说完转身欲走。
“哎慢……等等……”老者连忙喊住他,“你小子倒是性急,怎么,怕回去迟了挨师傅骂?若他对你不好,换个师傅也不是什么难事。”老者似是不知李星云想法,话语间带着打趣意味。
李星云面露苦笑,“可能我资质平凡才疏学浅,因而师傅对我一直不大满意,倒也并非苛责于我,只是希望晚辈能有所长进。他老人家的一片良苦用心我还是知道的。况且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晚辈谢过前辈关心。”
老者啧啧嘴,点了点头。“你倒是个懂规矩的徒弟。”若真能令李星云轻而易举更门换派,那这小子也就不值得他如此上心了。
拍拍李星云肩膀,老者低头像在思索什么。李星云心里没底,却也不好开口。
过了会儿,老者抬头,直视李星云认真道:“今日你我相遇,本就缘分一场。你又是故人之子,看在往日情分上,我也确是应当对你照拂一二。这样吧,你有没有什么想学的,不妨说出来,我尽量教授给你。”
李星云眼睛猛地一眨,似是不敢相信。
这么好?什么都可以教他?真的假的……难懂他以前欠了父亲不少债务?
李星云心里暗自揣测着,忍不住拿眼打量。
七旬左右能当他爷爷的年纪,却只着一身破碎陈旧的短衫,脏乱看不出原色的单裤松垮垮系在腰上,一双前门漏风的老布鞋直咧咧露着几颗黑乎乎的脚趾,令李星云不忍直视。
全身唯一与白沾边的就是他那一头华发,却也是乱如鸡窝毫无形象。
李星云如今是知道他乃前辈高人,不然真当他是从边邑饥荒之地逃难过来的呢。
不过自己没钱没权,仅有的小命他刚刚却是放过了,难道真就白教白送大发善心了?
不管真假,且试试再说。
李星云思量一番后,略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