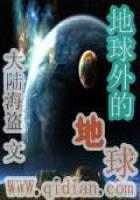当阿日斯兰从思考中醒过来的时候,场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大帐,留影石还在火堆里待着,只是快被柴灰淹没了——他瞥了瞥自己的大帐,不由感到一阵失落——就像很多年前他从邑城看花灯归来,回到寒酸破旧的帐篷时一样,只不过这次的触动更加强烈。
但他已经不是那个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孩子了——虽然他觉得自己喉咙有些干燥发火,胸膛里的心脏战鼓一般咚咚作响,血管大江大河般狂流不止——他强迫自己记起一些绝对能让他冷静下来的记忆片段——
“哈?你喜欢她?那你为什么不拿着马头琴去歌唱呢?——那个女孩当了你八年的侍女啊!你明明有八年的时间去让她爱上你!八年!”那个嘲弄的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而你最后却等得让苏日格这个乞颜小子抢走了爱人——你在等什么呢?等我死?还是等你弟弟发生意外好让你这个废物去继承我的一切?”
“我是怎么教你的?北原人的权威只能靠自己去树立!”
冰渣一般的声音刀子般扎进了他的心,疼痛让他迅速冷静下来,而他看过黄金时代的留影后,如此迅速的回复让对面的夏侯轻轻点头,暗自心惊。
“你说,”合鲁台咂咂嘴,失落又神往地问道,“黄金时代...还能再现吗?”
“很难了。”夏侯的声音同样有些失落,声音低沉道,“要恢复黄金时代,需要大地、天空和海洋的物产,比如大地的血液,比如大地的骨骼,比如风神的叹息,比如雷神的愤怒...这些东西都已经在第一次黄金时代消耗殆尽了,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长什么样子、该如何获取...
“这些物产在黄金时代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在‘守望者’观察到的时间内,再也没有恢复的迹象——就算恢复,这个时间也是如此地漫长,以至于需要昊天上帝舞动持开天斧几个轮回...
“大地已经没有盈余了,甚至只是在现有基础上稍微增加几倍人口,大地的承载就会崩溃...
“自黄金时代的人类之光熄灭后,大地上其实已有两次复兴:一次为白银时代,一次为黑铁时代。但是最终又相继熄灭。人类一度建立起统一的城邦、统一的帝国、甚至统一的天下!但一切都被时间再次淹没。仿佛有看不见的黑手在阻碍着人族的复兴...
“到了我们这次,就只能算是青铜时代了。即使人类的文明之火再次点燃,即使隐在幕后的‘守望者’携带着旧时代的火种,但复兴,一次比一次艰难了。
“我们像是被诸神囚禁在这片大地上的生物,是笼中的鸟,被圈养了太久,再也没有当初摘星踏月的实力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心塞,感到了冥冥中宿命的重量...
“但这些跟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什么关系?”阿日斯兰突兀地问道,眼睛依旧那么平静,他学着夏侯微笑起来,“无论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还是黑铁时代,一切都已经过去。复兴或者衰落,都像大雪山上的雪莲,东西虽好却离我们太遥远——这与现在的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从开始到现在,你让我们讲了黄金时代的故事,看了黄金时代的留影——但我们能随你这么久,却是因为你实实在在地拿出了一瓶‘源血’。”
最后,阿日斯兰微笑着看着他,一字一顿,“你的废话太多了,和你合作,我很不放心。”
合鲁台和巴扎有些尴尬,但少爷毕竟是少爷,既然不能反对,那么就沉默吧。
啪啪啪,却听夏侯欢快地鼓起了掌,他的眼睛里居然是掩不住的欣赏,“你说得对——但请你原谅,合作之前,总得互相试探——你已经赢得了我对等的尊重。”
“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人一起上路吧,你之前说让巴扎去萨满哪儿去要大雪山的信物,并说他就算把萨满脑袋砍下来也一定会得手,那么我们就去吧,去大雪山看看,看看黄金时代的财产怎么成了萨满教的圣物?看看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宗教怎么出了一个‘有人格的神’?最后——”
夏侯话锋一转,“——我会把操纵息...哦不,‘源血’的方法交给你——如果行动顺利的话。”
他诚实坦荡的发言和光风霁月的风度折服了骄傲的乃蛮少爷,阿日斯兰沉吟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重华,上地图!”
“少爷,带哪些人去呢?”合鲁台忧心忡忡地问道,“这件事情...牵扯到的人太多啦,有萨满老爷,有单于大尊,甚至还有拿颜...老爷——他们都是该知道些什么的人,可一个个都保持着沉默。”
“巴扎,你觉得呢?”阿日斯兰眉头一挑,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谨慎一点,”巴扎字斟句酌,“安答,就像你说的,黄金时代的东西就像大雪山上的白莲花——东西虽好却离我们太遥远。他们来历不明,身份未知,目的不清——寻找失落文明的宝藏毕竟只是他们自己声称的目的,而据我所知,能制造幻境的巫师虽说不多,但也大有人在。他们事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我们一旦失败,却得面临萨满教的愤怒——”
“我认为您得三思。”巴扎单膝跪下,行了一个庄重的礼。
阿日斯兰微笑了一下,“巴扎,我的安答,你说得很对,但是,你知道吗?——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幻境能制作得像是夏侯今天给我们展示的那样真实,一鳞一羽,纤毫毕现——巫师的环境更多的是通过语言的暗示和和手势的诱导,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才有可能实现——而我们今天全程清醒,跟你们关于细节的对照又是惊人地一致——这是一场机遇——”
“但你说得对,他们对我们了解太深,而我们对他们了解太少。他们所声称的不一定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有所防备是必要的,”阿日斯兰目光幽深,“事成之后,说不定还会灭口呢?但是——”
但突然阿日斯兰豪迈地打马而过,“北原人的权威只能靠自己去树立!我不想去继承了!我要亲手去得到!”
巴扎看着英姿勃勃的安答,目光也渐渐变得坚定。
当天晚上,阿日斯兰对着自己的伴当下令,凡是不跟着自己的箭射击的,斩之。那可儿们觉得这不是个事——跟着射有什么难的?马背上的民族谁人不会?不过弯弓、瞄准、搭箭、射击而已。
但阿日斯兰瞄准了那对价值连城的大宛宝马,突兀地射了过去,大宛马瞪着无辜的眼神,责备地看着往日对他们爱护有加的主人——爱马的北原人迟疑了,有些人悄悄地松了弦,不忍心来自西域的精灵,没死在挨千刀的慢慢偷运长途,没死在跟随主人征服草原的却无意义地死在自己手里。
最终,射箭的得到了表扬,不射的也没得到惩罚——松弦的人以为逃过了一劫,暗暗松了口气——他们只是被要求带着少爷的羊群去北边放牧,不得参与这次行动。
巴扎暗暗觉得那里不对,直到出发当天,他们像往常一样杀羊祷祝,向长生天祈求一路顺风时,负责仪式的伴当一直在打哆嗦,不敢打开盖过羊头的布帕。
巴尔嫌他们墨迹,自己径直向前,一把扯开,但这个汉子恐惧地尖叫一声,侧身闪向了一旁——于是大家看到了那几个血淋淋的东西,一时间有些呆愣,接着一齐沉默地看向一边冷漠无言的阿日斯兰
——这是那几个不跟着射马伴当的人头。他们几天前还一起喝过马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