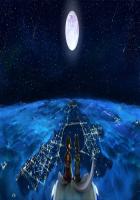12月的到来就像幽灵一样来的无声无息。然而这天气还没有远离热情的气氛。时不时地能在学校里里外外看到女孩那性感的臂膀和细腿在外面炫耀和诱惑。可见,大学本身也算的上是一块福地。
同梅景几次交谈以后,感情日益增长。他是十分有魄力的,并不像我经常有点优柔寡断,这一点让我特别羡慕。我们也经常争论在旁人看来是无聊的问题:时事政治、文学、文艺、哲学、网球以及漫画。(我因受到华子的影响也开始喜欢起了漫画)。后来,华子也加入了我们,他那安静的性格和梅景很投缘。
我没想到再过一些日子就是25日了——圣诞。这一天,耶稣担负了全人类的罪过,而上帝,却在这一天留下了罪过。
这一天,本该是我说再见的时候,玉晨承担了这全部的一切。
想不到,“诞”与“死”就这样在时间的水流中有了碰撞。
下午没有课,我呆呆地站在阳台上,看那像瀑布一样倾泻的雨。世人也许能够望断秋水,而这秋与冬交际下的雨我却无法看穿。
那天也是如此,因为下着雨,加上路段的缘故,我居然没有看到那冲劲十足的卡车向我撞来。也许事实并不是如此,是我非得将自己的心不在焉强加在雨和路地罪过上而让自己好受一些而已。总之,玉晨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危险,快走。”是的,我离开了,而他却承受了本该是我的命运的安排。只听得“碰”的一声,司机失措了。我的伞掉在了地上,望着被撞飞的玉成目瞪口呆。120,110都来了,他在我的身旁,而我却无能为力,那时候,一切都改变了。
有好几次,我在梦里碰到了玉晨,我问他:“你没死,对吧。”他笑着说:“我怎么会死?”我很高兴他能这么说,他怎么会死呢?
但是醒来后,望着空荡荡的墙壁,一切都没有了,你只能坐在那里怅然。我相信他不会撒谎的,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回答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梦与梦想是不同的。如果说梦想是辛苦着地人们所执着的信念,那么梦纯粹是人们在万般无奈下所获得的安慰。曼哈顿的乞丐在里面一下子可以找到昔日风度翩翩的身影;失恋的小子在里面可以宽容地原谅情人的离弃,并重新将他(她)拥入怀中;甚至濒危的动物一旦有了梦也会立马繁衍出好几百代,像孙悟空那样骄傲地喊一声:“孩儿们。”可,这只是梦而已。除了它本身的虚幻,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梦做的多了,我干脆就问他:“你已经不能回来了吗?”
他似乎不想回答,不想告诉我答案。可是没有答案就已经有了答案,没有告诉等于全部坦露。
很长时间里,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那一天我和他的处境对换,我会救他吗?会,不会,会,不会--------我发现原来我是多么的可鄙。
我就这样痛苦了一段时间,后来一位经济学老师无意间说了一个事实:救人的时候,其实多半不会有太多的思考,有时候那只是一种冲动而已,一种道德的催促。经历过后,也许不会再做了也说不定。”
暂且不论该理论对还是错,总之它救了我。我也由此相信我会扑上去的,哪怕我再胆小,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正这样胡思乱想着,齐国民大喊一声,俨然有张翼德大闹长坂坡的架势:“呔,睡觉浪费生命和青春,死人才会长久依靠这个。”
我回转身子,走进寝室,看到他用那双眯眯眼打量着我等5人。他指着众人:“瞧瞧你们这群没出息的样子,就知道玩电脑,哥真替你们和家长为你们的将来感到惋惜。看来还是得让我来拯救你们。走,跟哥打球去。”
胖——李正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滚,自己电脑坏了就瞎起哄。”
国民既不爱国,也不爱民,却有三大爱好:电脑、篮球和女人。电脑是因为时代在驱使,篮球是因为看了《灌篮高手》。别说,还真有两下子。至于女人,他喜欢经常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天生就喜欢玩一个新鲜感。
他等了一会儿,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和华子,华子假装没看见,我只是说累了。结果只能一个人可怜巴巴地走出了寝室。至于他会不会真去打篮球,那就不得而知。也许是跑到最新交的女友那边去“躲雨”也说不定。
我打开抽屉,从最底层找到了那本日记。封面我已经重新包过,纸张却有些发黄了。我缓缓地打开,听听那雨声,翻阅那雨是否渗入了我的心,翻阅那个陌生女孩的世界,以及翻阅玉晨留给我的思念。
我将这些日记的碎片穿行起来,伴随着玉晨曾经对她的留恋,交织成了这样的岁月:
她叫关岭月,每天开开心心地带着弟弟上学。这一天她终于上初中了,因为成绩优异被安排到全校唯一的重点班。之后过了一个月,校长带着一个男孩子——花心槐来到重点班,并安排让他做在了岭月的旁边。
奇怪的是,全班只有他不怎么爱学习。班主任在多次找他谈话无效之后,便找岭月:“岭月,老师知道你也为难,但是校长,也就是你舅舅说了,不能放着他不管。至于原因,以后我会告诉你的。你就帮助他,让他一心在学习上。”
在关岭月的心中,老师永远都是神圣的,何况还有她舅舅,她只得点点头。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心槐从没有正眼看过岭月,只是说了一句:“你既然那么爱管我,就帮我把作业做了好了。”关岭月自然没有答应。除了放学要去接弟弟以外,她一直跟着花心槐。心槐原本就有很多小混混似的朋友,他每次下课,中午或者放学都找他们去。现在可好,多了一个障碍让他十分不痛快。有一次,心槐威胁着说:“你再跟着我,我就打了。”
“你一个大男生欺负一个女生算什么本事。”岭月倔强地回答道。
“你--------我懒得理你,走开了。”心槐推了岭月一把,差点让岭月摔倒。关岭月硬是忍着泪水不让它掉下来,毕竟那时候还只是初一而已。
跟心槐混的朋友们就看不下去了,其中一个走出来说:“老三,算了,她爱跟不跟。我们几个可说好的,欺负女生的不是人。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