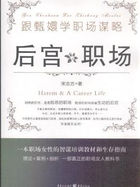国赛回来后,舒老师再也没和她争论过到底要叫老师还是叫远明的问题。喜欢怎样喊就怎样喊吧,没所谓。
而所有人也都这样叫了,舒远明的学生路北北。舒老师不再反驳,转而拿出了一整套谱子,肖邦的谱子。他是肖邦赛出身,所有人都知道,而他现在决定带着路北北好好弹肖邦。
“既然是我的学生,总要学一些看起来像我学生的曲子。”他说,“这样出去也好见人。”
“好。”路北北答。
她从肖邦的练习曲开始重新弹了,路过圆舞曲,路过夜曲,弹了叙事曲,谐谑曲,然后到波罗乃兹,玛祖卡,乃至奏鸣曲和协奏。肖邦的曲子很美,很好听,而更让路北北惊喜的是,她的想法很多与舒老师不谋而合。
“中国人生来合适弹肖邦。”舒老师解释说,“外国的钢琴家也会这么说。他的曲子里面有些东西和我们骨子里的很像。”
“所以我也会和你有一样的想法。”路北北说。
“是啊,我也挺诧异。我以为我在外面飘了挺久,有些事会不一样。但是没有。”舒老师答。
肖邦她真的弹得有模有样,而且那么好听。舒老师挺开心,她也挺开心。
而她也彻彻底底要把他的名字挂在前面了,至少在这座城市里是这样。本土这位天才钢琴家的本土学生,大家都喜欢这个组合。学校校报那个最多愁善感的老师说,如果舒远明遗憾地离开了钢琴前,至少路北北还在,我们这座城市总会有位好钢琴家。路北北不喜欢这句话,舒老师就一笑而过。
“那谁说得好呢。”他说,“过去,将来,谁知道。总之你要好好弹琴就对了。”
舒远明的学生路北北,一年多之后,她与舒老师一起演出,报幕员也是这样说的。她弹主旋律,而舒老师在副部托着她。下台时他也牵着她一起谢幕。路北北看着身旁穿演出礼服的舒老师鞠了躬,她也赶紧弯下腰。
“你知道远明跟我们摆多大的谱吗?”
音乐厅后台里,乐团的老指挥说,“他一回来,我们就找他想弄点什么曲子,他就是不同意。可现在——”
他看看这会儿躺在地板上的年轻钢琴家,刚下台,他还得躺着。
“这次是他主动来找我们的,想带着你来。”老指挥向路北北说,“这还了得?他还敢说是自己领你,明明是你领着他来。不是看在你的份上,就冲他上次回绝我们那一次,我就要把他踹出去。”
“谢谢您看在路北北的份上,赏我口饭吃。”地上的钢琴家说,带着笑。
“那是。路北北上小学时候我们就合作过了,她比你资历深得多。”老指挥说,“那时候她在钢琴前一坐,我站在指挥台上,只能看见一撮头发。就那么小。可就算她那么小,台下也是满座。”
“今天也是,观众都是冲她来的,和我没关系。”舒远明又笑道,“不然我就去弹主旋律了。”
“你弹没人听的。就得是她。”老指挥说。
他说着递给路北北一个小信封,出场费。“这是你的,你老师没有。”他说,“你乐意给他点零花钱,就给他。不乐意给,就自己揣着。”
“别啊,起码要赏我点饭钱啊。”舒远明说。
“那你要跟北北好好聊聊。”老指挥答,“她开心了,没准就分你点钱,买个茶叶蛋。”
舒老师和这位老指挥的关系其实很好,他是他出国之前的恩师之一。伤病回来,舒远明仍是登门拜访了这位指挥,拖着身子也要去。饭钱没要到,心碎了的舒老师躺在地上思考茶叶蛋的滋味,老指挥又看看他。
“行啦远明,你也就出来这一次了。”他说,“别再折腾了,好好歇着吧。”
“我知道。”舒远明答,“不过北北——”
“北北在我们团里,比你资历深多了。”老指挥重复道,“什么时候她心情好,才能带你来演出。不然你就老老实实在家躺着,看她上台。”
那的确是舒远明回国以来唯一一次正式演出了,此后再也没有过。而路北北和乐团又再合作了一次,舒老师真的只在台下。课还是照常上,两人上一次演出很愉快,舒老师就带着路北北弹了更多协奏曲,还有四手联弹,还有双钢琴,还有声乐伴奏。
多一个人合作总是会有趣好几倍,他这样觉得,路北北也这样觉得,不过自此他躺着的时间也更多了点。弹琴久了,舒老师有时也会和路北北开开玩笑,故意弹得让她跟不上,路北北累死累活追到了他的世界里,几个和声一换,他又把她丢开了。
“你放过我吧。”路北北说,“我跟不上你的。上一秒还在河里划小船,下一秒就飞上天了。”
“好吧,我这次保证不丢下你。”
他坐到那架旧立式琴前,路北北守着小三角琴等着他。旋律起,路北北就跟进去,一问一答两乐句,路北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另一架琴在向她说什么事情。是什么,暂时不知道,但他们在慢悠悠地聊。
她就安下心来,试着去捕捉琴声里的话语。静谧长夜,雪花纷飞,两个老人在暖炉边的摇椅里慢悠悠地聊天。过去也曾有这么大的雪,那是多少年前那个冬天——是这样吗?是啊那时是雪夜,一片漆黑而我们点起灯火——那一定很温暖。不止有灯火而且有歌声,旧时的调子我还记得——你不如唱它出来。好的,这调子是如此——咦,我也会唱。
一瞬间,两架琴的和声走到了一起,一高一低唱出同一个主题。终止式响起的那一刻,路北北情不自禁向舒老师那边望了一下,果然,他也回头看了她一眼。
“你喝了什么茶?”他问。
“红茶。”路北北脱口而出。
她一下就愣住了。是的,摇椅里的老婆婆拿着杯茶,橙红色的茶叶在阳光下起起伏伏,茶水就映出闪亮亮的光芒。
“你看,我没丢下你吧。”舒老师说。
“我突然觉得,和你一起弹琴会很危险。”路北北说,“每件事你都知道,所以每件事你也可以很容易就篡改了。你要是想让我弹不好,那我就弹不好了。”
“可你这次弹好了。”舒老师答。
路北北扭过头不看他。“幸好上次演出你也没想着让我弹不好。”
她那么认真,舒远明忍不住又笑出了声。
“为什么让你一说,这事情听着就很吓人呢?直白点,不就是合奏时候想到一起,效果就会很好,没想到一起,就会出演出事故嘛。”
“这个——”
“对吧。”
“但是就是很吓人啊!为什么你知道我在喝茶啊!”
“因为我就是知道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能不能换一个?”
“那就,嗯——因为你弹得出来。这样很好的。钢琴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想说什么。”
“可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喝茶。”
“那你就连想都不要想。音乐不说谎,你又表达得很清晰,怎么藏得住?更何况我还坐在你旁边一起摇椅子呢。”
无言以对。路北北爬回琴前,自己开始弹独奏,这一次想怎样来就怎样来。一条小练习曲弹完,她终于觉得茶杯摇椅午后阳光都不见了。她从舒老师那个世界里脱出来了。
“对了北北。”舒老师突然说,“你和我弹合奏,的确是一直在跟着我走。有没有觉得不甘心?”
“啊?”
“有时会吧。”舒远明答,“就好像演出的时候,人家介绍你,总会说一句舒远明的学生路北北。这几个字在前面,其实有时——挺头疼。”
“不,我就是你的学生啊。”路北北答。
“以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他说,“你会有你自己的曲子,你自己的肖邦,你自己的舒伯特,你自己的音乐。那个时候,你就会愿意被人叫钢琴家路北北,而前面不加任何人的名字。”
“会吗?”路北北问。
“一定会的,每个钢琴家都会这样想。”舒远明答,“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音乐。”
路北北低下头,是有过的。“但是我自己的音乐,怎样才会有呢?”
“你一直都有。”舒远明答,“你的小河小船,你的肖邦,你的960。尤其是960,我没有教你太多,因为我弹得不够好,可你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
“但还是没有你弹得好。”路北北说。
“方向对了,只是还不够。”舒老师说,“但没关系的。只要你一直走下去,总有一天会到达那个地方的——曲子真正在的地方。”
“那时就会和你弹得一样好了吗?”
“怎么这么没志气?要比我更好。那时我就会和别人说,看,虽然我根本不懂怎么教学生,可是这位叫路北北的钢琴家,我有幸教过她呢。”
将来可能是个比舒远明更好的钢琴家,现在暂时还是舒远明的学生,不管怎么说,路北北三个字不会变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