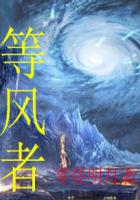静本身并不出奇,因为这是所有人都曾有过的体验。但想心常清净可就不容易了。所以从修为境界上来说,偶然入静还不能算修行突破。只有勤而行之,习以为常之后才算有所体悟。
经了这么多的事,我好像有些进步了。虽然总是有各种意外,牵绊着我的心,但是吃一堑长一智,我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已经悄然改变。这些无所谓是非善恶,只是对心性的不足有些补益。
或许我还没有随时随地都能入静的本事,可这种体验却是越来越频繁了,与之前完全无法入静有着天壤之别。可是很遗憾,静中的种种体验我都没有感受到。至于神通法力,那更是一句笑谈。古月的境界也就如此,他为什么有那样强大的神通呢?
心中有许多不解之事,但是静坐之时,心思却渐渐淡了。不管我主观如何想,心念都渐渐澄澈。心静之后,思维会更加清晰,而且不会轻易被扰动混乱。可我的修行尚浅,想要静下去根本就不能想太多,一旦心念过重,静便会被打破。
于是我放弃去寻根究底,放弃了雪恨报仇,甚至连七情六欲都渐渐远了。我说不清这是主观的一种淡然还是修行的必经阶段,只是觉得包括自己在内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事后想起来,这也是很可怕的,我的修行从一开始就出了差错,所谓的静似是而非。
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有了特别的感受,吓得差点就坐不住了。
由于元神没有显现,所以我无法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我不敢贸然动弹,只好苦苦忍受。
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肾部,虽然我不学无术连肾在哪儿都不知道,但这一刻,我无比确信。最开始的一瞬,就感觉把肾放在油锅中煎一样,差点没叫出声来。勉强收摄心神,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忍住,我担心修行出了差错,所以不敢随便动。其实以我的境界,动不动根本不妨碍,因为修不来所以也就不会失去。收功也是有一套方法的,但我平日里根本就用不到。
如果直接从修行的状态中出来,那就跟散功没有差别,修炼得的好处十成起码要散去五成,所以收功尤为重要。除此之外,一旦发生变故,用收功的法子也能做出点补救。所以我忍住诸般不适,准备收功。可就在念头刚起的时候,不适感消失了,热油锅变成了滚水锅。双肾像是泡在了热水中,既温暖又柔和,感觉异常舒服,甚至都忍不住要呻吟了。就像是大冬天泡温泉,但是温泉只泡皮肉,现在却是泡着形神。
我努力克制着心头的愉悦,尽量冷静地看待这一切,同时又将心头的种种念想和诸般感觉一一剔除,尽量保证心态的平稳和内心的宁静。其实我的静境已经被打破,但我自以为还能维持。
愉悦同样是不长久的,两肾正在舒爽着。一股要命的寒意突然出现在内心深处。这么讲也不准确,寒意是同时出现在心脏和心灵中的。原本双肾泡汤浑身舒爽,从里到外都懒洋洋的。这股冷意骤然出现,心脏猛地收缩,让我一下子惊醒了。就像是被人从温泉里一下子扔进了冰天雪地中,真是苦不堪言。
不过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寒意很快就消失了,变成了一股清凉的感觉。就像是三伏天的一根冰棍,让人好不舒爽。一冷一热,一紧一松,我只觉得身心都得到了洗涤,比前辈牺牲一具化身射出的箭还要有用。
而与此同时,浑身上下气机自发而动,在身体中运行。我既没想着去控制,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即使想用道种中的周天搬运之法,也是有心无力的。周天搬运有好几种,分别适用于修行中的各个境界。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河车搬运,不过我连稍微操控一下都做不到,也就没必要生出这样的心思了。
可现在我偏偏想起了河车搬运,有这样一句口诀——“三车拉上昆仑顶”,我周身之气的运行似乎与之有些暗合。但这是采大药过关才会出现的情况啊。难道我也跟古月一样,境界突然就突破了?
正在做着大梦,想着好事,气息却完全混乱了。刚才还是从海底自发而上,而后又从天庭垂落。现在却是乱糟糟没有明确的路线。如果是我自己控制气息运行,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坏了。胡乱导引,很容易出问题。可是气机自发而动就不用多管了。我只须尽量保持内心的平稳,克制自己的欲念。
修行人所说的打通经脉与武人所说的不同,武人所说的打通经脉与凡俗之人又有不同,但是凡俗之人都将其混为一谈。普通人想要活着,百脉俱通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必然命不久矣。可是有不少练气功的整天要打通什么气脉,真是害人害己。普通人的先天元气在经脉中运行毫无阻碍,甚至连一般的修行人都没法轻易控制。普通人找到所谓的气感后胡乱导引,使后天谷气运行其中,简直是找死。幸亏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强,一般的折腾坏不了性命。
武人似乎没有提过打通经脉,如果非要附会,也只能理解为内劲和真气的运转。领悟内外之理,内劲和真气就可以遍布周身,直至神通显现。
修行人也是一样,似乎也没有提过打通经脉,唯一有点关联的是通三关。其中运行的是神气或者说是真气,按我的理解大约与所谓的法力差不多——精气神之理实在不好懂,我都不敢去深究。
体内自发运行的气渐渐平稳,也不知道这是股什么气。其实我真的不想分辨清楚,因为实在太累。按惊梦的说法,要少想些东西。心思少了,欲望就少,很多时候已经明明察觉出苗头不对,但偏偏自欺欺人……
气息终于平稳,只是心肾等处还有一些奇怪。肾中有水欲上涌,心中有气要下降,我的意念完全被禁锢在心和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