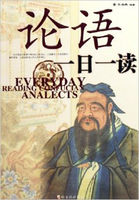胡里却仍是一副闲闲散散的样子,只懒懒地站在那里等他进招,眼睛却抽空,又望向了胡璃。
行空双掌翻飞,招招狠辣决绝,掌影翻飞,掌风所到之处嗤嗤作响,白气飘散,只盼立时毙了胡里,以泄胸中恶气,胡里明白他的心思,从不与他以实相抗,只管闪、转、腾、挪,逢到实招只管避了开去,碰到虚招,便伺机以巧借力,虽不得手也必出言相激,叫行空面上难看。
如此堪堪拆了三四十招,行空竟没占到丝毫上风,忽然行空纵身而起,他使出一招“泰山压顶”向胡里头顶和胸口同时拍了下去,胡里自然不敢硬接他双掌,旁略侧步,闪了开去。行空身在半空,见胡里****相避,旋即也在半空变了招式跟了过来,胡里便回踏一步又自立定,见他僧袍肥大,于是心念一动,也向行空劈了一掌,不过他这一掌却不是劈向行空的身子,却是自下而上,推向行空的僧袍下摆。这一掌,掌风疾劲,将风衣下摆掀起从下往上浮了起来。
行空正自而下双掌齐下,这一番没打着胡里,却将自己的袍子灼了两个是手掌形的大洞。一时布料燃着的焦味儿便散了开,那两个手掌大洞便挂在他灰色僧衣之上,好不尴尬。
见到行空自己烧了自己的僧袍,义盟中几个江湖客忍俊不禁便笑了出来,觉得不对,忙强自撑住,忍了下去,那笑意却是挂在脸上一时散不去。偏是这时,那只被放脱的白鹅振翅“嘎”的大叫一声,在院内转了几圈,仿佛也在嘲笑行空。
行空原本性如烈火,这下更恼,不由得开口骂道:“贼狐狸!你大爷的!打不过我便是这等阴损奸计!”
胡里使诈耍弄了行空,自己肚内好笑,却正色道:“和尚自己送上门来挨耳光,自己给自己烙了手掌印,却都来赖我”,他借此时停战的片刻,又转头望向胡璃,心想:“若在往常,她看到我如此作弄敌手一定开心的很,可惜现在却是伤心难过,又对我起了疑忌。”
胡璃被谭如山拉出战圈后,并未望向这边观战,只自己坐在地上,默默流泪,她无神呆坐,胡里却在心中不住地转念:“是谁杀了汪母?那两个先我进入观音院的人是谁?凶手为什么要杀汪母?今日被冤该如何洗白?平日里被冤的也不少,也不去在意,便说我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掳人新娘都不在意。今日这般却关乎小狐狸的亲人,倘若她也信了这些话,便要将我视作仇人。”
恶斗当前,饶他机敏也想不出结果,行空挥掌正要再来相战,却被如山剑庄的庄主谭如山给拦下了,谭如山出言道:“行空大师且暂歇一歇,你性子直率刚烈,确实容易着了奸贼的道儿,不如让我来试他几招,看看大盗狐狸究竟是怎样的功夫?”
行空面红过耳,不肯住手,怒道:“此时我们胜负未分,怎么好半途而废?”其时武人比试,必要分出胜负才歇,否则不尴不尬,反被武林同道看得清了,慷慨豪烈些的说这事时便讲“互无胜负”“点到为止”,阴损刻薄些的便能别说些“贪生怕死”“软骨头”之类的阿臢言语。江湖人极重面子,何况此时是代这院中众人出面相斗,斗到一半叫自己没输没赢的退场,那传将出去可是丢了极大的脸面,是以行空不肯退出,非得自己拿了狐狸才罢。
谭如山自然知道这些江湖规矩,出手拦他确实另有深意,原来他听说了复唐之事,于是派了子侄来打探,听得了切实的消息便有意入伙,此时他还未曾被正式引荐给汪义泽,只知这汪义泽就是复唐盟主,并且此人在江湖中、官衙内都颇有些名望。今日本是就要正式拜会这位汪帮主的,恰逢他母亲惨死,若此时自己能一举擒杀这凶手,岂非大功一件?对这复唐盟主既有恩,那么今后在军中、在帐下自都是地位尊崇,待以后得了天下,汪义泽自然也能在新君面前多进美言,得进庙堂高位了。
行空不知谭如山心中是做的什么打算,只想挽回自己颜面,于是摆手请谭如山一旁观阵,说道:“谭庄主稍候,若再走二十招我双掌还劈不了他,再请谭庄主下场捉狐狸”,心下暗想:“我自负武功高强,功力深厚,如再倾尽全力二十招还拿不下胡里,那也说不得,再无脸面在这复唐义盟中呆下去了。”
谭如山不愿将这功劳让给行空,盼着烈性僧人败了才好,那时自己一手擒住胡里,才更能显出自己强过了他,于是出言相讥:“行空大师,我瞧这狐狸的功夫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狡诈的紧,你几次三番上他恶当,须得当心在意,也不用说定在二十招之内,便斗个三五十招拿了他下来也是好的。”他这话中明着是示好关切,暗着却是绵里藏针说胡里的功夫不怎么样,可是行空却难以胜他,须得再多番游斗,才有把握。
行空性子烈,脾气直,人却不傻,谭如山话里的意思听得明白,于是冷哼一声,瞪了他一眼。
胡里不理他二人说话,已自行走到胡璃面前,矮下身子轻声唤道:“小狐狸”,胡璃低头不语,只抬了抬眼睛,胡里见她伤心难过,眼睫之上还挂着泪水,温言道:“小狐狸,姑姑去了,你定是伤心极了,要哭便哭吧,哭出来倒是痛快些,不过你不用怕,姑姑没了还有我,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你的。”
胡璃看着他,泪水不止,心道:“若是换个时辰,换个所在,我听你说这样的话宽慰我,定会伏在你怀中痛哭,让你哄着我。可是现在人人都指认你是我的仇人,应该杀了你给姑姑报仇。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她心中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直起身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你是凶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