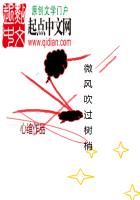我看了一眼写字台上摊开的字画,意识到,对阿姨而言,那并非只是怡情养性的爱好。阿姨说,我不怕忘记所有的伤害,我就是怕有一天,我老了,我会把妮妮忘记。阿姨一句话,叫我顿时泪流满面。我从来不知道,看上去那么要强的阿姨,会有这样多愁善感的情绪。张了张嘴,我想说点什么,而阿姨并没有让我说。她的话还没有讲完。
也是那年冬天,放寒假了,你们老师说要补课。不知为什么,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早上起了大早送妮妮去补课班,虽然手上戴着很厚的手套,还是冻得不行。冬天的早上,街上人很少,店铺都关着门,我手指头冻得像轻轻一敲就要掉了似的。我就想,怎么没有一个店开门呢,哪怕是花钱,让我进去暖和一下也好。那是阿姨最难的时候吗?我不敢问。因为,那个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和以前任何一个冬天都是一样的,无论走到哪里,我体会到的总是温暖。倒是行走在街上的寒冷成了一种情趣,再加上几片雪花,几阵北风,头发被吹着,极是快乐自在。
虽然我一口水也没喝,阿姨还是拿起暖壶给我的水杯续了点水,只有几滴,我仿佛听到了叮咚的声音。这时,我的心情已经稳住了,我问,阿姨跟我说这些是要告诉我,我离开他,我会生活得有多难吗?阿姨没说话,只是看着我,我又说,现在,我和他在一起,每一天都过得度日如年。今天他出差不在家,我想着回家了不会再看到他,心里才觉得舒服些。
阿姨仿佛还沉浸在她的回忆里,她放下壶,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有一次我问妮妮,如果妈妈死了,妮妮怎么办。妮妮当时不明白什么是生什么死,她说,我去投奔姥姥。我问她,你怎么不去找你爸爸。她把头埋在被子里,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以为她哭了,等她抬起头,我看到的是她澄澈明亮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本来没有忧伤,是我们错了,才把忧伤带到她的眼睛里。我一直希望她能快乐地成长,她也好像总是很快乐地成长着。我不知道那是她做给我看的,还是她真的非常快乐。这辈子,我只希望她能幸福,如果能用我的痛苦抵消她的坎坷,我愿意再苦百倍。
然后电话响了,是阿姨的老姐妹打给她的,叫她去跳舞。阿姨说,今天我就不去了,我下午得把我的窝整理出来。哪怕是一个人,只要心情好,什么样的窝都可以是温暖的吧。阿姨太坚强了,坚强得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阿姨是个冷漠的人,今天听了她这些话,我终于知道,无论多少坚强的人,只要她是一个母亲,她心底就一定有最为柔软的地方。
因为是一个人,她必须坚强给别人看。而我,也要做到这点,是不是?
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没说话,天空仍然明亮如初,像是再过很久,都不会等到暮色似的。阿姨终于起身,从箱子里翻出一个特别旧的小本子递给我,说,妮妮八九岁时的日记。我接过来,只翻了第一页,就泣不成声看不下去了。
第一页只有一个日期和一句话:好几天没看到爸爸了,我好想爸爸。字迹稚嫩,却还在本子的空白处画了一张难过的脸。我心里压抑着一团一团的愁苦,我把本子合住,放在茶几上,我说,对不起,阿姨,我实在没有勇气看下去。阿姨却说,我们刚分开的时候,妮妮一直惦记着家里的一个布娃娃,总是问,总是问。有一天,我就给她爸爸打电话,叫他爸爸托人把那个布娃娃拿了过来。妮妮看到娃娃,没有欣喜的表情,她愤怒地把娃娃扔到地上,哭着喊,谁让你去拿的。布娃娃在,爸爸就知道我们还会回家,你把布娃娃拿来了,爸爸会以为我们再不回去了。
阿姨说,你们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孩子的路才刚刚开始,能不离婚还是不要离了。我说,阿姨,哪怕你也是经历了背叛和伤害的人,还是会选择原谅吗?这么问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深深的绝望。我就要为了这样的原因,一辈子和一个不相爱的人,痛苦地生活下去吗?
阿姨没有回答我,她好像在认真思索着答案,又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我的手机响了,放到眼前,看到启贤的名字,我本能地站起来,向外面走去。是不是很蹊跷呢?阿姨没有注意我,见我走开了,她就去书桌那儿,一样一样地整理她的东西。
接通电话,我“喂”了一声。他问,在家呢?好安静。我说,我在妮妮她妈妈家。他反问了一个,妮妮?竟然一下没反应过来这个妮妮是谁。我补充了一个人的名字——“王妮”。他才恍然大悟地“哦”了声。说,我记得你提起过,你和王妮以前是邻居。我说,对啊,可惜她是女的,她如果是男的,我们就是标标准准的青梅竹马。启贤开心地笑了起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是忘不了异想天开。我心里想,我异想天开是因为,我想有一个懂我的人来怜惜我。可是,这种可笑的话,只适合想一想。是啊,想一想,就当是做了一个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