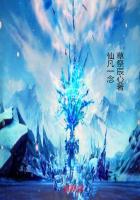出了林子之后,这片地带就空旷了起来,这里暂时是安全的了。不必急着赶路,死里逃生的喜悦过后,便是浓浓的沮丧了。一天辛苦,用命来搏,不就是为了一口吃食,到头来,不但空手而回,还损失惨重,即便剩下的这些人也有不少带着伤,勉力坚持着。
距离村子越来越近,众人越显得沉默,田叔一个铮铮的铁汉子这会儿像只无助的羔羊,一会儿看看村子的那远远可见的木墙,一会儿瞅瞅沮丧的众人,不停地叹气,两只拳头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半个时辰的功夫双眼已可见赤红的血丝了。
太阳西斜,赤红的云朵在四周不断地徘徊,恋栈不去,风儿不断地拉扯,它们痛苦的扭曲着,变化着各种形状,然而再是努力,终是抵抗不住大自然的伟力,太阳还是缓慢而又坚定不移的向着天边落了下去。空旷的天空,唯有云儿还不放弃,还在努力的追逐,赤红如血,但终还是要被黑暗慢慢的吞噬,不知云儿可知,只要等待一夜,太阳就会重新从东边升起?
“唉,这就是生活。”陆安生注视着天边那只剩下一半的夕阳和被夕阳照射的赤红如血的云朵:“我本没什么大志,只想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而已。天不遂人愿,患癌而死,却又遇着穿越这档子事,本以为终将可以衣食无忧混吃等死了,却又落魄到了这种地步,母亲病重无药可医,生活困苦忍饥挨饿,年小体弱空度流年。”
拖着细长的身影,陆安生握紧了拳头:“我不甘心如此沉沦啊!我不甘心啊!”
太阳西斜,狩猎的队伍还未归来,村里人早已等得焦急了。木墙上一直都有人在不停向着深林张望,但是林子里昏暗的光线和密密麻麻的枝叶让他只是做着无用功而已。
当狩猎的队伍刚刚出现在视线之内的时候就被警戒的人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睁大双目打量着,没有欢声雀跃和如山的猎物的队伍让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过他还是尽职的吹响了哨声:“他们回来了!”
在木墙后面,早已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等待了,他们很多都是外出狩猎的人的家人,等待着孩子回家,等待着晚点儿能够分块兽肉填补一下饥饿的肠胃······
当队伍来到大门下,大门早已打开。门后的人们用吃惊目光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巡视着,吃惊于居然一头野兽的尸体都没有,也是在确定自家的孩子有没有活着归来。
不用解释,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相较于以往那时候的赤手而归损失惨重,这一次可算是相当不错了,至少没怎么死人,重伤都没有。
大家一个个的离开队伍,来到自己的亲人身旁,人群便一拨一拨的离开了。待得人都离开完了,还是有五家人没有等到自己的孩子,一时间压抑的闷吭、痛苦的嚎哭以及杂乱的安慰声此起彼伏,天已经黑了,该回家了,夜晚即便是在村子里也最好不要待在外面。
陆安生没有等到人群走完,当开始有人离开的时候,他就背着自己的篓子左边插着把小巧的铲子右边插着把破旧的斧子从边上离开了,他身形矮小,大家又都在混乱中,是以都没有人发现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当田叔想起来要叮嘱他几句关于那只猛兽的事情的时候,他早已不见了踪影。
院子的大门早已敞开着,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依靠在门上,大大的眼睛里此刻只有远处那个背着个篓子插着铲子和斧子的少年,落日的余晖映射着少年微笑间露出的一口白牙,陆春觉得,为了这一刻受再多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到得近前:“母亲,我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好好好,快进来快进来,回家回家!”陆春手忙脚乱替陆春拍打着身上的草叶,弄得一手绿色的草木汁液。
“母亲,我自己来吧。”陆安生扶着母亲过了门槛,转身关上大门,复又扶着母亲的胳膊向着院子中的小凳走去:“您先歇着些。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只是跟着采摘些药草,又不去狩猎,危险的事儿我是一点都没沾上,大家伙也都多有照顾我,再说了您的儿子精着呢,您什么时候见过我吃过亏过?”
“就你能耐!”自家的儿子什么秉性做母亲的最了解,单论自保的手段,全村子没一个能比得过自家儿子的,这让陆春很是自豪:“你也饿了吧,晚饭我已经做好了就放在锅里面温着呢,你快去洗洗手端了来快些吃了,别没得给饿坏了。”
用袖子擦了擦凳子,先扶着母亲坐下:“得嘞,我这就去。待会儿我再跟您说说林子里的事,先吃饭,本还不觉得饿,您一提起来,我这就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快些去,快些去!”
陆安生把身上的篓子、铲子、斧头一股脑的往墙根上一丢,径直往厨房跑了过去。不是说假话,他是真的饿啊。
先是洗净了手,掀开锅盖瞧了瞧,四个馒头一小盘腌制的野菜还有一锅野菜汤,绿绿的汤水里游荡着几根被煮的已经烂糟糟的的野菜。又打开旁边的木厨,点了点里面的吃食,叹了口气,为了省下饭食,母亲中午又没有吃饭。
陆安生瞧瞧自己的小身板,十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段日子自己的饭量是越来越大了,看着厨子里面不多的食物:“哎,得想办法弄些吃的了。后面田地里的庄稼还得过俩月才能收割。”
收起乱糟糟的心思,端了饭食出来和母亲在院子里面吃了晚饭,期间把这次狩猎的经过简略说了下,太过危险的自然略过不提。说到那五个失踪的人的时候,陆春唏嘘不已,但也没什么别的,每次狩猎,生死常事尔!至于这次空手而归,也只是说是田叔觉得那只猛兽不能力敌只得放弃猎物自保了,所幸那只猛兽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放了大家伙儿一次。
吃了晚饭,又给母亲熬了草药,服侍母亲喝了睡下,陆安生脱了衣服痛快的洗了个澡,爬上床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这个时候,还有不少人家都没睡下,偶尔有人声传出来,在幽深的夜晚传出去很远,中间间或还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哭泣声,听不真切,混合在一阵阵的兽吼虫鸣之中,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陆安生做了个奇怪的梦。
他还在地球上。那时候他已经患癌了,回到了老家。
中午的太阳很是温暖,陆安生便搬了张床在房前阳光下躺着晒晒太阳,很是舒坦,各种各样的鸟儿不断地在陆安生上方的树枝上啼叫,啾啾的极是悦耳。
往往返返的人们从远处走过,扛着务农的工具,大声的欢笑。
“喵呜···喵呜······”忽然一阵猫叫在近前响起,陆安生睁开双眼,是家里养的一只小花猫,只有巴掌大,牙才刚刚长齐了,甚是可爱,就那么站在床下面看着陆安生,大眼睛眨啊眨的,喵呜喵呜的叫唤,直萌到陆安生心底里去了,萌死了。
陆安生起身下了床,蹲在小猫前,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小猫的脑袋,绕了个圈转到了小猫的脖子下,一下一下的给小猫挠痒痒,小猫对着陆安生眯着眼睛“喵”了一声,就闭上了双眼伸长了脖子,极是享受小尾巴在后面摆啊摆的。
只是忽然间,小猫却一口咬在陆安生的手掌上,陆安生除了轻微的挤压的一点点疼痛感,却没有其他的不适。低头一看,却发现小猫的两边嘴角两根森寒的獠牙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来,刺破了一点手掌,有针扎的感觉,小猫的双眼这会儿却只是“饶有兴趣”的盯着他看,有一种猫戏耗子的感觉。这种不合乎常理的现象还是让陆安生一阵心惊胆战,想抽回手掌,却惊恐的发现,全身僵硬,使不出一丝一毫的力气。
陆安生只能不停地挣扎,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挣脱,小猫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但是陆安生还是在保持着那个姿势动弹不得。
终于,也许是他的力气足够大了,他挣脱了。
“嘶啦······”黑暗的房间里一串撕裂声响起,陆安生猛地睁开双眼,他还好好的躺在自己的床上。陆安生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心脏还在砰砰的直跳,松开手,摸索了几下,皱了皱眉头,被子被他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明天得缝补下。
摸索着找着衣服穿上,就着月光,陆安生开了门,轻手轻脚的来到院子里,打了些井水洗了洗自己满脸的大汗。
被冰冷的井水一激,陆安生也冷静了下来。抬头看着月亮想了想,梦里最后小花猫的样子和白天的那只狡猾的猛兽如出一辙,叹口气拍了拍脸颊,自己这是被吓到了吗?
不过话说,为什么那只猛兽会有那么人性化的眼神?
难不成它有着不下于人的智慧不成?
它是看出来我的与众不同了?
“唉,这里还是太偏僻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深山老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真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的?”目光重又落在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上:“月亮啊,你是我的那个月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