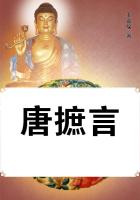赵国的老将,廉颇,长满老年斑的脸上挂着盈盈笑意。此时他正站在一座山丘的顶端,整个战场的情况尽收眼底。他从容的对着身后十几个发令官发号着司令,一面增兵围剿,一面忙着安排伏击前来增援的卞家军。
“哼!没有了卞喜,卞家军就成了一块没有生命的鲜肉,看我怎么将你们慢慢的蚕食掉。”
须臾之后,廉颇意识到了战场的变化。那被围的水泄不通的卞家军,有几道白色的痕迹冲天而起,瞬时上空响起了霹雳,然后从内部分出一股溪流,这溪流虽小,但所到之处可谓所向披靡,于是厚重的包围圈,愣是被破坏出一个口子来。
“咦!什么情况?”廉颇感到不可思议。
“这不可能!”廉颇一字一顿。
这时,一个慌张的探子跑到廉颇的面前,跪拜下来之后,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汇报战情。
“廉颇将军,西南方向出现了一股部队,,估计有万人之众,正朝着翠屏山的方向赶来,他们打着晋国第三十三军的旗帜!”
廉颇听到三十三军,竟然颤抖了一下,老态的脸上生出顾虑。
“这怎么可能?再探!”
探子得令,急匆匆的下去了。
“将三千第一护卫军投入战斗。”廉颇迅速下达命令,动用了手中的王牌。
“通知楚军,强敌出现,速来增援,如果少于十万人的话,就让他们去****吧!”
一个传令官被吓得缩了一下脖子,然后迅速拿出纸条,在上面一阵涂写,片刻之后,他将纸条捆绑在了一只信鸽的腿部,对着西南方向放了出去。
廉颇好似还不放心,脸上挂满了焦急。他迅速的转过身,迈开大步走下山丘,到了一匹橙红色的战马身边,一个轻快的翻身,骑到了马上,然后接过身边一个士兵抗着的大刀。
“尔等随我同去,势必要活捉重耳!”廉颇说罢,一骑绝尘而去,其后在旁蓄势的三千精骑,紧紧跟随在廉颇身后,于是人仰马嘶,旌旗招展,荡起灰尘漫天。
先轸的人数不多,只有五十来号,却是个个骁勇善战,他们均久经沙场,远比生活在太平年代的卞家军要强上数倍,所以说,军魂是需要战争来洗礼的,当然,若不是短兵交接,他们也讨不来好处。
重耳作为晋国的公子,他生在晋国衰落之时,成长于晋国灭国之际,自幼修的文武双全,对战争早已侵湮许久,在这数万人的战场上,他带领着勇猛的部下,就像是一只无坚不破的利器,在人肉中搅拌着,一颗敌人的眼珠带着血水黏到他的嘴边,此时他正杀到兴起处,只见舌头一伸,一卷,那眼珠就进入了他的口中,随即咀嚼、咽下。
赵军哪里见得这样的场景,握着武器的手开始发抖,甚至还有几个扔下武器抱头鼠窜,引发重耳阵阵狂笑,重耳的狂笑响彻战场,足见他的武功修为高深莫测,而且他的笑声也成为了战场上鼓舞士兵的擂鼓,甚至还感染了卞家军。于是以重耳为头,晋国三十三军做翼,卞家军护尾,一个凌厉的冲击阵营默契的形成了。
一炷香之后,重耳竟然冲出了重围,将被吓破胆的赵兵甩在身后。在先轸的提示下,他们奔着西南的方向杀去,卞家军则分成了两股,一股在一位副官的带领下,一路向东,一股则继续尾随重耳。
重耳回头望了一眼身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是他的勇猛给他平添了上千名的卞家军粉丝,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看来是不假的。然而,正待重耳即将奔赴曙光的时候,铺天盖地的马蹄声响起,一股磅礴的烟尘正由远及近,赶赴而来。
“那是骑兵!是赵国的骑兵,好个胡服骑射。”
先轸用袖子擦拭了一脸血水,视力超人的他率先看到了滚滚烟尘中的旗帜。
“是廉颇!”转而先轸对着重耳说道。
“公子!一会儿先轸为您夺下一匹骏马,你就骑着它一路奔赴西南方向,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重耳是一个果断的人,未作细想,就点头同意。重耳认为,他的性命凌驾于他人之上,为晋国而亡的将士已经不下数十万了,如果他们真的为国捐躯了,那将是他们的荣幸。
片刻之后,骑兵临近,一波剑雨先行问候,三十三军的将士站在重耳的身前,舞起一团团刀剑的花朵,但仍有十几人被射穿。先轸大喝一声,挺身跃起,直奔一匹高头大马而去,其余的数十人则是奔着主将廉颇的方向,廉颇的位置很好辨认,只要识得那杆绣着“廉”字的大旗便是。
骑兵势如破竹,其余的卞家军哪里见得这样的阵势,瞬时就被骑兵队伍冲的七零八落。廉颇早已看见重耳,但苦于应付身边围上来的数十个高手,一面大下杀手,一面维护着自己及身下的爱马,大刀抡起,每一个起落均会带走一条性命,但那些三十三军的勇士们就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哪怕是注定死亡,也毫不退缩。
先轸凌空将一个骑兵踢下马来,自己坐了上去,他挥舞着青铜剑一路砍杀,向着重耳的方向杀来,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剑已经折断,虎口处溅出漫天血雨。他身体一个踉跄,身体大部分已经脱离马背,险些跌下马来,好在他的缰绳抓的很紧,身体的平衡也把握的恰到好处,然而正待他正位之时,余光可见一柄巨大的虎头刀迎面劈来,气势如山。
保人还是保马!先轸迅速做出抉择,他身体微微倾斜,那柄虎头刀在他的眼前落下,甚至斩下了一缕他额头凌乱的刘海,几根发丝在空中飞舞着,如同生命一样卑微。
虎头刀来势太猛,这一刀正砍中马背,先轸的坐骑瞬间就被劈成两半,血水将他浑身染透。先轸借机瞧出了使虎头刀人的破绽,他伸手抓住刀柄,起身一个飞踹,那名骑兵中了先轸狠狠的一脚,握刀的手再也把持不住,身体腾空而起,落下之时正好撞倒另一个骑兵的怀中,随即他们一同倒地,骑兵的青铜剑却是将他的身体贯穿,他看着身边讶然的战友,不甘的闭上了眼睛。
先轸以刀柄触地,一个翻身跃上战马,紧接着一个大刀轮圆,几名身边的骑兵被斩下马来,他未作片刻喘息,用尽全身力气不断的挥舞着大刀。
此时重耳的发髻已经散开,他的头顶被一名骑兵削去了一块,露出了阴森的头骨,但转而就被鲜血覆盖,那鲜血正顺着脸庞和发丝落下,使人看来惊悚万分。当然赵国的骑兵也好不到哪里去,此时重耳的身边已是死马狼藉,尸体层叠。
先轸斩飞了一个骑兵的头颅,终于靠近了重耳,重耳提着血淋淋的青铜剑,正对着他癫笑。重耳癫笑未殇,就一剑直刺先轸,先轸迅速牵马躲过,但仍被那一剑划破了大腿,血液涓涓的流了出来。先轸顾不得疼痛,瞧准时机,伸手抓住重耳持剑的手腕,然后发力,将他拉到了马背上。先轸在后面紧紧的抱住重耳,遏制住他已经癫狂状态的身体。
“公子,我是先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