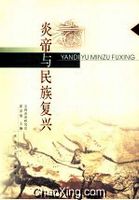约旦河西岸,安息故土,新汉与拂林帝国边界,夏夜。
天穹中,一弯弦月,繁星如簇。一千年前,古巴比伦的占星师们就是在这里,一颗一颗地绘制出黄道十二宫诸星座图。
那些精通命数、勘破历史轮回的星官们,穷尽一生也想不到,有一天,来自天山以东的华夏族人,会挥师西进,重夺三千年前失落的故土,并在这里复兴了汉家帝国。
天穹下,离河岸二三里远,沿着旧河道,绵绵延延四五里地,散布着大汉骠骑军的营帐。营帐外的火把交通串联,仿佛一条游弋的蟠龙,将当年女娲补天后留下的龙脉死死地钳住。这条龙脉自叙利亚经伊拉克,穿伊朗再入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王朝盛衰之命门,几百年间,数十度易手。现在汉军扎营在此,就是要向西与罗马人决战,夺下龙首处的条支城,霸占整条龙脉。
而在这条蟠龙的咽喉处,还有一顶营帐未眠,分外醒目。帐中几案前,昏黄的铜灯奴下,一人二十四五岁年纪,羽扇纶巾,正襟危坐,正对着舆图向两名少年面授机宜。只见他冠发庄严,仿佛武侯诸葛孔明转世,浩浩然有鸿儒之气。但若有善相面术者,只需一眼,便能看出,那清眉俊目之下,藏着一双杀气凌人的瞳仁。此双眸者,虽平日含情脉脉,好似柔弱,但一遇大事,杀伐决断,不会有半分犹疑。有此面相者,若非巨侠大盗、专诸要离之辈,就定是始皇那样的千古一帝了。
此人,便是一手缔造新汉帝国,时人尊称“天师”的汉家大司徒。
而身旁的两人,便是天师如左膀右臂的亲信,骠骑将军谢云官和轻车校尉李破奴。两名少年,都只有十六岁。
天师的身世,对这一世的人讳莫如深。人们只知道,天师姓洪,一百二十年前,他与皇甫嵩、李业长安结义,于初平元年领兵救走废帝刘辩,辗转西域,经过近百年的征伐搏杀,灭葱岭以西三十六国,终于于安息帝国故地奠基立足。而最为传奇的是,天师的容貌,百年未变,且有两大法宝:一把神弩,可以于百丈之外轻取人首级;一身铁骨,可以腾跃百尺,高墙深壑如入无人之境。
每当朝堂之上,有人称颂他的神功伟业,或是有人暗弹他是妖蛊余孽时,他都不以为意,也从不辩解。毕竟,到一千七百年前的这一世来,有些事情说多了,会干扰历史的进程。历史进程若是改变太大,天师作为穿越者所拥有的预言能力,也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要怎么跟三国魏晋之时的古人解释,自己本是职业杀手,那神弩铁骨,都是自己从现代带回来的军用装备这件事呢?
还是解释兵法来得轻松。
“云官,破奴,刚才为师所说的战阵布置,尔等可都清楚?”天师左手执袖,右手一指战舆图上的一处。
“徒儿都清楚啦!”说话的是李破奴。他身着金银绣片两当甲,古铜色的脸上挂着一幅满不在意的笑容。
“从为师学兵法以来,你哪一次认真过!”天师嗔怪道,“云官,你来说说。”
“诺。”只见一眉目清秀、肤若凝脂的美少年收起舆图,用食指蘸了錾银莲花狮子壶中的酒,便在几案上画了一条长线。“刚才审了那拂林细作,得知河对岸有敌师十万人,敌帅乃拂林皇帝君士坦丁。其中,披甲重卒三万,圆盾轻兵四万,北蛮骑兵一万,还有条支弓箭手五千。剩下的人,多是随军奴隶,没什么战斗力。“
天师点点头,让他继续。
云官又将食指去蘸酒,然后在长线一侧画了一个圆圈。
李破奴问道:“这是什么?”
云官淡淡答道:“这是“战眼”。方才天师讲阵时,你又不听。”
“云官他又瞧不起我!”李破奴觉得受了耻笑,忿忿不平,要找天师评理。
云官不搭理李破奴,伸手又去蘸酒,然后在圆圈下方画了一个方形。“约旦河对岸,方形处,就是拂林军的大营。那大营北部,就是画圈处,是一座小山。这座小山,便是战眼,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天师率南军精甲卒三千,绕到渡口以南的崖壁后埋伏;而我自领北军去夺那山头,以步军三万、弓弩手七千、轻骑一万、重骑一万吸引拂林主力。”
说完,云官又在长线另一侧画了一个圆圈,并对李破奴说道:“你的任务,便是领三百亲卫死守此地,不到战死最后一人,不得后退一步。”
“现在明白了吗?”天师看了一眼李破奴,又看了一眼谢云官,“若是清楚了,便速速去休息,明日一鼓作气,全歼拂林大军。”
“明、明白了,我这就去。”李破奴脸色赧红,捧起几案上的玄铁兜鍪,道声告辞,便出帐去了。帐中,便只剩下天师和云官二人。
“云官,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吗?”天师见云官没有离开的意思。
“天师,云官有一事不解。”云官回道。
“有什么事便说,不必多礼。”天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看这战局中,破奴儿所在之地,十分凶险,只怕是死穴。天师为何独派他去守那里?”云官也不客气,张口便问道,气势咄咄逼人。
“不错,此处确是死穴,然则死穴也是生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天师伸出一指,按住了几案上用酒画成的圆圈处,“只要在此处以饵兵缠住敌重骑兵,南、北两线皆可无忧。这个也叫,置之死地而后生。破奴儿天生勇力,只有他可担此大任。”说罢,天师收回手指。那按过的地方,竟然陷下去了一个浅浅的坑。
“就算如此,为何只给三百亲兵?只要战局稍有变异,那就是亲手害死破奴儿!”云官不依不饶。
“主力尽拨调向北路,三千精甲卒要打穿南部的通道,手中实在再无余兵了。”天师并不正面回答。
“皇甫将军的十万波斯枪骑还有三天就到了,等等就有余兵了,为何要急在明日进攻?”只见白衣少年伸出一双藕节纤手,将战舆图又铺开来,提袖探指,按住图上的一处红点,“如今汉军兵力见劣,还要渡河而击,这是兵家大忌,天师不可能不知。徒儿不解,恐此中别有隐情,斗胆相问。”
云官啊云官,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此时真不知是该害怕还是高兴。
“我在世已一百二十年,虽然容颜未老,但也自知时日无多了。条支城中有我必取之物,等不及皇甫将军了。”
这必取之物,其实才是天师穿越回来的真正原因。不过那物为何,他从未与任何人提及过。
“天师,这必取之物,可否让徒儿知道?”
“事涉机密,还是不要为好。”天师言辞闪烁。
云官叹了一口气。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问了,然而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我入军中虽只有六载,但也听老军讲过不少事情。他们说,当年下楼兰、于阗时,您就曾派兵四处搜寻西王母遗物。兵围泰西封时,您也是为了城中一块名叫“洪水泥版”的东西,下令孤军冒进,害得先将军李继遇伏战死。
“还有人说,在征疏勒时,有方士惑众,说当年共工撞倒的不周山崩塌成了安息国,西泄的天水成了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二河。您听了这传说,便认定安息就是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之地,遂说服先帝发兵讨之。
“更有人说,您恐怕不是世间之人,来此只是为了取走镇天的灵髓,拿去修炼万年的道行。
“徒儿知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但有一点众老军说得对,值得如此劳师动众搜寻之物,恐怕不会是凡品。天师,若您真如当日所说,视我如己出,为何不能将此事与云官一言?”
云官说得很激动,一只手竟紧紧地扣着几案边沿。一双明眸,直直地剜着几案另一侧的天师。
“云官儿,不是为师有意要瞒你。”天师将头悄悄地扭向一侧,“只是此事关系重大,并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你只需知道,为师要寻的,是一件能颠覆这上下五千年所有善恶黑白的东西,也是唯一能澄清为师身世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到。”
话音刚落,帐中便是一片阒静。
帐外,只有一片风展旌旗倏倏的声音。
“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云官说吗?”云官眼中泛起了泪光。
“云官,不要逼迫为师。”天师的声音变得冷漠生硬起来。
“不惜牺牲无辜的人也要取得那东西吗?”一滴晶莹的眼泪终于在眼角挂不住,沿着云官浅浅的法令纹,滑落到了唇边。
“牺牲千百人,是为了救亿万人。为师心意已决,你不要再说了,快回去休息吧,还有两个时辰就天亮了。”
云官知道无论如何都问不出来什么,也劝说不了天师什么了。他起身作了一揖。
“天师,云官还有最后一句话,望您听进心里去。以弱逆强,最忌一个字“赌”。不管天师所求之物意义如何重大,需如何不惜代价,也再莫犯当年同样的错误了。李继将军将破奴儿托付与您,不是为了他有朝一日,也在战场上为了那“必取之物”,捐身枉死的。今日徒儿多有冒犯,在此赔不是了。”
一语落罢,云官白衣一引,旋身便去。
天师看着云帆的背影,想着他最后的那句话,只觉得心口一阵绞痛。
“云官,为师对你与破奴儿的苦心,一时难说清楚。可惜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机会了。”
一口黑血,溅在几案上那用酒画作的战舆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