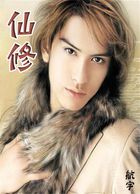华原大地。
大越王朝。
大越王朝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甚是富庶。在鼎盛时期,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均达到很高成就,乃是迄今统治华原大地历代王朝中最为强盛者,故周邻诸国无不臣服。大越王朝将华原大地划分为十州,而十州以下共设置三百六十五座府,府下共设置一千五百七十三座县。
大越王朝乃是推翻大吴王朝而建,至今已立近三百年之久,但在一百多年前,曾发生一次席卷大部分地区的叛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却使王朝从此由盛转衰,逐渐走向没落。特别最近十年,君王越发昏庸无道,好大喜功,重用奸佞,贬谪忠臣,贪图享乐,荒淫无度,以致朝政日益荒废,民怨沸腾,贼寇横行。
岭州。
岭州乃是大越王朝最西南的一个州,境内崇山峻岭,数不胜数。山高水秀,层峦叠嶂,植被茂密,气象万千,真可谓是无山不绿、无峰不秀、无石不奇、无水不飞泉。有道是:深山大泽,多生龙蛇。幽谷深林,多居虎狼。故而,众山之中多有野兽横行,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数量浩大,多如牛毛。除此之外,在众山之中,多有瘴气与毒泉,不明真相之人若是误入瘴气之中或误饮毒泉,均会有性命之忧。缘由于此,岭州皆被认为乃是蛮荒凶险之地,不宜居住。除一些土著外,多数为王朝的流放犯人。
盛夏。
此日。
碧空如洗,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无有微风。天地间万物犹如存在于巨大蒸笼之中,树木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伫立原地,而树荫之外的花草垂头丧气,如奄奄待毙一般。没有鸟影,没有兽行,仅有鸣蝉,嘈杂阵阵,不厌其烦。
岭州东北乃是剑南州,从其进入岭州境内三百余里有一座郁郁葱葱且人迹罕至的无名小山,在其起伏不平的山路之上,慢慢地行来三匹马与一辆吱嘎响不停的马车。
走在最前方者乃是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马鞍之上端坐一位虬髯大汉,年纪大约三十余岁,身长六尺挂零。黝黑脸膛,浓眉大眼,眼窝深陷,双眼深邃而有神,蒜头鼻子,四字方口,两腮微塌。头戴青色结式幞头,身穿交领右衽开胯青袍和青色长裤,腰束青色革带,脚登青色长靿靴,单从身形尚可看出,其本应十分魁梧,但此刻略显清瘦,时而还会咳嗽几声,仿佛大病初愈。大汉左手握住缰绳,右手倒提一条镔铁盘龙棍。在其身后有两匹马并排而行,右侧之马乃是通体青色,掺有少许白色杂毛,而左侧之马则是通体黄色,额中生有白章。
骑乘青马者是一位老者,年纪大约有六十余岁。细长脸颊略显消瘦,八字眉,深窝眼,矮鼻梁,塌腮,颌下一缕花白胡须。头戴青色粗布平式幞头,身穿青色交领右衽粗布袍和粗布长裤,腰束布带,脚登麻布履。左手握着缰绳,而右手则抱着一个被薄被子包裹且正熟睡的婴儿。其腰间插有一杆二尺左右的铜制烟袋,烟袋锅有茶杯口大小,在烟杆上系有一个精致绣花烟荷包,其中装有一些旱烟丝及火镰。
骑乘黄马者是一位年纪四十余岁,身着衙役服饰的大汉,双手握着缰绳,腰间悬挂一把钢刀。
走在最后的是一名车夫赶着的一辆破马车,车上仅载有一口陈旧大木箱。
虬髯大汉姓韩,名悦峰,原是剑南州人氏,家住州府九江城,曾在府衙谋事,任录事参军一职。至其这代,韩家已然是四世单传。其父名叫韩世昌,武功了得,早年开得一家镖局,积攒些许家资,故而家境比较殷实。其母早年不能生育,但由于夫妻恩爱有加,故其父一直未曾纳妾。韩世昌遍访名医,终将韩悦峰母亲的不育之症治愈。在韩世昌四十五岁之时,韩悦峰顺利诞生。可想而知,其父母是如何宠爱,如何将其视为掌上明珠。
老者名叫韩春义,乃是韩家的老管家。韩悦峰尚未出生之时,他便追随在韩世昌左右,对韩家可谓是忠心耿耿。他原本姓谢,只因与韩世昌交情莫逆,加之又做了韩家管家,故而改为韩姓。
另一大汉名叫钱跃鹏,曾是韩悦峰部下,现乃剑南州州府之衙役。
韩悦峰天生神力,受其父影响,对武术极其酷爱。十岁时,便将其父之武功学完。韩世昌自然十分高兴,为了教子成名,便花重金聘请多位高人,传授韩悦峰武功。诸多兵器之中,韩悦峰尤其喜爱长棍,习得多种棍法,其中以六十四路八卦棍和七十二路驭虎棍最为擅长。缘由此点,韩世昌又花重金请一位居住在九江城多年但无人知其姓名的铸造老者,专门为其打造一条镔铁盘龙棍。此棍径有两寸五分,长约六尺有余,棍头乃是龙头,龙身盘绕于棍身之上,棍尾乃是龙尾,整条龙栩栩如生,似天然浑成一般,而棍身之上除有一些无人懂得的奇怪文字样符号外,还铸有“天下之兵,独此一棍”八个篆字。二十岁时,韩悦峰武功学成,身兼万夫莫当之勇。后二年,韩世昌与妻子因病而相继去逝。临终之前,韩世昌将韩悦峰托付给韩春义。韩悦峰料理好双亲后事,平复悲痛心情,依然继续习武。如此过了四年,韩悦峰武功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由于为人正直,行侠仗义,在剑南州及附近州府已小有名气,人送绰号“剑南棍侠”。
韩春义初始以为韩悦峰心情悲痛,便任由其行事,后见他整日习武,沉浸其中,便劝他不能如此闲赋在家,应该找份差事。韩悦峰觉得有理,便委托韩春义花重金捐得录事参军一职。只是,韩悦峰根本不懂为官之道,人情世故也知之甚少,并且为人正直,故对州府官员所做贪赃枉法之事,十分不满,常有微词,无意之中得罪不少人,但由于他武功极高,加上韩春义暗中打点刺史,得到刺史庇护,因此他才能够在八年之中安稳顺利地将官做下去。
一年之前,刺史因得罪上司而被革职。新上任的刺史名叫李奉春,为人贪婪诡诈,素有恶名,为了钱财往往不择手段,只因其善于阿谀奉承,又舍得花重金打点,故此非但未得到严惩,反而屡屡晋升。至剑南州上任之前,李奉春早已探听出剑南州内的商贾富户,并谋划如何能敲诈出大笔钱财。上任两个月后,李奉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但凡被其盯上之人,轻则流离失所,重则家破人亡。以韩悦峰之家资,本不在李奉春的敲诈之列,无奈韩悦峰对他的所作所为时常进行阻挠,甚至数次当面叱责,故而李奉春对韩悦峰恨之入骨,便捏造罪名将其打入监牢。
韩悦峰早年痴迷武功,直至二十八岁时方娶妻。入狱不久,其妻诞下一子,但得知他入狱消息,不久便抑郁成疾,最后怀抱幼子于深夜之中悄然而逝。韩春义料理完韩悦峰之妻后事,便尽全力解救韩悦峰。
李奉春倾吞韩家所有财产,又企图将韩悦峰判成死罪。幸而,韩春义遵照韩世昌临终之叮嘱,暗中埋藏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金银财物。他用这些钱财东奔西走,上下打点,费尽周章终于打通朝廷中主事官员,方使韩悦峰死罪得免,被判流刑,流放之地便是岭州。韩春义雇佣一辆破马车,装着所剩无几的家当,怀抱韩悦峰之子来到监牢。
韩悦峰在牢中受尽残酷刑罚,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虽经韩春义打点,狱卒将其伤治愈,但元气已然大伤,身体大不如前。后来,他又从狱卒处得知妻子死讯,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而崩溃,一直颓废不振。韩悦峰头发蓬松,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双目无神,胡须凌乱,身穿囚衣,颈上戴有二十斤重的大木枷,双脚如同陷入泥潭一般,拖着沉重脚镣艰难走出监牢。
韩春义见状,百感交集,眼泪在眼圈中不停地打转。他擦拭一下眼睛,行至韩悦峰近前,说道:“少爷,您受苦了!”
韩悦峰呆呆看着韩春义,片刻之后,说道:“原来是义叔。”
韩悦峰言罢,便低下头,一语皆无,心中满是悔恨,暗忖:“当初若听得义叔忠言,改改脾气秉性,何至于此?”
韩春义见此,不再多言,右手抱住婴儿,左手从腰间取下一个沉甸甸包袱,来至一个黑脸大汉近前。只见此黑脸大汉络腮胡须,肿眼泡,小眼睛,不时流露出一股股凶光,腰间悬挂一把钢刀,再一看穿着打扮便知他乃是衙役班头。黑脸大汉面沉似水,一言不发。
韩春义将包袱递给黑脸大汉,恭敬说道:“孙头!不成敬意,分给兄弟们,还请兄弟们在路上多多照应。”
孙班头接过包袱便知是银子,掂掂分量,立刻变换嘴脸,眉开眼笑,小眼睛瞇成一条缝,忖道:“足足有五十多两!老家伙,还算你懂事,不然的话,这一路上非叫韩悦峰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孙班头将包袱交给身旁一名衙役,吩咐道:“分给弟兄们!”而后对韩春义,笑道:“老人家,放心吧!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说得算了。一路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韩参军。”
韩春义点点头,而后又从怀中掏出一张五十两银票,塞给孙班头,说道:“孙头,这是孝敬您的,还请您笑纳才是。”
孙班头先是一愣,看看银票数目,忖道:“这老家伙可真下血本!看来老子又发一笔小财。”而后又故作不解之状,说道:“老人家,您这是……”
韩春义笑道:“孙头,小老儿还有一事相求,万望您能成全。”
孙班头说道:“老人家请讲。”
韩春义叹气道:“我家少爷摊上此等横事,而今又被判流刑。家中侍奴鬟婢早已各奔东西,只剩下小老儿与怀中幼子。所以小老儿恳请孙头将我们这一老一小也顺路带上。等到流放之地,我们就在附近乡镇择一地住下,等待少爷刑满释放。”
孙班头拉长声音,道:“这……”眼珠转了一转,接着笑道:“按规矩当然是不行。不过,规矩都是人定的!此事,我答应了。你们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韩春义深鞠一躬,说道:“小老儿多谢了!”
孙班头点点头,然后大喊一声:“走!”
韩悦峰被孙班头和包括钱跃鹏在内的十一名州府衙役押解,赶往岭州。韩春义怀抱着婴儿坐在破马车之上,跟在最后。一行人刚出九江城后,孙班头便命人将韩悦峰的木枷连同脚镣一并去掉,并牵来一匹黑马供他骑乘。
韩春义见此,暗忖:“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银子没有白花。”
一行人晓行夜宿,此日终于进入岭州境内。
孙班头立即命人将木枷与脚镣给韩悦峰重新戴上。韩悦峰一脸茫然,看看韩春义。韩春义亦不知何故,遂行至孙班头近前,问道:“孙头,您这是……”
孙班头解释道:“老人家!现今进入岭州境内,已经不归属剑南州管辖。如果被岭州官员看见囚犯不戴刑具,很有可能会上报朝廷,那么弟兄们甚至刺史大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惩处,所以只能如此,还请老人家不要见怪。”
此次,无论韩春义如何塞银子,如何央求,孙班头均是拒不接受。韩春义无奈,只得作罢。
在官道与一条小路的交叉口处,孙班头带领众人走下官道,沿着小路行至一座小山,并解释说,此乃是一条近路,可以早日到达流放地点。韩春义无法阻拦,只能跟随。众人来至小山山麓的一座破寺庙前,孙班头与其余衙役略一商量,决定在庙中休息片刻,再行赶路。商量之时,钱跃鹏似与孙班头稍起争执,但极快便平息。
众人向寺庙行走时,韩春义趁机至韩悦峰身边,低声说道:“少爷,提高警惕,小心提防。自进入岭州以后,事情似乎有些蹊跷。此时又要在破庙中歇息,多半有什么阴谋。如果发生意外,切记往马车跑,在车板下面,藏着少爷那条镔铁盘龙棍。”
经过韩春义一路劝导,韩悦峰精神状态已然大有好转,闻得此言,点点头,眼中一丝寒光闪现而过,暗忖:“义叔所言不虚!还真得留点神,不然定要吃亏。”
寺庙很小,院墙残破不堪,庙门业已丢失。院内仅有一间大殿与两间厢房,屋顶均无有片瓦遮盖,门窗亦不复存在,并且在大殿后面还有一座倒塌佛塔。大殿之中只供奉着一尊落满灰尘以及结了无数蜘蛛网的佛像,而且镀在佛像之上的金漆已然脱落,生出厚厚铜锈,而供桌之上空无一物。众人走进大殿之中,而孙班头走在最后。
孙班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蓦然喊道:“动手!”
韩悦峰暗叫:“不好!”遂大喊道:“义叔,小心!”
便在此时,孙班头与十一名衙役几乎同时拔刀在手,将韩悦峰与韩春义围在中间。二话不说,孙班头与钱跃鹏以及八名衙役举刀砍向韩悦峰,而另外两名衙役则举刀砍向韩春义。如此攻击,显然是早有预谋。至于那个车夫哪里见过如此阵仗,已经吓得瘫坐于地,慢慢地蹭到供桌之下躲藏起来。
两把刀砍向韩悦峰双腿,其余八把刀砍向他的脑袋。当刀快到未到之时,韩悦峰双腿并拢向上一跳。此一跳真是恰到好处,不但使双腿得以避过,而且使木枷正好挡住砍向头顶之刀。咯吱吱几声微响之后,木枷表面裂开许多条细纹。韩悦峰双臂一用力,咔嚓一声,将木枷掰得粉碎,并且在落地之时,双脚正好踩住砍向双腿的两把刀。
韩悦峰大喊道:“义叔!跟我冲出去!”
韩悦峰两拳打倒两名衙役,撕开一口,噌地一下蹦至门外,便向马车跳去。
韩春义左手抱着婴儿,右手拔出旱烟袋,与两名衙役缠斗在一起。他的武功虽远不及韩悦峰,但是毕竟跟随韩世昌走镖多年,武功也一直未曾荒废,原本对付两名衙役绰绰有余。只是此时怀抱婴儿,怕其有所闪失而无法使出全力,方与两名衙役斗得秋色平分。闻听韩悦峰所喊,韩春义身子刚一向大殿外移去,立刻被两名衙役拦住,根本来不及跟随韩悦峰冲出去。
孙班头暗忖:“如果不解决此二人,我们回去可是没什么好果子吃。”遂吩咐道,“钱跃鹏,你留在大殿和他们一起宰了老儿,然后再出来帮忙。其他人跟老子一起追,必须拿下韩悦峰的狗头,要不然咱们都没什么好果子吃。”
孙班头言罢,率先冲出大殿,紧随其后又冲出八名衙役。
韩悦峰跳至马车旁,探右手至车板下,便摸到一根棍子,用力一抽,正乃是镔铁盘龙棍。他以棍拄地,低头不住地喘着粗气,翻着眼睛向庙内看去,眼中尽是疲惫之色。与此同时,孙班头与八名衙役已冲至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