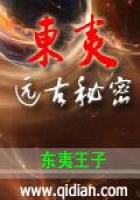东方朔听得院里别无动静,回首目视卫青。卫青恢复常色,道:“先生看我做什么?”他反倒上前叩门,叫道:“二姐,我回来了。”顷刻之后,木板门往两旁敞开,来人却是卫子夫。卫青见了她,自不惊奇,语气颇显生硬地道:“姐姐。”
卫子夫面上的笑容戛然而止,眼底溢出淡淡的忧伤。东方朔上前拱手道:“卫姑娘,鄙人又来打搅啦。”卫子夫强颜笑道:“先生哪里的话,先生请进。”忽而瞥见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老者,观其容貌装束,颇似在侯府里见过的一位老先生,惊奇道:“你,你是……?”
董仲舒凝视芳容,说道:“老夫认得你,你是平阳公主身边的侍女。”卫子夫衽身拜道:“卫子夫见过先生,失礼之处,万望莫怪。”东方朔先行说道:“无妨无妨。卫姑娘,可否领我二人瞧瞧去病?”卫子夫讶道:“去病?”惊容霎息即过,道:“他,他就在屋里。”言讫,领路在前,掀帘进里屋。
这时卫少儿不在屋里,小去病躺在榻上睡眠正香。东方朔看孩子脸色粉嫩,却比昨日消瘦些许,常人一眼是瞧不出来的。东方朔更添愁怜,向卫子夫道:“这孩子似乎染有小疾。”
卫子夫惊道:“先生莫要吓我。”东方朔安抚她道:“姑娘不必急。这位老先生是京城里有名的医师,他此来便是给孩子看诊。”
卫子夫虽不知董仲舒之名,但思他在侯府里被奉为上宾,必然不是常人。他们家中钱财无多,极少请医看病,更何遑是有名的医师。一听东方朔如此言语,心里稍稍宽心,道:“多谢先生。”
东方朔道:“你和小兄弟先出去等候。”卫子夫应下,与卫青退出屋外。董仲舒不言不语,径自走到榻前,观摩婴孩的面色。
卫青出了里屋,仍旧如锯嘴的葫芦。若在平日,他回到家里之后,仿若话无不尽。此时反差这般之大,卫子夫岂能不知他心里有事。卫子夫低头道:“刚才的话,你都听进去了?”
卫青重重地点头,别无话语。卫子夫凝视他的脸,忽地滚下泪来,道:“我早知道瞒不了你。你,你怪姐姐麼?”
卫青道:“我,我不知。”一语未尽,便即沉默。卫子夫和他并肩立着,却目不相视,端的似“身离咫尺,心隔天涯”。
卫少儿从灶房出来,一面走来,一面问道:“你们两个杵在这里做什么?”卫青咬牙道:“二姐,你可以把我爹的信给我麼?”卫少儿登时色变,狡辩道:“信,哪有什么信?”
卫青默声不语,突然一个飞步,从屋里跑出去。他疾奔起来,赛似骏马飞驰,一溜烟的工夫,不见了踪影。卫子夫唤之不及,倚门垂泪。卫少儿左足在地下一跺,恼道:“全是你,非要和我吵。”
东方朔掀帘而出,噤声道:“休要吵闹。”卫少儿见了他,惊道:“你,你怎么在里面?你在里面干什么?”话音刚落,便急急往里屋走。东方朔经她一撞,蹬蹬退了两步。
卫少儿冲到榻边,推开董仲舒,抱起孩子,护在怀里,斥道:“你们想做什么?”董仲舒脸色发白,拂袖而去。东方朔紧跟其后,二人刚出院门,董仲舒摇头道:“好狠毒!”
东方朔道:“连大师也无能为力麼?”董仲舒长叹道:“在这世上,能救这孩子者不出三人。”东方朔皱起眉头,问道:“是哪三人?”
董仲舒道:“天道宗尊主齐元君是当今武林第一人,道法精深,功力之高,无人能出其右。最紧要的是,天道宗独有的清心诀心法对于涤洗经脉,有惊人之效。”
东方朔道:“若齐元君施手相救,于他可有害处?”董仲舒直言不讳道:“轻则损失上十年的内力,重则功力尽失。”东方朔登时摇头道:“莫说鄙人见不到他,便是能请得动他,鄙人也不会这样做。”
董仲舒也不多说,续道:“第二个人是医家乐仙君,传言其医术超凡入圣,犹在古时神医扁鹊之上。若连他也束手无策,此子的性命,大抵是难以保全。”
东方朔未料董仲舒会说出这般重的话,沉吟道:“这孩子到底受何种内伤?”
董仲舒摇头道:“老夫也不甚清楚,从未见过这门武功。此人歹毒无比,不直取这孩子的性命,偏偏将煞气逼入这孩子的经脉之中,让他生受煎熬。”东方朔眉头苦锁,摇头道:“长者之间的恩怨,奈何让个孩子受苦!”
董仲舒道:“老夫倒有一事未明。这家人并无奇特之处,他们怎会与这般人物结下梁子?”
东方朔亦不尽知其中原委,不敢妄加断言,只得道:“兴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晓。”
董仲舒道:“刚才老夫发功时,险些为那妇人所阻。”东方朔双目一亮,道:“大师的武功修为深不可测,难道真无半分法子?”董仲舒仍是摇头,道:“若是一个健壮的汉子受这内伤,老夫拼却十年功力,应当能救下。偏生是个娃娃,筋骨娇嫩,受不得真气冲荡。老夫所能做,便是以内力为他续命。”
东方朔面露讶色,他深知这般施功,事后非得大病一场,折损自身功力,不由得心生敬意,又觉奇怪,嗫嚅道:“大师不为儒家大业保重身体麼?”
董仲舒淡淡道:“老夫不过是残命尚存,折损些许阳寿,换得一个婴儿的性命,又有何不可?况且,老夫一生研学典籍,但知以理服人,从未牵涉于两派之争,今后也断然不会。”
东方朔拱手拜道:“大师之仁,晚辈敬佩。”董仲舒却道:“即便老夫拼却一生的功力,至多能续其三年性命。”说着又是一叹,道:“乐仙君仙迹难寻,近些年来,已无人知晓他去了何方,连是生是死,也是个谜。”
东方朔微微沉吟,道:“这第三个人又是何许人也?”二人已行至河边垂柳地,董仲舒盘坐下来,道:“道家有两大宗派,其一是如今独步天下的天道宗,另一个想必你也知道。”东方朔正坐其旁,道:“莫非是长生堂?”心想:“如今长生堂只顾炼制丹药,妄图长生,如何能救这孩子?难道董大师也信他们能炼成什么长生丹药?岂不可笑?”
董仲舒捻须道:“不错。但若要细究起来,此人算不上是长生堂的人。”东方朔也颇晓其事,恍然大悟,接着话儿道:“大师所指,可是殷长生的嫡传弟子?”董仲舒点头道:“殷长生一脉人才辈出,武学心法亦是奇特无比。昔日,殷长生创立长生堂,便是要将其延年益寿之法传诸世人,可惜终究未果。若是他的传人能有殷长生昔年之大成,救这婴孩,当有可能。”
东方朔苦笑道:“这一脉人亦是踪迹全无,非有三年五载,遍寻九州,怕是找不出他们。”董仲舒道:“老夫可给你三年,至于能否救得这孩子,全凭天意。”东方朔见他嘴唇发白,舌头打紧,施功之患已现端倪,可董仲舒说起这话,却是云淡风轻,心下崇敬不已。不觉关心起他来,问道:“除此之外,真无其它法子?”
董仲舒低声道:“若说法子,倒还有一个。”东方朔急急问道:“大师请说。”董仲舒凝视其目,道:“江湖上有一个传言,不知是在何时,有一位况世奇人,曾悟出一套内功心法传诸后世。据说习得此内功心法,不仅功力飞涨,更有起死回生之能。”他眼中也流露出向往之色,“世人称之为‘回魂诀’。”
东方朔喃喃道:“回魂诀、回魂诀,这个传言难道是真的?”董仲舒叹道:“这门心法曾在三十年前现身江湖,引起各派血战不休,然而下落至今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