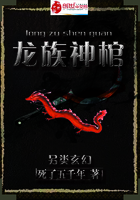常熟城的冬季秉承了亚云王朝北方的一贯的寒冷,大雪追随暴风,黑云加裹乌光,像只野兽般横亘在东陆镇的南方,虽然这里是亚云王朝的北边境,但丝毫看不到宽阔的驿道,高筑的边墙。万里雪原加上常年频现的乌光,让这座城与镇仿佛被人遗忘。
这里的祖祖辈辈没有经历过烽火擂鼓,却和孕育了自己的土地奋斗了无数年。与亚云王朝每年这时的夜夜笙歌杯光熠熠不同,坚毅,果敢,无华是这片荒芜的边陲赐予人们唯一的冬幕节礼物。
呜咽的寒风吹起小镇酒馆的酒牌却依稀听见豪爽的笑声,铁匠铺溅起的火花随风起舞……
东陆镇北60里雪原深处方正的石碑是亚云王朝的国境石,这座不知何种材质何年做成的如人高的石头,和东陆人一样,默默守卫着亚云国。
东陆人亲切的称呼它为北石,却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仿佛亚云王朝千年立国之初就已经存在。
石旁有座松木棚,简易却牢固,谓之守石。
东陆人从阿火出生很久之前就有这个习俗,每年都会在小镇即将成年的男性中由小镇教学先生挑出一位驻守国境石一年,直至下年新选之人替换。虽然教学先生只教识字,很多年里不见得会有第二个,但这一届的教学先生除了满头白发让人信服之外,博学健谈更令小镇所有人尊敬。
东陆镇的教学先生从来不是东陆人,近乎每过百年就有一位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旅者来到东陆,自称教学先生,他们教东陆人识字,帮东陆人捕猎。
至于这一位,则更是教会了小镇王大妈用东陆镇七十里外的铎拉深林中随处可见的小叶草做湿唇水。这让常年处在寒冷裂唇的王大妈欣喜若狂。阿火还记得在小时候偷用王大妈的湿唇水后,被她含着冷风的唾沫星子和利索的粗腿赶进雪原的场景。
阿火全名陈火,也是教学先生起的名字,听隔壁李婶说是因为他出生那年他爸的铁匠铺忽然起火,半座铺子在狂风中被烧塌,遂单名火。虽然名是教学先生起的,这些年也教会了阿火很多别的孩子都不曾学的东西,但此刻在守石棚里虽不至瑟瑟发抖但亦觉寒冷的阿火依然对满头白发的先生碎念不停。
上个月刚满17岁爱笑的他,是这一年被教学先生挑出的守石人。一人独在的雪原,冷寂艰苦,每过七天,小镇上的人就会送来吃用,或果脯或肉片,一件衣服、一把猎刀和两小块生火石便是全部。
为何如此,阿火曾问过父亲,父亲转述而答曰:“守石,守之为心,锻骨为石。”
且不说单纯的小镇少年是否懂得其意,但拥有两块生火石的他已心满意足。说到生火,则是对于东陆镇的男孩来说,只要有块生火石,就连以前整天追在阿火的屁股后面爱流鼻涕的三胖都能轻松搞定。
每月月中,守石人都可回小镇一次,不是因为东陆人的成人礼不够残酷,而是每月月中都是乌光最盛的时候,雪原无垠的乌云在此时仿佛会让人格外压抑。
关于东陆天空之上、乌云之中常有的乌光,则是环生大陆最离奇的景象。
多少年来,东陆镇迎来送往般的陆续来过各种人物,或富贵游客,或二三学者,镇子不大,不多停留的他们只为乌光而来。
大雪和寒风不曾阻断他们的好奇,但无知往往让人心生敬畏,于是探究无果后,在环生大陆,乌光,成为了人们猜想力延伸的天堂。佛祖启示,天降雷霆等等纷说而起。
然而当每夜每晨阿火偶望乌光,心里想起的却是那个白发先生亮眯眯的眼神和镇头久违其实才不见月余的碧婷姑娘。
这天清晨依然寒冷呼风,阿火起后立于棚口望向南方,因为今天不是吴婶,而是他老爹陈铁匠白忙之中亲自送吃用的一天。不多久,远处渐现魁梧的身影。阿火自小没见过娘,父亲说他出生后不久他娘便病逝,连教学先生也没有留住她,只说是产后虚弱。
对此年幼的他倒没有太多的哀怨,只觉着有些可惜。碧婷的妈很温柔,那自己的娘呢?
“火儿”一声呼唤打断了阿火的遐想。阿火咧嘴开笑,前跑几步站到父亲前双手比划着说道“爹,你又矮了点。”陈父笑着点点头,望着接过几挂食物的阿火说“是啊,我们的火儿长大了,以后肯定也是个打铁好手。
听闻此言的阿火抿嘴侧望父亲笑着不语,快走了几步,挡着风吹来的方向。
雪花落肩,洒下两行渐远的足迹……
几近入夜,围坐在火堆旁的两父子被映红的脸庞那样的相似。阿火望着父亲说道:“爹,南午城还是能不去就不去,那么多铁匠少您一个不少,南午城主未必在意。您这一去几月不定,我还是喜欢吃你制的腊肉。”
陈父笑到:“你个滑头,整个东陆镇都知道你爱吃吴婶的挂肉。不是我想去,镇长老王头亲自找的我,他这些年没少帮咱家。”
陈父顿了顿继续说道:“再说合两城之力百多铁匠,打造之物肯定不是凡品,你爹我身子还成,再不活动活动以后怕没这机会喽。”阿火默然,知道确实如此,铁匠这行当越是好手生意不断,能打铁的年限越短。父亲年纪四十过半,但不超过五十身子骨便不宜再锻造。
片刻,父亲话音再起:“火儿,我是看着你长大,知道这一年风雪压不住咱陈家的种,但还是要说句勿入深原,安心守石,等你成人礼一过,我去跟碧婷她妈说亲。”
“啊这个··回去再说,我听您的”阿火眨了眨眼片刻后“懂事”的笑道。
“对了,李先生还有封信,让我晚上交给你,并让你,哦,是阅后即焚。”陈父起身从兽皮衣里边说边掏出信交予阿火。
阿火接过信后皱了皱眉头,看着熟悉的“陈火启”字迹,不明白什么事能让亦嘻亦嗔的老师郑重交待。送过父亲后,躺在老旧虎皮包起的床板上,信在指尖,疑惑却越看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