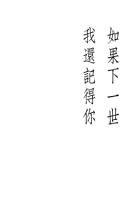贻萝醒来的时候是在东溪宫,月蝉背对着她坐在正厅扶腮发着呆。
外头已经是黑夜,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辰了。贻萝侧着头去看向窗外,发现有些不对头。
只因东溪宫外头的小院有个栅栏,里头种了些前朝住在这里的妃子种下的花花草草。所以夏日的每个夜晚,这里都是虫鸣声不断。
唯独今天晚上安安静静地没了声息。要不是屋内的这个场景,她都不敢确信是在她自己的寝宫。
头昏昏沉沉的,贻萝有些发怔,无意识的发怔。
内间的桌子上有张湿漉漉的纸,她下床走过去。才猛然想起是阮炎的信,好端端地放这怎么这个样子了?
前头发呆的人还没察觉到她已经醒来,坐在那一动不动。
贻萝微叹气,禁不住感叹,恋爱中的小少女啊。想着也没去喊她。
自己将信摊开来晾干,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水晕的模糊不清了,只落款处阮炎的名字还看得清一点。
看来就算是晾干也看不到里面写的上面了,她把信卷成小团往旁边字纸篓里扔去。什么事等阮炎回来再问他好了。
虎啸宫,殿内灯火未熄。宋离背对着光看不清神色,“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尉迟长荥剪着灯里头的烛花,甚是没心没肺的回道,“有倒是有,去西势找舟弦要到解药,一切就都变得简单得多了。”
宋离没出声。尉迟长荥当然知道梁国现在同西势的情况,单论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给出解药。
再一个,梁国现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宋离也抽不开身来专心对付这一件事。
“本来她可以不用经受这么多的。都是因为朕。”尉迟长荥朝抬头前头那个有些暗沉的背影看去,只听得他微微地叹气,“就给她自由吧。”
尉迟长荥将灯罩子罩好,走上前去拍了拍宋离,安慰道,“终归是你们有缘无分,昌和兄,有一句话我从西势回来就憋着一直没讲。”
“什么?”
尉迟长荥走到他前头,将门打开,回身看着他道,“虽然我和木贻萝也是朋友。却还是觉得能真正伴你身边长久的,唯江姐一人。”话毕,大步迈了出去。
整个虎啸宫只刚刚被尉迟长荥剪过烛话的灯还亮着,恍恍惚惚地照着门口那抹欣长寂寞的身影。
今夜大梁皇宫的上空,难得的无月。
翌日,东溪宫。尉迟长荥按着点准时来给贻萝诊脉。
二人如同平日里每次来的一般叽叽喳喳的闹腾。月蝉端着茶水来,对着尉迟长荥白了一眼,“太医没个太医的样子,每次来看病跟来玩似得。”
尉迟长荥正翘着腿把手枕在脑袋后头趟外室哼着小曲,一听月蝉这话就不乐意了。“嘿,我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我哪次是来玩的了。神医!神医你懂吗?神医看病自然和普通的大夫不了。”
月蝉嗤鼻道,“哟,神医。看病不还是要别人上。”她说的是内室那个忙活着诊脉,施针的十五。
尉迟长荥一把站起身来走近月蝉,长手往她肩上一揽,“我这是在训练我徒弟你懂个屁啊。”
内室,十五还笑着时不时的瞄两眼外头的两人。一见尉迟长荥揽着月蝉,不由得一呆。手中银针掉在了地上。
贻萝朝十五望去,顺着他的目光去看了一眼,又看向他。心里闪过什么,对着他唤了一声,十五方回过神来,对着贻萝的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贻萝回着他一笑,没做他想。